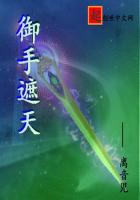唐敏
鹰
天上再也看不到翱翔的鹰了。
现在的孩子们也不玩“老鹰捉小鸡”了。
小时候,住在一大排高高的桉树底下。小木房子,前面是荒草地后面是野草地。蓝天格外开阔。在草地里赛跑,有人喊:
“老鹰!老鹰来啦!”
小手遮住阳光,久久眺望着鹰。张开翅膀,凝在蓝天心里的“一”字。许久,身子一斜,听任气流托着它回旋。
在我们心里,鹰是空中的音乐。
最难忘的是老鹰带小鹰学飞。鹰爸爸、鹰妈妈,中间是很小的鹰。逆风飞,迎风飞,并拢翅膀直线坠下,再鼓动双翼直线上升。
爸爸妈妈并排齐肩,后面是儿子。品字形上升,品字形下坠,品字形斜过蓝天。
不管多么绝望、悲伤,只要看到鹰从天上飞过,心就不会死。
大自然在安排时序和生死时,允许鹰的庄严万寿无疆。鹰是少数能够预知生死的种类。
自知死亡将至的鹰,悄悄离开巢穴,飞向人迹罕至的深山。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向高高的蓝天冲击,直到竭尽全力。它收拢巨大的翅膀,箭一样扎进瀑布冲泻的深潭。
潭水深,深得羽毛也无法浮起来。
每一次见到雪浪万丈的瀑布,便听到鹰的歌声从九泉下直达蓝天!
鹰的生存艰难。一对老鹰要两年才生一个蛋,平均两个蛋中只能孵出一只小鹰,全靠充足的食物它方能侥幸长大。
活到现在,我只抚摸过一只鹰。
我抚摸时,它已经死了。
那是我住在小木房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看见四五个解放军战士,持着枪,悄声没息地来到桉树下,躲躲藏藏地眺望天空。我们跟来跟去,问:
“叔叔,你们打飞机吗?”
“小声点!我们打鸟呢。”
“你们谁打得最好?”
“他!他家祖祖辈辈打猎。”
我们立刻迷上了这位严肃的小个子战士。
可是他们并不打麻雀,在这里等了有四五天。我突然明白了,问小猎人战士:
“你们,要打老鹰吗?”
他一下子捂住我的嘴,悄声说:
“不许讲,它会听到的!它知道有人打它,就不出来了。它是最了不起的鸟!”
我顿时呆住了。等他们一走,我和伙伴们破坏性地向天空大喊:“老鹰啊!不要来!”
但是枪终于响了!半自动步枪和谐清脆的连击。我奔出小木屋,看见鹰以一种波浪状的斜线向地面上慢慢落下来。
“啊——老鹰!老鹰啊!”
我奔进宽阔的野草地。
老鹰啊!老鹰掉在草地上无声无息。
猎人小战士从远处奔来,神情万分痛苦。他跑起来也是无声无息的,像敏捷的鹿儿。但是他张着嘴,眼光迷离。
我从草地上爬近那只鹰。它竟是那样年轻,像十六岁的少年。一只翅膀张开,保持着飞翔姿态。它的一只眼睛看着蓝天,睁得圆圆的。这是一颗淡紫色的玛瑙,布满细小的蜂窝状棱面,太阳在里面反映出无数亮点,最清澈、最明亮的。
传达室的贺老头挥舞着大蒲扇,骂声震天地跑来。他本是个老猎人。他对战士们大喝:
“你们!竟敢打老鹰?!从今以后,你们的枪子儿别想再打中目标啦!谁打死老鹰,谁的眼要瞎掉的!”
小猎人屈下一条腿,跪在鹰身边,抚摸它的羽毛。他颓然、悲伤。
“我是为我们班长。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让我瞎了眼吧!让我再也不能打猎了吧!”
其他的战士默默低着头,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从那次才知道,人的脑子受了伤,会留下剧烈的头痛症,老鹰的脑子是最好的药品!
战士们带走了那只鹰。
我突然追过去,说:“让我摸一下,叔叔!让我摸摸它!”
我的手触到光滑冰凉的羽毛。我心里发出响声,小小的、晶莹的瓶子就这样碎开了。
从那以后,我心目中的鹰都被击中了。它们纷纷坠入雪浪腾空的瀑布,一去不复返。
没有鹰的天空,没有庄严,没有音乐。
只有长风呼啸、蓝天清澈时,还能听到鼓动羽翼的声音。巨大的、透明的鹰张开翅膀,它的羽毛,它的骨骼,它的爪和嘴,还有它犀利的眼睛!
我再也没有见过飞翔的鹰了。
虎
画册、故事、电影,所有幼年的教育告诉我——老虎是个坏东西。
因为不想看见老虎,连心爱的动画片也不敢去看了。外公一再保证:今天的没有老虎。
糟糕,又跳出一只嘴巴血红,不讲道理的傻老虎!它伸爪子、撅屁股、尾巴来回扫,威风地跳来跳去,发出呜呜长鸣。
照例来了一只洁白的羊羔。我神昏气短,缩在座椅里。它无忧无虑走向老虎。我转过身,看着放映孔里旋转的光柱。
“吃掉了吗?”我浑身发抖,“吃掉了吗?”
“吃掉了。”外公说。
回过头来,老虎正得意洋洋逼向羊羔。我又扑到椅背上。
外公说了二十遍:“真的吃掉了。”前后左右的邻座也保证:“是吃掉了。”我回过头来。森林里鲜花盛开,百鸟鸣唱。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一直吵到邻座们气愤了,外公只好携着我离去。他忧心忡忡:“这么胆小,长大了有什么用呢?”
为了让我勇敢,爸爸妈妈残忍地拖我去动物园看老虎。我决一死战,闭上眼睛。
“老虎不可怕。你看一下。”
“只要看一下!”
“要不我们就等下去。等到你哪天肯看了,我们再回家。”天知道,我多么厌恶,想吐!
备受迫害的我!睁开一只眼睛,看了!扭头就跑。
铁栅栏深处有一个乌黑的方穴,拖出来一条大于猫腿一千倍的后腿。又
脏又潮,自暴自弃,绝望的大后腿。
老虎!最恶心!最难看!老虎!良心烂透!
一直到15岁那年,我才真正看到了真正的虎。
到闽北山区,我首先就问山里人:“这儿有老虎吗?”
“老虎吗?可惜现在不多了。”
他们满脸缅怀神圣事件的表情。
“老虎,会吃人的!”我说。
“不,你不害它,它不会来吃你。”山里人说,“难得也有吃人的老虎。它们喜欢偷猪吃。”
山里人好像巴不得有老虎来村里偷猪。那样可以整夜点起火把,妇女们聚在村中心,从小到老的男人围着村子跑动、喊叫。火把的龙向着深夜的高山峻岭示威。
山上的老虎仿佛心领神会,好久不来拖猪。
老虎不来,山里人竟有点儿寂寞。
山里有了老虎,便有了生与死的种种情趣。山里人最喜欢讲他们遇到老虎的经历。
那种兴奋,那种自豪,仿佛得到荣誉。
冬月清澈,白雪遍地。打着手电筒走路,危险比点火把的大。迎面看见有人打着手电过来,近在咫尺了,才从黑暗中显出狰狞的虎头,一双金亮的圆眼睛!
彼此都误会了,以为遇见了同类。
停下来,双方都珍惜生命。这时候不能喊,不能奔,脚趾一点儿一点儿移向路边,彬彬有礼地、贴着草木,蛇一样地溜过去。
老虎站在那儿,动它的脑筋。一会儿,它低下头来,继续赶路。
有时遇到好奇心强的老虎,会掉转头来跟着人走。要非常非常坚强,才能保持正常的步子走回村里再昏倒。往往是忍不住又跑又喊,激起老虎追逐猎物的本能,一直扑逗到人气绝身亡。就是老虎不来扑,狂呼乱叫奔进家门,气一松,暴出浑身大汗,倒地便死。
这种恐惧强烈地刺激着山里人的心。大白天走路也感受到广阔的危险感。枯树怪石荒草。生命在热血中涌动,晨星暮日,荡涤胸怀。
猎虎的人从江西、浙江过来,山里人讨厌他们。“为了钱,什么都不放过啦!”然后唾一口,把脸板紧。猎人被虎吃了,山里人感到自豪,又有点儿怜惜:“我们山里的虎啊!”
我听了许多关于老虎的事。
老虎不住在树林里。它们极爱清洁,闻不惯兽类的气息,受不住落在头上的鸟粪、虫子。
它们住在茅草覆盖的长冈上,到很远的地方狩猎,在溪流里沐浴。干干净净的老虎走到长风拍打的山冈顶上,等待明月从东方升起。
鹅黄的月儿从高高山冈下群山的海洋里露出来,光辉冲散星斗。
老虎发出渴望的、忧郁的长鸣,通过风送向月儿,催促圆满的月亮从地上跃起。
这是孤独的男子汉在呼唤永远不来的情人。
我开始盼望见到老虎。山里人传染给我这份奇怪的愿望。只要是诚心的愿望,大自然一定会听到。
秋天来啦,山坡上盖满黄叶,红树、绿树在干燥的空气中劈啪拍手。阳光是凉凉的金色。
秋天,砍柴的季节。一握粗的杂木敲上去梆梆响。梆声沿着山谷好听地跑远。
我贪心地砍倒一棵一棵落尽树叶的小杂木。我眼前金灿灿的秋色突然聚成一团,在黄叶盖满的坡顶上无声无息地移过。透过疏疏的杂树灌木,星星般耀眼的红浆果向两旁分开。
柴刀栽进厚厚的落叶下,一只年轻的虎站在不到五米远的坡上。斜阳从它背后照来,它被明亮的火焰包围,颀长优美的身子呈现在我眼前。它停下来两秒钟,一只前足停在空中。
它侧首看了我一眼,似乎感到意外。
金色的目光和阳光溶在一起,飘过一绺嫣红的烈焰。就看了这短短的一眼。
人类最美的目光都死了。
静静的、威严的、穿心透腑的、超然的一眼。它转过头,踏下前足,走向太阳。一身富贵光亮的皮毛,棕色的横纹随着步子流水般滑动。爽白的天空把每一丝虎毛映衬得清清楚楚。
像无形无具的梦,消失了。
我沿着山坡狂奔而下,血液在全身蒸腾。激情脱去沉重的躯壳,裹着我轻盈地滑翔,哽咽堵塞了喉咙——
我受到了真正的蔑视!
仅仅两秒钟!人的骄傲颓然倒地。这轰顶的刺激炸开一片崭新的欢喜狂悦。
大自然用两秒钟告诉我,人可以夷平山川,制造荒凉,淘空地球,但是依然侵犯不了它的自由!这肃然起敬的、无法驾驭的自由!
彻骨的幸福倾倒下来。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人能用蔑视来伤害我了,绝对没有了!
老虎光艳夺人的美目敌御四方。
我飞奔回村,跃进家门,彻底欣慰地扑到床上,每根骨头、每块肌肉都在发抖——
啊,我见到了老虎!
彩虹
有了虹,荒凉的深山有了灵气。
虹的表情,山里人百看不厌。
大自然的手抚摸了哪里,哪里就留下彩虹。
虹是静静地呈现的。随之,喧哗的草木,人群也静下来,看着虹慢慢舒展,在碎雨和急风中凝然不动地悬在空中。
静穆优美的虹,一道一道浮现在眼前。
在遥远遥远的天边,纵深而明亮处的山峰上,虹很细很淡,像一道无力而忧伤的眉毛。猜不出应该有怎样的一只眼睛来与之相配,想象不了真有那样的眼睛,怎么能让它和短命的虹一起消失?没有眼睛的眉毛啊,寂寞的虹。
乌黑的峡谷,惨白的溪水,雨后湿淋淋的石阶,上山的小道陡直地升上十里。歇下担子喊一声,再喊一声。
声音虚张空洞地纷纷逃回耳朵里。怆然的眼睛找不到答应。
啊,有的。在高处,山路的尽头,两峰间的峡口,一片蓝天渐开,斜斜地亮起一痕微笑的虹。说不出的谢意,温柔的虹。
厚厚的青云挤在天顶翻滚,撞出粗大的雨粒,东一点西一点射下来。阴沉着脸的云里裹着发怒的虹,向地面逼来。冷风飕飕,五彩的龙发出异样鲜艳的怪色,好恐怖的虹!
对峙的陡壁悬崖,不见底的深谷。伐木人在两边崖壁中凿出栈道,积满腐叶,柔软无声。栈道上下都是一球一球绵密的树冠,经历了隆冬寒春,彩色的树叶中泛出一层新绿。延绵的峡谷像感觉温暖的绒绣。
似有似无的雨,若即若离的雾,宽阔的虹的彩带从深深的谷底拔起,透明的七色在峡谷沉重的底色前聚起灿亮的气流,用力冲上淡蓝的天空,在那里消失了另外一端。
隔有彩虹,两边栈道上细小的行人在变幻颜色。“嗬——嗬——”的呼唤声透过彩虹传到对面。瞧啁,这雄浑有力又半魔半仙的虹。
虹不尽是透明的,它会像新鲜的奶油那么浓。粉红、粉黄、粉绿、粉蓝,结结实实。它先在远处的山头站好一只脚,然后划出一个真正的半圆形巨弧,另一只脚迅速地垂下来,好像要落到我们小小的村子里。男女老少高兴地欢呼。彩虹却把脚放在了村后的山冈上。年轻人拼命地奔上山冈。
“抓住它的脚,抓住它!”
狡黠的虹一点一点后退,退过山冈,退过溪谷,退到远而又远的山头上。小村子像小船,从虹的桥拱下飞流急下。
鲜蓝鲜蓝的天,撕成破布般的云,橙色的西方,又小又亮的一点太阳,巨大的彩虹威风凛凛地站着,左右映出两道清淡的虹影。空中那样拥挤,一片欢乐的喧哗。
村里人不干活、不做饭,高声谈笑,仰头望虹。小孩、小狗、小鸡跑得眼花缭乱。
大自然这样与人娱乐。
它的关怀体贴入微。
在山区我患了很重的疟疾病。这病常发。身体给折磨得不成样子。
又一次发病了。没有钱乘车回家。离家七八百里,想要搭上一辆运货汽车,真是渺茫。
下了一夜的雨,早上起来,草木衰败,一片凄凉。不到发病的时候,头脑里很清爽,感觉到秋气萧然。
近晌午时,出去帮我找车的同伴捎来口信,叫我下山。运山货的卡车下午进县城,明天一早开往福州。
我离开小村子,只见白茫茫的云海横贯天际,到处露出海岛般的山峰。云海平展展地滚动波浪。我走在狭长的山冈上,在云海中宛如一个孤岛,公路从岛上纵伸而过。
云海底下仿佛是几万年不见阳光、没有声息的深海海底。
云海之上的天空高处,云层正由青转白。这两层云海中漾溢着不可察觉的阳光。
白色海洋中的荒凉的岛,空荡荡的路。只有我的脚步声。远处银灰色、蓝色的群岛在轻移慢动。转过一个大湾,下坡。
我一下子呆立不动,吸进一声“啊……”
在二十米来远的前方,巨人的虹的瀑布从大顶的云层里倾泻下来,一直落在公路路面上。宽阔的彩虹切断坡上的树木,切断公路,切断坡下的乱石坡。
无限透明的屏障,笔直地竖在前面。
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屏息靠近彩虹。
我眼前一片闪烁的模糊,看不见了。那是泪水布满了眼眶。映满彩色虹光的眼泪坠落。
彩虹没有后退。清清楚楚,虹的外弧到内弧,红橙黄绿蓝靛紫,最纯正、最洁净的色彩排列在眼前。
我站在直冲霄汉的巨大的彩虹面前。
小岛上微小的人,拖着疲病,软弱地站在举世无双的长虹面前。
彩虹溅落在地面上,激起蒸汽般颤动的气流,亿万缕升浮的细弦交织着向上,形成并不存在的虹的平面。在这个平面后头,每一片叶子,每一根细枝,每一块石头,直至路面上每一颗沙子,在虹光内的所有物体都镶上了金色的光圈,溶解般地颤栗。甚至沙子,甚至泥土,都那样清晰,那样洁净。
红色的树;橙色的草;黄、绿、蓝分割的路面;靛色的石头;紫色的泥土。洁白的云潮也蒙上不同的七种颜色。
我举起双手,伸进彩虹。立刻有一双透明的手掐住了我的手。手掌、手指绕着金色的浮光,那双透明手把我的手染上了超越现实的光辉。我感到它的抚摸,无限的安慰,无限的怜惜。
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希望在心里苏醒、抽芽。我的手在彩虹里变幻颜色。
从天上倾下来的色彩,缭绕我的生命。
云海下面,隐隐传来汽车爬坡的吼声。我和彩虹都猛然一惊。我们的相会要结束了。
我穿过彩虹,它竟是这么薄。被彩虹燃烧的景物还原出本来的色调。我回头,彩虹又点燃另一面的景物,只是再没有前一刻的辉煌。
我知道,一生仅有一次的相会结束了。
我退一步,再退一步。
彩虹从路面上缩起来,慢慢向空中抬起。
无限依恋,还是慢慢退远了。
彩虹黯淡了颜色,变得又稀又薄。
它将回到天上。我的脚踏进云海滚滚的白潮。
云潮淹没了我的腿。
我知道,再也没有一双手能像彩虹的手。
云潮淹过了腰。
我知道,再也看不见如此清纯的色彩了。
云潮冲击到胸前。
我知道,再也不会和彩虹并肩而立了。
白色的潮卷过眼睛。我坠入沉闷的雾中。
啊,彩虹,彩虹。再也无法相见的彩虹。
云雾底下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人声,生活的各种声潮在大地上起伏。我穿过云雾,朝着这汹涌的声潮走去。
彩虹,彩虹。缭绕过我的彩虹。
它是无形无具的色彩,它是并不存在的事物,它是光明的缥缈的本质。我们的世界正是由它照亮的。
多少天,多少年,永远照耀的光明。
在这个世界上,我已得到了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