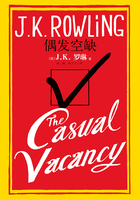研究凉州神婆是很有趣的事,它不仅是民俗学的范畴,更涉及到文化学和心理学领域。笔者在长篇小说《大漠祭》中,塑造了一个神婆,很能代表凉州神婆。节录如下:
神婆姓齐,是沙湾的二号有钱人,五十岁了,脸上的皮尽打了褶儿,上嘴唇长,下嘴唇短,红丢丢的,说一句话就伸出舌头多情地舔舔红唇,抿着嘴笑。她走起路来也风骚得很,又是个小脚崽崽儿,真正扭成个风摆柳枝儿。听说神婆年轻时害过一场病,病了三年,怎么治也治不好。第三年的一个夜里,忽然有了神。神是每天晚上亥时来。来时,神婆总要打三个呵欠,再打个冷颤,浑身的骨节就咯吧咯吧响起来。响一阵,才口吐白沫晕过去。晕一阵,神就入了窍,就能给人算命燎病。
……病一燎罢,神婆就妖声妖气拖一口怪腔调说自己是陕西蓝田人氏,十八岁那年病死的,修成了鬼仙……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但求速成,形如槁木,色如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精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名鬼仙……于是,一入夜,远远近近的人便挤满了神婆家的大书房。几十年来,沙枣木门槛给蹋折了十八次。
读了上面的文字,读者便明白凉州神婆的特点了。概而括之,可有以下几点:风流多情、患病多年、鬼神入窍、举止神异、交际很广、生活富足等。下面,分而述之:
一是风流多情。在生活的重压下,凉州女人已无暇浪漫了。但凉州神婆却可以例外,她们大多健谈,会唱歌,会跳舞,极有情趣。这是凉州神婆独有的秉性,无论在当神婆前,还是成神婆后,她们都是一群游离于当地妇女圈之外的女性。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二是患病多年。在现实的希望破灭之后,她们无一例外地患病了,病得死去活来,直磨得“形如槁木,色如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才终于有了自己的“神”。
我在《凉州与凉州人》中写道:“凉州女人多梦,几乎每个女人都有一晕向往,一抹绚丽,一个五彩梦……那是支撑她在艰辛人生中挺直脊梁的标杆。一旦毁灭,人生的殿堂随之倒塌:或从此沉沦,或以死殉梦,或浑浑噩噩度世,或遁入宗教以求寄托。粗心的凉州男人是读不懂凉州女人的。雷台湖里尽神婆,居士群中多女人,此中真味,谁能解得?”
读完这段文字,也许你便明白了凉州女人的患病之由,你才会明白神婆为何尽是风流多情的凉州女人。
三是鬼神入窍。女人病到一定程度,鬼神便趁“虚”入窍了。
沈从文在《凤凰》中有相应描写:
……因人与人相互爱悦和当前道德观念极端冲突,便产生和神怪爱悦的传说,女性在性方面的压抑情绪,方借此得到一条出路……觉得洞神亲自换了新衣骑着白马来接她,耳中有箫鼓竞奏,眼睛发光,脸色发红……家中人……只以为女儿被神所眷爱致死。料不到女儿因在人间无可爱悦,却爱上了神,在人神恋与自我恋情中消耗其如花生命……她在恋爱之中,含笑死去。
我在《凉州与凉州人》中写道:“与沈从文描写的苗女不同的是,凉州神婆在与神的相恋之中,‘幸福’地活着……相较于一般凉州女人,能与‘神’有感情交往和性交往的神婆无疑是幸福的。”
四是举止神异,神神道道,异于常人。“神”入窍时,神婆常见的表现是打呵欠,打冷颤,浑身骨节暴响,再口吐白沫晕过去。也有以“人神合一”自称的,便用不着这些入窍表演了。在当地人眼里,她们是“学”来的神婆,其地位,自然不如神入窍者了。
此外怪异的,便是口音了。神入窍后,神婆的口音便也成“神”的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平日呈萎靡相且操一口硬怪怪的凉州土话的农妇,忽然间神采飞扬地拖一口外地腔调出现在村人面前,出口成歌,随问随答,不假思索,言辞顺达押韵,怎能不令人惊诧啊?
五是交际很广,生活富足。有了“神”后,女人们的苦日子才算熬出了头。
一位自称是某个大人物“入窍”的神婆是凉州神婆中公认的明星。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南方方言,能装扮出“大人物”特有的派头,言谈举止,威风异常。她的生意,自然格外红火,家中常常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她“出马”已有十年。有人算过一笔细账,以最保守的每日十人计算,再以最保守的每人孝敬十元计算,每日她足有百元的进项。十年下来,她至少已有数十万的收入。
这样的神婆虽是个别,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凉州神婆大多相对富足。她的“神”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惯于靠老拳在女人身上显示“权威”的凉州男人便再也奈何不了她了。
(雪漠文化网www。xuemo。cn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