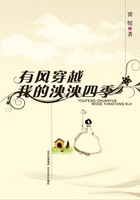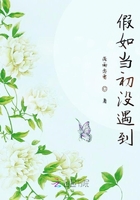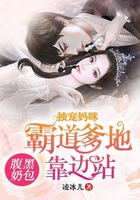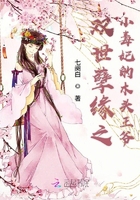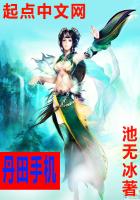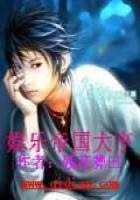杜甫流离失所逃难到成都,好不容易靠王十表弟(仅是个小小的司马,出门还得步行)的资助,盖了几间茅屋,不料五月遭一场风雨,把门前二百多年的老柚树都连根拔起刮倒,可见茅屋所苫的草已寥寥无几了,“三重茅”,茅少得可怜,所存微乎其微。可是郭老却偏说住上高大的草房,冬暖夏凉,连他都没住过,说“三重”是每重半尽厚,三重是一尺五,大地主的草房也没这么厚的。
杜甫自从住在浣花溪,与邻居处的关系很好:“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野人相赠(樱桃)满筠笼”,“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儿童们对老诗人更好:前一年,江水暴涨,是“儿童报流急”的,平日“惯看门户儿童喜”;老诗人更爱护儿童,看到他们扑鱼猎鸟,采莲控藕,把鱼鳞碰掉了,藕上带着河泥,就关心儿童们,告诉他们“人情逐鲜美”,“物贱事正睽”,卖不上好价会吃亏的。可是,这场八月风暴把茅屋上的苫草吹得到处飘落,这些孩子不但没像往日那样热情地来帮忙,反而“公然抱茅入竹去”,累得老诗人“唇焦口燥呼不及”,暗恨这场风灾,把孩子们竟逼得竟“忍”心干出“盗贼”一样的事来。这是恨灾难大,因为五月、八月连遭风雨灾难,把周围人们的生活害得苦到如此程度,这哪里谈得上“阶级对立”,“把贫民孩子视为盗贼”。你想此时杜甫如真的是个大地主,还用自己去拾茅草,还用自己去追孩子们,不早派恶奴去追打了吗?不但未派恶奴,连恶狗也没出来汪汪两声,连自己的孩子也没让出来追赶打骂,而是自己和普通穷人一样心疼这失去的茅草,去自己“唇焦口燥”地追喊,累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至于说把自己的孩子称“娇儿”,并不是在对“群童”“抱茅”一事相对比说的,而是回屋看到“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时,孩子们不入被窝安睡,因为“恶卧踏里裂,布衾多年冷似铁”,才心疼孩子说的。杜甫此时的生活情境很苦:“翠柏苦犹食”,“无衣床夜寒”,“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贫病转零落,”“三年饥走荒山道”,“故人供禄米”,来了客人“自锄稀菜甲”,孩子经常挨饿“恒饥稚子色凄凉”,穷困如此,今天又看到遭此灾难,自己当父亲的怎能不心疼地叫声“娇儿”!这正是自爱自怜自责自怨的苦情流露。
也正因为,看到家中妻儿之苦,最后才“推己及人”,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天下寒士”当然包括方才“抱茅入竹去”的“群童”。因为他方才亲眼看到“群童”穷困到一点茅草也抢抱的程度,他们回家不也要过着和自家“娇儿”一样的不能安眠的生活么?杜甫这些年看到很多穷困的流离失所的人民,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愤愤不平。他同情战乱中的农民,“边庭流血成海水”,家里却“禾生陇亩无东西”,“具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不止一家如此,不仅一年这样:“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黎。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直弄得“老弱哭笑道终”,“死人如积丘”。再加连年自然灾害,害得人吃不上,“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穿不上,“焉知南邻客,九月尚”。“天下寒士”不包括这些人,能包括谁呢?可郭老偏说“士”乃读书人,读书即地主分子,“寒士”只能是破落户的地主分子。不错,杜甫是有些未官的地主友人,如姜士少府,秦少府,卫八处士、阮隐居、赞上人等等,但是这些人全接济过或招待过他,人家有鱼宴、黄粱、新菲招待他,他得到的是这些处士对他的援助,他怎会在风灾雨难之后忽然想招这些人去住他理想中的“广厦”呢?
这种不懂,是因读的人带有强烈的成见,不想去设身处地心平气和地去理解作者思想感情。所以没个真正读懂,实际也不想读懂。
还有一种读书人,故作新奇,标新立异,也达不到读懂的境地。就拿头几年争论岳飞的《满江红》的著作权来说,就属于这一类。标新立异,必须有真新,才可以另立新说。没有“新”,而故意节外生枝,提出个“新”来,那就是没读懂,装懂。取消岳飞著作权的理由不外这几条:《四库提要》早已质疑;岳珂编辑时未收入;是文征明伪作,模拟得像;岳飞时西北无战役,不能说“踏破贺兰山”;“匈奴”“胡虏”是汉代说法,不能用于南宋;不同于《小重山》风格。
这些都是强词夺理的,一点也站不住脚:《提要》质疑,只是参考,不是结论,不能作为依据。岳珂后来在《桯史》已附录这首词,说刻本不可靠,那你拿出更可靠的来,再说明刻本不可靠,那《桯史》也不可靠么?《桯史》附上了这一首词还不可靠吗?再说遗文,后世发现补进去的,也不在少数。是文征伪作,只因文写过一首《满江红》,风格相类,就给文征明安上了。其他根据没有。岳飞《满江红》以后,仿其风格之作多矣,能说都是伪作者么?贺兰山,只是北方的一个历史性标志,并非固定专指。岳飞说过“北逾沙漠,喋血虏庭”,能说沙漠是西北瀚海,于是说《五岳初盟记》也是伪作。岳飞目的在于“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故地乃指中国古代旧有之领地,当然包括西北,这是他的战略目标,不一定没得说“痛饮黄龙”。至于匈、胡更是泛指北方与南宋敌对势力而言,如果连匈胡是汉代称呼都不懂,那给文征明安上也不公平吧?难道文征明连汉、宋还分不清么?不能这样看问题。《小重山》与《满江红》写作背景不同,一个是处在受重压时期,一个是处在进军胜利时期。前者有些低抑,后者有些高昂,这乃自然之理。总之是猎奇之辈的借口,非真想读懂者也。事实证明,有些细心研究者,近年已查出词中所指的贺兰山,不是宁夏的,而是河北的具体所在,岳飞真在这里作过战,驻过军。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好故作惊人之笔,如说《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又曹雪芹实无其人,应该是“石头”;大禹没有这个人,是个大爬虫等等,荒谬之说迭起,“搅乱一池春水”,徒使文人费不少笔墨去打官司。
搞艺术而又不懂艺术创作规律的人也常读不懂真正的艺术品,清初的毛奇龄本是翰林院检讨,能诗词散文,以治经史音韵学著称,又从事诗词研究,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可是他却读不懂苏东坡的诗,他说东坡“谓其词繁意尽,去风骚之意甚远。”友人举《慧崇春江晚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毛奇龄却发出谬论:“鹅讵便后知耶,独尊鸭也?”这是多么荒唐的说法!如他所论,则江上除了鹅,还有各类叫不上名的水鸟,还是来往船只,等等都没写上了。竹桃两三枝,也不对,应是千万枝。满地岂止蒌蒿、芦芽,还有各种草木,写不胜写。岂止“河豚欲上”、春江水暖,水深处的鱼虾等水族哪个不想浮游上下玩个痛快呢?二十八个字的绝句怎容得下如此之多的物类?写一部名物专著,也得万八千字吧?毛奇龄会这种文艺批评家就是不懂创作规律的,他们不知道艺本创作向来是以个别显示一般,以这一幅春江晚景来看整个春光之美。这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的特写镜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之物。它不可能也没必要把春江中的所有动物摄取进来。何况这是一首题画诗,惠崇画的内容有什么,苏轼也只能写什么,不可能题画外物,写画外诗。
要说李渔该比毛奇龄更懂艺术吧?一生从事戏曲、小说的创作,有极其丰富的艺术创作实践。特别对闺情儿女之情表现尤多。可是不知怎的,对宋祁的《玉楼春》(又名《栏花》)没有读懂。
“东城渐觉风光好,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杏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唐宋诗词简释》评价非常之高:“此首随意落墨,风深闲雅。起两句,虚写春风春水泛舟之适。次两句,实写景物之承,绿杨红杏,相映成趣。而‘闹’字尤能撮出花繁之神,宜其擅名千古也。下面,一气贯注,亦是劝人轻财寻乐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若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可李渔《窥词管见》却大批这个“闹”字:“若红杏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谓闹字极粗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
§§§第28节杂谈诗词点评——《难老泉声诗词选评》读后
山西诗词学会新出的《难老泉声诗词选评》是一本好书。正如其《前言》所称:“此书评诗,见仁见智,有欣赏有批评。”看来此意图是达到了。全书共选253首,欣赏评语占2/3,批评语占1/3,这在近年一片颂扬式评诗的大潮中是罕见的。一位诗友说得好:“论诗之作极易流于空泛,只一味赞去,说不好便如谀墓碑文,了无情味。这本书基本没有这类阿谀之辞,即使对名家之作,亦有批评者。大多评家的评语是严肃认真的,是与人为善的,真诚的,平等的,互交心曲,相互探讨,尽量在肯定优点之后指瑕正误,一阵清风,吹动骚坛春意浓。”
书中有不少好的评语。有的善于发掘诗词内蕴,起到画龙点睛之效。如对《自西安还洛阳道中作》:“河声岳色双筇外,汉恨唐愁一梦中,此处犹堪摩老眼,铜驼陌上看革呈红。”评道:“最后一句却呈现出异常光彩。作者在铜驼陌上观看冲天怒放的牡丹,既反映了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无限生机,也反映出作者的无限欢欣,何等新奇!”这样评语真令人精神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