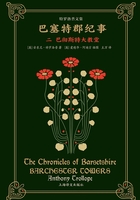7月8日。
山野,阴雨霏霏。队员们从山下爬上来,一头钻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中。
由于下雨,林子里的光线不充足。不过这种天气情况下拍出的画面是我最喜欢的,光线均匀而凝重,各种色彩在磁带上还原出它们特有的质感,不像阳光下的物体所呈现出的都是经过雕琢的形态。
整个搜索的过程异常沉闷。可能是因为昨天在营地发生了那件事情的缘故,大家的神情都很严肃。因为在下雨,当时一定给拍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潮湿的空气对摄像机的危害最大。所有电子设备的最大敌人就是水,一旦空气中的水含量超过一定的指标,机器就会自动启动保护功能,从而停止工作,直到机器内部的湿度恢复正常。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摄像机穿上一件特制的“衣服”,避免水直接淋在机身上。但是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这层衣服会阻止空气流通。机器运转产生的热气因此无法排出,会在衣服所包围的小空间里结成水汽,这会让本来就恶劣的拍摄条件更加不理想。
画外忽然传来夏老师急促的喊声。
夏老师:你们快过来看。
大家快速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汇拢。见夏老师在一棵粗大的冷杉树下用手抹去附着在树皮上的青苔。随着青苔一点点剥落,渐渐露出树皮上的一些凹痕,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自然生长的,带有明显的人工痕迹。等完全将青苔清理干净,一个刻功一流的图案呈现在千年古树的树干上。
一时间,所有人都一言不发,集体处于失语状态中。许久,周立君才终于打破了沉默。
周立君:那里还有一个!
果然,在不远处的另外一棵树上有一个不同的图案。于是大家开始在周围寻找,总共发现了六个不同的图案。最后大家围在最早发现的那棵树前议论起来。
Helen:这些符号有新有旧,有些是刚刻上去的吧?
夏老师:那边有一个,用手摸还有新鲜的树脂浆,说不定刚刻上去不到几个小时。
Helen: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夏老师:一时还不好说。我都拍了照片,回到驻地再认真琢磨一下。不过这些符号所刻的高度有高有低,应该不是一个人刻的,最高的身高估计在一米九以上。
刘媛媛:你怎么肯定是人呢?
夏老师:这些符号刻功精良,应该使用了很好的工具。另外造型也是很讲究的,没有很高的智商根本办不到。
尹杰:会不会是什么文字?
刘媛媛:这些文字一定代表一个完整的意思。
尹杰:对,是天书。哦!我们终于有重大发现了。我们要改写历史了!
刘媛媛:这么看来出现在我们营地的那个符号也是它们干的。它们一定在向我们传达什么意思吧?
尹杰:不管是人还是其他什么刻的,可是树下一个脚印都没有。难道它们是悬在半空中的吗?
Helen突然转向Zachery。
Helen:Zachery,你那天晚上究竟看到了什么?
Zachery铁青着脸沉默不语。我能清晰地听到雨水“落在树叶和枝干上发出的滴滴答答”声。
Helen:既然这些符号有新有旧,说明这里是它们不断光顾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这里作为重点观察的区域。我们分成两组,每一组一部摄像机,轮流二十四小时守候,希望能有所收获。
虽然在树上发现的那六个符号中,并没有与营地或Helen他们身上同样的,但我意识到这是出自同一类的作品。当然,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比如我觉得营地和树上的符号从线条上看更具亲和力,显得十分柔和,充满善意;而Helen他们身上的却隐含着说不清的肃杀感。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Helen他们目前十分接近危险的边缘,所以有些先入为主。
而此刻,那些身处漩涡中心的摄制组成员们还丝毫没有体察。他们还沉浸在专业摄制人员因为可能即将拍摄到世界奇观而感到无比兴奋的情绪中。
看到帐篷中得意洋洋的夏老师,就会知道我说的没错。
夏老师在帐篷内挂满了他拍摄的树上那些符号的打印照片。他咬着一支铅笔,一边听着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时断时续的短波音乐节目,翻阅着随身携带的工具书,将那些符号和书上什么东西进行比较。
作为古人类学博士,这应该是他最幸福的时刻。在无人的神农架原始森林中,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沉浸在学术思考中,甚至即将破解全人类都未曾触摸到真相的答案,这恐怕在他人生中是难得一次的美好时光。
一想到“一生”这个词,我不免为夏老师的命运感到担心。他现在还活着吗?从编号最后一个号码的录像带看,画面中仅仅出现了Helen和窦炎,而他们最后也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至于夏老师、刘媛媛、周立君、尹杰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抱任何幻想。
我在为那些摄制组成员的命运提心吊胆,却忽略了我自己还身处在危险的漩涡中。对于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我设想了数种可能性,但是当它接近我的时候,我的那些假设都变得可笑起来。
7月11日。
这些录像带的编码中缺少三个日期。后来我才知道,那并非丢失了,而是他们在山上空守了三天,一无所获。
Helen:我们在这里等了三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它们都藏起来了吗?它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许它们仅仅是匆匆的过客,和我们擦肩而过。我没有答案。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尹杰:这里太潮了。天天这么下去,我身上非烂掉不可。好痒啊!窦炎你有什么止痒的药膏吗?
窦炎:在帐篷里。
尹杰:他们换班的怎么还不来?
Helen:那我们下去吧。你腿上的伤口必须处理一下。不要抓了,都化脓了。
镜头出现尹杰伤口的特写,在大腿根靠近耻骨的地方,有一片红肿的创面。创面的中心部位已经溃烂,看着令人作呕。我忍不住将这段快速扫过去。
不知不觉已经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饥饿感袭来,我感到口渴得不得了。我必须马上喝些东西才能继续工作。
忽然,画面如同受到强电波干扰一样,出现一片雪花点。我的心狂跳起来,我记得同样的现象曾经在高强那里发生过。就是因为当时磁头被脱落的磁粉糊住了,高强才替我受过,送了性命。如果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将面临什么?
我急得差点要叫出声来,雪花点却又神奇地消失了。我松了一口气,赶忙将录像机停止,让它也休息一会儿,散散热,让各部件恢复到最佳工作状态。我也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出去找口水喝。
我悄悄拉开房门,走廊里一片漆黑,值班室的灯也熄灭了,值班的警官可能已经进入梦乡。按照一般政府建筑的习惯,洗手间通常设在走廊的尽头。我向前摸索着,走了不多时,我的鼻子告诉我洗手间靠近了。我急不可待地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找到水龙头,打开水龙头,大口大口地猛灌水。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干渴,就像在沙漠里待了三天没有喝水一样。
这时,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吓了我一跳。我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见是一条短信,是我的那个研究古人类学的朋友发的:
你是从哪里得到那个照片的?妈的,不得了啊!这是重大发现啊!立刻上网,上面有你要的东西。保重!
我的心再次狂跳起来,隐约感觉到我离一个巨大的秘密核心不太远了。
在派出所一定有可以上网的地方,资料室是可能性最大的。
我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进入资料室。这还得感谢我妈妈,大学时她给我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市档案馆的新馆安装所有的门锁,我不但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份不菲的工资,还学会了安装锁和拆卸锁的各种技巧。
这件事情过后我才知道,派出所的每一个办公室的电脑都可以上网,木鱼虽然只是个小镇,但也并没有远离尘世。可当时我只能选择一根最硬的骨头来啃——被兴奋的情绪冲昏了头吧!
我按照短信里的网址打开了那个网页,大致浏览了一遍。
这是一个介绍各种神秘事物的网站,由一个遍布全球的会员俱乐部建立。当我在键盘上敲出那个神秘符号的英文单词,在网站内进行搜索后,立刻有一大堆信息涌到我的屏幕上。
我滑动鼠标浏览这些信息,一组图形紧紧地抓住了我的眼球——初看起来像是阿拉伯文字,又像是二进制的数码排列图。
这组图是由一个设在法国的公司粘贴上去的。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有需要的人尝试和外太空的生命进行沟通。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公司,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他们将客户的信息用二进制编程为一组信号,利用设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沙漠上的一个天线向外太空发射。每组信号的长度大约三十秒,客人根据发射的次数付费。他们在网站上解释,那组图形是他们的接收系统于2002年6月的一天接收到的,至今仍无法破解。而且也不能确定它是来自外太空的哪个地方,抑或是电离层反射地球上某个地方发出的信号,也有可能是人类的恶作剧。
刻在树上的六个图形并没有出现在那组图中,但已经很接近了。
难道,Helen他们遇到了外太空人?
想到这里,连我自己都笑起来了。虽然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仍愿意相信那是地球上的某些好事分子的恶作剧。据资料显示,每年关于外太空生命存在证据的报告有几万个,但是造假率高达88%,还有10%是误判。只有不到2%具有研究和跟踪观察的价值。
当然,应该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同类生物之间保持着某种联络。在神秘的神农架原始森林中的那些可怕而能量巨大的神秘力量,也许在地球的某个角落还存在着同伴,它们之间互传信息,保持联络。这些理论早已被广泛接受,不过要让我将野人和以符号互传信息的高级生命联系在一起,我还是有些抗拒。
现在是凌晨三点多,我必须立刻回到看片室去。有多不胜数的谜团有待从那些还没有观看过的录像带中找到答案。
我小心翼翼地按下播放的按键,唯恐再次出现雪花噪波。还好,画面清晰如常。我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好奇,忍不住冒险将录像带倒回到刚才出现噪波的地方重新播放了一遍——这一次居然没有出现刚才的噪波!
虽然这种现象在录像系统时常出现——比如此刻走过录像磁头的磁带,上面的磁粉脱落将磁头糊住,下一段磁带可能就充当了抹布的功能,将磁头又擦洗了一遍,被擦洗干净的磁头当然也就可以播放出正常画面了——可我仍觉得有些不对劲,背后不禁冒出一层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