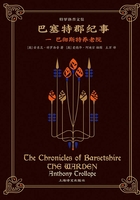立过功,戴过花,得过奖,人人夸,县城谁不知道刘小丫。并非刘小丫有多大的名气,实在是这个蛤蟆腚县城太小太小,蛤蟆撒泡尿,眨眼功夫城东冲到城西。有谁上了回电视,大街小巷第二天一准言论纷纷,何况刘小丫上了不止一回电视呢。
刘小丫是县小化肥厂工人,最后一批下放知青,最后一批招工回城。刘小丫回城,本来是可以进梆子剧团的。因为小丫的基本条件不错,先不说她那极标准的三围,极富东方女性之美的瓜子脸、樱桃嘴、丹凤眼,单就她那极富磁性魅力的先天性女高音嗓门,就把剧团的头头脑脑震住了。可惜,当时县梆子剧团正在被砍掉的风雨飘摇之中,自身难保,怎敢再冒昧招人。刘小丫没当成演员,本来还可以去做广播员,因为小丫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可是,一切测试完毕,刘小丫却以最高分而未被录用。追起原因,说是小丫有诱发性鼻炎。刘小丫对这样的解释很有些想不通,所以每当晚上看电视,一到地方新闻栏目,心头隐隐的不平,特别是听到播音员那拗口的土洋结合标准语,就气不打一处来,“啪”地换了频道。
刘小丫最后进了化肥厂,先是开票据,很轻松干净的活儿。可是,先天的身体条件常常招来麻烦,刘小丫干了不到一年就自愿申请到了装卸组。装卸组本是傻大粗憨之类聚集的地方,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临时工或者季节工,突然来了个如此光彩照人的尤物,仿佛给组里打了一针兴奋剂。打架的不打了,醉酒的不醉了,平时最爱出问题的部门一下子安静起来。月月超额完成任务,任务完成的好,奖金拿的就多,装卸组的大老爷们开始注意自己的内心和外表装饰了。这变化很使厂长莫名其妙。一连几年,刘小丫都被评为先进、劳模。后来刘小丫和厂里的销售科长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些身外的荣誉少了些,但以往的名声还在,厂里厂外,只要一提刘小丫,口碑还是不错。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时光轮回也许是太快了些,哪等到三十年呢,化肥厂因为污染问题,一夜之间被勒令关闭了。销售科长去了海南,下岗的刘小丫只好在街角开了一间花店。不是小城人的消费意识滞后,实在是小城人兜里没钱。刘小丫的花店生意并不怎么好。每天起个大早去城东十里外的个体户花农的花圃里取花,登自行车来回二十几里,少不了淌几身汗。买花的大多数是年轻人或是中学生。照刘小丫的想法,买花的人都是一些有情趣的人,不忍心在他们身上宰黑钱。再说,这么清淡的生意,还得想着拴几个回头客呢!那花价因此格外的平稳偏低,从不敢乱涨乱要的。半年前,销售科长在海南发了小财养了小蜜,提出给十万元要和刘小丫离婚,刘小丫哭了一场,十万元没要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厂里下岗的男男女女骂刘小丫傻货。实在是便宜了那个负心贼!想当初,厂子里追小丫的不下于一个加强连,可硬是让那个尖白脸捡了个便宜。刘小丫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她说,人都没有了,还要钱干什么!刘小丫就是这么一个散淡的人。
有钱的时候没觉得钱重要,没钱的时候才觉得离了钱不行。离婚后,一对龙凤双胞胎,儿子去了海南,女儿留在身边。女儿已上了初中,要吃要穿加上学费开支不少,刘小丫一个花店养活母女俩,紧紧巴巴,就想着在花店里再加上半边书架,以卖书为主卖花为辅,书和花都是上层次的正经人所需要的。
县城里的书店已经不少,刘小丫认真考察了一遍,心中有底,决定要办一个特色书店。她看到各家书店都是鱼龙混杂花花绿绿,她想办一个精品书屋。她的老同学在县图书馆搞采购,她让老同学为她开了一张书单,她准备办好执照就去先进一部分书试试行情。
跑执照很不容易,她几乎是碰了一鼻子灰。借贷款也不顺利,因为没有人为她担保。那一刻,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她沮丧地坐在工行巨大的玻璃门前的台阶上,心灰意冷。有一束落日的余辉穿过楼群的空隙撒在了玻璃上,玻璃的反光将门前的水泥电线杆照成一抹胭脂红,就在那抹胭脂红里,刘小丫发现了一则广告:市工业总公司招聘下岗商嫂。这消息对刘小丫有着很大的诱惑。刘小丫本来就是市里下放的知青,因为成家立业在县城,也就死了回市的心,可是现在家也没有了,业也没了,若能招回去,岂不了却半生的心愿。截止日期就在今天,刘小丫不敢耽搁,回家取了自己的身份证和各种资料,就按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邮电宾馆五楼508室。
508室的外面,是刘小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场景。来招商嫂的竟是当年一同下乡的知青启军。当年的启军能歌善舞,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刘小丫和启军一同扛锄下地简直就是乡间一道迷人的风景。村里的婆娘都说,这俩人真是天造的一双地设的一对。刘小丫心里对启军的感觉也是热辣辣的甜丝丝的,就是通俗歌曲里唱的那种“爱在心头口难开”吧。可启军那时太单纯,挺拔得像株未经风雨的小白杨。虽然也喜欢刘小丫美丽动人的歌喉,但离谈情说爱还差十万八千里。最放肆的一次是收工回家,走在铺满落日余辉的田野里说过一句,小丫,你看咱俩个头一般高,声音一样美,还真怪般配的。可惜刘小丫没有接上话茬,只是心头忽地一热。启军以为小丫不高兴了,伸出舌头做个鬼脸,故事便到此结束。不久启军参军入伍到了北京,刘小丫过了两年也回城当了工人。二人从此天各一方。一别竟是二十年。
二十年将启军从部队送往大学;又从大学送往深圳。如今,启军是沿海地区支持内地的建设回乡投资的大老板,闪亮的双眸掩饰不住成功的喜悦,翩翩风度无言地展示着顺达的旅程。“小丫”,是启军先认出了依然年轻的刘小丫,而刘小丫却呆了半天才认出启军。拿着在报名处填好的登记表,刘小丫张口结舌,找不出久别重逢的言语。
“小丫,你怎么了,我是启军啊!”启军从沙发上走过来,双手抓住刘小丫,用力地摇晃着,“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你是阔了还是咋着,还是我变丑了,变老了,你就这么看着我发呆?”启军牵着小丫的手,拉到沙发边上一同坐下,“说说看,你这些年都干些什么?”
“二十年,一言难尽……”刘小丫仅仅吐出这几个字,便一发不可收的泪如雨下了。
“好了好了!既然一言难尽,那就先别说了,今天我不走,咱先吃饭,然后来个彻夜长谈!”启军一手握着小丫的手,一手轻轻拍着小丫的肩,就像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男人的大手毕竟是有力的啊,刘小丫一时间竟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晚餐就在启军住的套房里举行。墨绿的落地窗帘,玫瑰红的阿拉伯地毯,圆柱型的双人小餐桌上,一枝粉红的蜡烛正在悠悠地燃烧,蛋黄色的烛光里,一枝怒放的玫瑰插在一个造型精美的细颈花瓶上。镂刻着天使圣母玛利亚的墙壁上挂着一只硕大的花篮,红玫瑰、红玫瑰,满墙满地都是灼灼怒放的红玫瑰。
刘小丫一走进这宽敞优雅、颇有些华光宝气的套房就有些愣住了。虽然当了多年的劳模,但终究是个小工人。一点也不知道蛤蟆腚大的小城还有如此梦幻般的去处。她原想老同学留吃饭,大不了是找个饭店酒馆之类嘬一顿而已,却不知会被带到这样一个住所。她沉默惊愕了片刻,便说,“怕是我女儿放学找不到我了。”
“放心,我安排好了!”启军拍拍小丫让座。“你的情况,我刚才已经从工业局长那里都知道了,你吃了很多苦!”启军用力地挽住小丫的手。深切的同情和关爱就从这手与手的接触中传递过来。刘小丫心中倾刻间就如打翻了五味瓶。有舒缓悠长凄美的乐曲从墙角的音响里传出来,是周冰倩那首脍炙人口的“真的好想你”。启军放下已开瓶的茅台酒,忍不住和着乐曲轻声哼唱……我在夜里呼唤黎明,天上的星星哟,也知道我的心,我心里只有你……刘小丫早已无心跟着潮流唱这些时髦的流行曲了,可是此时此刻此景此境,竟也勾起了她沉淀心底已久的莫名忧伤的怀旧,也轻轻地跟着启军和起了节拍。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烛光里,两双明亮的眼睛都逐渐湿润起来。喝茅台酒对刘小丫来说,是今生头一遭,“这是不是有些太破费?”刘小丫握着酒杯,心里不安地问。
“这样的破费我二十年才难得一次,小丫,你太苦了,太落伍了!”启军又一次握住了小丫依旧白皙的双手。
“厂子倒闭了,我卖多少枝花才能赚到这一瓶酒钱啊!”小丫摸着那仿古的酒瓶,脸蛋泛出少有的浅红。
“小丫,今生又能与你重逢,说明咱俩还是有缘,既然有缘,我就有责任呵护你!”启军的话还没落音,小丫就夺过酒瓶连倒三杯,一气喝光,扬了扬空杯子说,“启军,在我困难的时刻,感谢老天送来了你,如此地安慰我,叫我怎么消受!”
“小丫,别说这种话,要不是当时我太小、不开窍,你不会是今天这个样!”说着启军摔了酒杯,换了茶杯,斟满了酒,指天发誓说,“有我启军在,从今不让你卖花!不让你受伤害!若有食言,就如这撞碎的酒杯!”小丫一听,连忙伸出手捂住了启军胡言乱语的嘴:“混说,二十年见一面,尽说些不吉利的,这些年不见,你不了解我,不卖花,我还能干些什么?”
“这你不必担心,我深圳有电脑公司,你可以去做业务员,你也可以去给我管账,做公关,什么都不做也行,我尽管养着你!”启军一口喝下了一茶杯,到底是见着醉意了。朦胧的醉眼里,他看见面前的刘小丫一句话不说,只顾低头喝酒,那样子极是羞涩,极是优雅,极是温顺柔弱叫人怜惜,依旧是那双迷人的丹凤眼,依旧是那张白皙的瓜籽脸,偶而可见的几缕细皱,不仅没有带来青春易逝的感觉,相反倒增添了几分成熟的魅力和风韵。启军的心里像张开了许多忽扇忽扇的小翅膀。那些小翅膀紧紧地把刘小丫包围了。
下岗几年来,刘小丫独立支撑着母女俩生存的这片天,吃过苦,受过累,挨过白眼。离婚的日子里,也曾瞬间有过寻短见的念头,可是转眼又被自己否定了。一个散淡的人,总觉得孬好都得活着,只有活着才是真实的,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几年来看惯了风来雨去的人情冷暖,早已心如止水。可今天,消失二十年的启军突然如此近距离地出现在身边,使她想起了小白脸男人和自己失败的婚姻。满心的委屈打开了她尘封已久的内心世界,于是那些迟到二十年的话题,便似滚滚江涛止不住地奔涌而出了。
刘小丫一度被自己强烈的倾吐欲和坦露无遗的直白所惊吓,启军更被刘小丫火热的初恋情怀、朦胧而美妙的少女情结所陶醉、感动,二人恨不能就此悄悄死去明早再光明正大重生一回。圆桌上的蜡烛已流完最后一滴粉泪,桌上的酒瓶空可见底,二人不再点燃新烛,只是挽着手靠在桌边的沙发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话。二十年彼此经历太多,那话题也像新雨后的山间小溪,汩汩流淌不停。小丫早已醉意朦胧,免不了经常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若得启军呵呵地笑,笑着笑着就问:“那时在乡下,村里人都说咱俩挺般配,我心里恣得很,不敢问你,今天敢问你了,是不是这样?”“敢情你有钱胆就大了,这话当年咋就不问我,我也不生气,为什么偏偏就现在来问我,看我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落井下石是不是?”刘小丫心头百感交集,忍不住就轻声呜咽了。
“小丫!”启军轻声呼喊着,双手无声地揽过小丫依旧纤细的腰肢。小丫的眼泪更加汪洋恣肆了,伸出双手不停地捶打着启军宽大的肩膀。一股股热流在启军的胸膛里翻涌,启军忍不住就把刘小丫紧紧地拥在怀里。刘小丫依旧呜咽,并不停地说着醉话“我恨你,我恨你,”说着说着恨字变成了“爱”字,泡在商海多年的启军被这早已流逝的情愫之火熊熊燃烧了。面对着面前刘小丫眼泪纵横流淌的面孔,启军用自己火热的舌头堵住了刘小丫梦幻般的呓语。他们彼此相拥,身心得到了慰藉,将来明天等等,全都抛到了脑后,只有昨天,只有过去,只有相亲相依相恋相戚,只有此时此刻。
毫无功利的异性结合是如此的美妙,少女的初恋情怀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终于得以释放,巅峰过后的启军安然地睡去了。浑身舒散松软的刘小丫却从沉沉的酒意和浓浓的爱意中醒来。掀开窗帘朝外看,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紫色的壁灯似有似无地亮着,满屋的玫瑰花在暗处悄悄地散发着一缕缕淡香。刘小丫忍不住就想起了自己那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起来的花屋。她心头一紧,才看清了自己只穿了一件三角短裤,才发现了酣睡的启军。启军依旧是漂亮年轻,孩子般的圆脸上嵌着两只活泼的酒窝。健壮的肌体,成团的腱子肉,依旧是一株挺拔的小白杨。
刘小丫跪在地毯上,就像当年慈爱地看着自己一双龙凤小儿女一样地观望着启军,想起他对自己的真诚许诺,对自己的深情关心呵护,还有那男子汉的阳刚细腻的力度,忍不住就在心底默默地念叨:天命!谁让我在二十年前错过你呢?念叨完了,流几滴清泪,爬起来穿了衣服,收拾起自己昨晚带来的资料,那里面有她历年的劳动模范、先进个人证书、奖章,什么都没有了,唯有这些个不能丢!这是她多年在岗的唯一收获。刘小丫细致地查对、包裹好那些心中的无价之宝,悄悄地掩上门,不告而辞了。
小城工业不发达,因此污染不严重。黎明的空气依旧很清新。刘小丫走在空气清新的马路上,用力地咳了几声吐出一夜的酒气和浊气,顿觉沉重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她知道女儿上学从来不用催,她不想立刻回家,她想赶到花店推自行车,去城东花圃还来得及,她要早一点把花取回来,她知道,那些买花的年轻人喜欢撒满露珠的鲜花。
原载山西《漳河水》
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