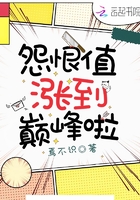洞源村口有座名唤经堂山的山头。此山不高,山脚下有一座小小庵堂,名灵瑞庵。庵堂内供着的送子观音像传说是朱球母亲的化身。善男信女到这里求神拜佛或居住,不但能求子得子,求孙得孙,而且还能消灾驱邪、强身健体。因此,许多人到这里来求子求孙、消灾避难。
传说大清道光年间(1821—1850),兰溪城内有一家小杂货店,店铺的主人名叫韩荣坤,妻子祝氏。夫妻二人年过半百没有儿子,单生一个闺女,乳名玉琴,年方一十六岁,生得美丽聪慧,举止文雅,孤高倔强,只是多愁善感,体弱多病。听说洞源灵瑞庵能消灾驱邪、强身健体,夫妻俩就商量把女儿寄送到灵瑞庵中疗养身体。
这年正月过了元宵,他们准备了香纸蜡烛到了灵瑞庵。庵中住着一老一小两个尼姑,她们见有香客到来,连忙出来把他们迎进庵内就坐。
小尼送过茶后,老尼问道:“不知三位施主到庵堂来烧香许愿,还是避难消灾?”
韩荣坤道:“只因小女从小体弱多病,百医不愈,听说这庵内能驱邪消灾,故而前来烦扰老师父了。”
老尼道:“施主何出此言,出家之人慈悲为杯,小姐不嫌小庵狭窄,老尼安排房间让她住下就是。”
说罢,就命小尼敲钟击鼓,陪他们拜过送子观音及其他菩萨。韩荣坤夫妻捐一些银两给庵堂后,便告辞回家。
就这样,玉琴姑娘在灵瑞庵内住了下来。从那日开始,玉琴在老尼的安排下,定时起床、定时休息、定时吃药、定时用餐,并要她做一些抹桌扫地、焚香拜佛之事。除此而外,还教她念枟受生度亡经枠、枟安邦天宝篆枠和枟劝修功卷枠等经卷。不到半年,玉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面带红润,美貌非凡。在这半年中,她的父母每隔十天半月都要到灵瑞庵来看望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每次都为女儿准备许多好吃的东西,见女儿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深深地感谢老尼对女儿的调养。老两口怀着这样一个心愿,等女儿康复回家,为她选择一个好女婿,让他们有个半世之靠。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一场厄运降落在这善良之家。
却说兰溪城中有个花花太岁,姓张名绪,乃是兰溪知县童锡明的妻舅。童锡明是兰溪城关人,本是个浮滑少年,家中并不富有,他到了二十岁时,却生得长身玉立、仪表非凡,博得兰城富翁张维生的青睐。这张维生为富不仁,家财万贯,却刻薄成性,膝下有一女一子。女儿名叫素娥,当时一十八岁,长得有几分姿色,可是年纪不大,私欲很重,尚未出阁就考虑着要帮夫成家。儿子张绪,小素娥十岁,却生得獐头鼠目,丑陋猥琐。妻子生下这个儿子不久就命归黄泉,父子三人相依为命。
近几年来,张维生感到身体欠佳,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眼看这样的儿子日后难成大器,因此一心想寻访一个有能耐的青年来做他的女婿,见童锡明精明能干、能说善道,就决定将女儿许配于他。
可是女儿素娥嫌童锡明家贫穷,不肯下嫁。张维生一则爱女心切,二则喜欢锡明,答应她如能听从父命,就把自家存在金号钱庄的几十万两金银存款全部由她带去。有了这许多金银做嫁妆,应该心满意足的了,可是素娥到了上花轿时,还是一百二十个不情愿,在闺房中只是痛哭,不肯上轿。父亲急得手足无措,进房来问她究竟还有什么不如意,因何不肯上轿。
女儿拭着眼泪,徐徐地道:“非是女儿不愿出嫁,既然爹爹做主的事,女儿岂敢违背?可是女儿嫁了过去,夫君是个白衣,没有一点势力和地位,钱再多有什么用?到时还得依附别人,照样要受人家欺负。女儿横思竖想,还是在爹爹跟前省事,不需我操心。”
张维生一听,原来她不肯上轿的原应,就是怕没有势力和地位受人家欺负,于是笑着道:“女儿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父几十万资产都给你了,还何惜这点小钱,等你过门之后,待为父再取三五万两银子,替女婿捐一个现任官员来就是了。”
素娥听了,这才转涕为笑道:“爹爹你要言而有信,不得反悔,这样女儿就可安心嫁到童家了。”说着,就欢欢喜喜地上轿去了。
童锡明凭空得了这么多的妻财,心中得意自不必说,对妻子的一言一行,不敢有半点违反,言听计从,妻子指东,他不敢向西。张素娥自幼在家过惯了如意日子,娇养已惯,稍不称心即大呼大骂,好在童锡明是个奴隶生性,只要日子过得快活,一切都能接受,心甘情愿做这种妆台奴,把妻子捧上了天。家中的一切事情,都由妻子做主,就是童锡明外出有事,没有妻子的同意,也不敢乱走一步。
丈夫这样顺从于她,可是没有权势,素娥还是看不起他,天天回家要父亲信守诺言,为丈夫捐官。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不久张维生果然花了三万两银子,给女婿捐了一个厘金局长,分发在浙江省内。
童锡明得了个现任厘金局长,风光了一时,可是过了一年,素娥嫌厘金局长官微,要父亲再出资,替丈夫捐个正印官来。钱能通神,两年后,她的父亲真的为童锡明捐来一个正印知县,省内挂牌,而且任于兰溪县。
不久张素娥的父亲去世,儿子张绪由于溺爱过度,不学无术,整天混迹妓院烟馆,十五六岁就知道嫖妓宿娼,父亲一死,不能独立生活,只得前来依靠姐夫姐姐。童知县深知,没有张家就没有他的一切,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小舅子到来。夫人张素娥一定要丈夫为张绪安排一个好差使,童知县觉得小舅子胸无点墨,无事可干,但又不敢违抗夫人的“圣旨”,只得安排他一个管理差役的差使。
童夫人只生过一个女儿,医生说她再也不能生育,所以她把弟弟当成儿子看待,对他溺爱无比,百依百顺,比孝顺父母还要周到几分。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弟弟中意,她就是花再多的钱也甘心情愿。童锡明有时看不惯说了一言半句,夫人就大发雷霆,骂他忘本、白眼狼,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童锡明也毫无办法,只好对小舅子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把这个张绪纵容得无恶不作,成了兰城出名的恶少、花花太岁。
这年过了端阳佳节,张绪玩厌了城中的花花世界,想到六洞山来避暑游玩。这天,他带着两个公差,以催讨钱粮为名前往六洞山而来。当他们路过灵瑞庵时,见这庵堂虽小,却十分清洁、幽静,暗想,这庵堂如此幽雅,莫非有绝色尼姑不成?就和两个公差进入庵堂窥探。
老尼突然见进来三个公差打扮之人,吃了一惊,问道:“庵堂静地,不知三位上差到我庵堂何事?”
张绪油腔滑调地说:“我们奉县太爷之命查户口,不知此庵有多少尼僧,叫她们出来,让我们查一查。”
老尼道:“小小庵堂,香火不旺,哪里养得起多少尼僧,只有我师徒二人在这里虚度光阴。”
张绪道:“既然还有一个徒弟,何不叫她过来让我看看。”
老尼不敢怠慢,忙到厨房叫小尼捧了三杯茶上来,请他们到庙堂喝茶。
张绪见小尼生得相貌平凡,感到失望,满以为如此雅静之处,定有好芳草出现,谁知出来的却是一个丑八怪,十分扫兴,茶也不想喝了。正站起来想要走,忽听一间房内传出黄莺般的声音道:“师父,鞋底已纳好,还有什么事情要做?”这又清又脆又柔又媚好似百灵鸟般的声音,把这个好色的花花太岁张绪喜得灵魂飞上了半天,睁着一双色眼盯着房门不放。
只听得门开声响处,人未出现,就隐隐露出了一只穿着大红绣花纱鞋、月白罗袜,小仅三寸,尖如菱角,胜似水红鞭儿样的一钩莲瓣,跨出在房门外。把张绪看得目眩神驰,心猿意马,忙顺着这钩莲瓣往上望去,见一个体态轻盈、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出现在面前。张绪睁大眼睛看着,只见她生着一张鹅蛋般的面庞,两道青山样的细眉,樱桃小嘴,不点而翠,鼻如悬胆,牙排碎玉,秋水媚眼,闪动生辉,杨柳细腰迎风摆,莲瓣金莲贴地行,说不尽的风流,道不完的妩媚,宛如西子洛神再世,像似南海观音下凡。
张绪暗想,在兰溪城中从未见过这般绝色女子,莫非是九天仙女下凡不成?看得他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呆呆地怔在那里。刚才玉琴在房中帮助老尼纳鞋底,纳好后,出来问老尼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忽然见三个公差打扮的陌生男人坐在殿堂之上,一个獐头鼠目的年轻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吃了一惊,连忙退回房中。
这两个公差瞧出张绪已着了这女子的迷,便对他献计道:“大爷你如果看中这女子,何不借查户口为名到她房中,我俩帮你守住房门,料她们这一老一小两个尼姑奈何不了我们。再说,我们看这小女子面带桃红,眼含秋水,正值青春年少之期,俗话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像大爷你这样有财有势的人物,只要说出你的名来,可能她就把持不定主动就范了。”
张绪听他们说得有理,朝他俩一笑,便闯进房中。玉琴见这人突然闯进房来,大惊失色,大声喝道:“男女授受不亲。你是何人,为何入奴家的房间?”
张绪随手关好房门,无耻地道:“在下张绪,兰溪知县童锡明是吾姐夫,今天奉命下乡检查户口,路过此庵堂,偶见小娘子如此标致,令人心痒难熬,望小娘子赐吾片刻之欢,吾就是为你做牛做马也甘心情愿。”说着,就对玉琴动手动脚起来。
玉琴见这人如此无理,恼恨交加,柳眉倒竖,高声骂道:“大胆狂徒,竟敢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奴家,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张绪哈哈笑道;“王法,什么是王法,我就是执行王法的人!我玩弄一个女子,谁人敢来管我,今天偶然相遇,想必是天赐良缘,岂可错过。”说罢,就上前搂抱玉琴。
玉琴羞愤交加,朝他脸啐了一口,急急想开房门夺门而逃。谁知房门却被他们反锁,无法打开,张绪趁机一把抱住玉琴,急得玉琴“救命,救命”地大叫起来。老尼听到玉琴的叫声,知道不对,连忙赶来相救。两个公差见拦阻不住,用力一推,老尼站立不住,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五六步,脚下一软,“嘭”地一响,后脑正好碰到石门槛上,鲜血直流。可怜这位善良的老尼,为救玉琴无缘无故死在这班恶人之手。
在房中,张绪把玉琴按在床上强行解她的衣服,玉琴拼命挣扎呼叫,不见有人前来救援,知道自己厄运已到,清白之身岂肯失节,不如以死殉节,以保清白之身。于是她伸出右手,从桌上抢过切鞋底的刀,朝自己的脖上一抹,一道鲜血像报复般地直射张绪,把这个无法无天的恶少吓得软作一团,浑身颤抖,忙脱掉血衣,丢在一旁,带着两个公差逃之夭夭。
这件事被躲在厨房里的小尼看得一清二楚,见他们仓皇逃走,忙来到庙堂,见师父和玉琴都已丧命,欲哭无泪,急忙赶到洞源,报于乡绅章邦杰。
这章邦杰是当时洞源最有声誉的乡绅,他一向维护正义,爱打抱不平,并且有个受道光爷青睐、林则徐大人重视、现任江苏常州知府的内侄章开璐,因此,他在本地有相当的威信,村中有许多疑难之事都要请他解决。只要他同意出面,就没有处理不好的事情。他听完小尼姑的诉说,立即带了几个人赶到现场,当看到这样的惨剧时,吃惊不小,说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哪有无辜屈死两条人命之理!此事出现洞源境内,我非管不可。”
他来到玉琴房中,见房门口丢着一件血衣,捡起一看,是一件公差的衣服,就对大家说:“这件血衣是最好的见证。我们就将它作证据吧。”于是,他一面派人通知玉琴的父母韩荣坤夫妇,一面请人写下状子准备告状。
韩荣坤夫妇听到这一噩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灵瑞庵,一见女儿果然惨死,玉琴的母亲疯了一般,抱着女儿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那些闻信赶来的群众,无一个不下泪。
章邦杰含泪劝他们说:“二位不要过度悲伤,人死不能复生,你家有此烈女,不辱你的门庭。现在首要的事情就是尽快向衙门伸冤,替你女儿报仇,决不让你女儿冤沉海底。”
韩荣坤哭着道:“大爷,现在我们夫妻二人方寸已乱,不知如何是好,一切事情只能请大爷为我们做主了。”
章邦杰毫不犹豫地道:“由我做主,暂且将你女儿停尸在庵堂之内,着人看护。现已请人写状,明日由我带你们去衙门告状。”韩荣坤深深拜谢。
第二天,章邦杰清早起身,带着血衣,和韩荣坤等人来到兰溪县衙前等候。不一会,兰溪县知县童锡明击鼓坐堂,章邦杰就叫韩荣坤进衙叫冤。衙役将韩荣坤带到堂上,跪在下面。童锡明往下一看,见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前来喊冤,便把惊堂木一拍,喝问他是什么姓名后,就喝道:“韩荣坤,有何冤枉当堂诉来。”
韩荣坤泪流满面地将女儿玉琴到灵瑞庵中驱邪消灾,昨天被县衙派去催讨钱粮的三个公差逼死庵堂的事诉说了一遍。童知县一听,感到奇怪,暗想,昨天县衙根本没有派人到洞源去催讨钱粮,莫非有人冒名顶替不成?便问韩荣坤可有状子、物证,韩荣坤忙把状子连同血衣呈了上去,童知县接过血衣一看,大吃一惊,这件血衣分明是他小舅子的衣服,暗暗说道:“这个畜生,难道这事是他所为不成?呆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章邦杰看这童知县的表情,觉得有点蹊跷,知道这作案之人有点来头,就出庭诉道:“启禀大老爷,此案情节严重,关系到两条人命,请大老爷在现实面前不可犹豫,速速下令捉拿案犯到庭对质,决不可让两名死者冤沉海底,望大老爷明断。”这几句刚肠嫉恶的壮语,让这个怀有亏心的童知县吓了一跳,暗想,一个乡巴佬竟有如此水平,定睛一看,吃惊非小,我道是谁,原来就是他。
章邦杰的威信,童知县早有耳闻,知道他向来做事老成持重,为人圆滑老到,洞源村的人对他奉若神明,有什么交涉之事都请他来做公判,又有章开璐这块金字招牌,就是兰溪县城内各级官员、大小绅士,也得让他三分。他一旦出面,这事就不可含糊了事,不管谁是谁非,都要秉公办理,若有包庇袒护,他必然要与你争执到底。自己虽是一县之主,但实力没有他强,一旦被他上访,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怎样,保自身要紧。
正要拿起令牌,命衙役捉拿案犯到庭,忽地大堂后走出一人,喝道:“且慢!”众衙役抬头一看,都吃一惊,出来的不是别人,便是童知县的夫人张素娥。
这童知县是个有名的“气管炎”,怕老婆的大元帅。每次坐堂审案,都得由夫人做一半主。众衙役正待接令,忽听到这声“且慢”,谁还敢不听吩咐,立即站于原处不动声色。
童锡明坐在堂上忽见夫人出来,连忙下座,笑着问张氏道:“夫人有何吩咐?”
张氏劈头道:“审什么官司,家中快要死人了,还不进去看看。”
童锡明一听,吃了一惊,心想,难道女儿得病不成?忙吩咐衙役暂且收庭,明日再审。衙役们答应,叫章邦杰等人退下,童锡明随着张氏进入后堂,问张氏何人得了重病。
张氏道:“你自己到内室去,即便知道。”
童锡明怀着疑惑的心情,走进内室一看,见小舅子张绪哭丧着脸倒在椅子上。
原来张绪昨天在洞源灵瑞庵逼死人命后,不敢回家,和两个公差逃出洞源后,就分道而行。他当天一人到了金华,在金华住了一夜,在宿店中,总觉得心宁不定,也无心去寻欢作乐,闷闷不乐地躺在房中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他的那件血衣还丢在灵瑞庵中,心上不免猛然一惊,只怪自己粗心大意,当时没有把它毁掉,倘若被他们拿去,这是最好的证据。明天死者的家属,定要拿着这件血衣去县衙告状起诉,这案件自然落在我姐夫之手,可是我姐夫软弱无能,并对我还有些成见,他若为保自己的乌纱,准了状子,我必死无疑。这事还需回去与姐姐说明,托姐姐阻止姐夫不收状子,方才妥当。于是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起身赶回兰城。
可是未到县衙,就听到章邦杰等人已进衙门告状,姐夫收了他们的状子。他知道章邦杰这人是不好惹的,姐夫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姐夫下令追捕于我,到那个时候就没有调和余地,一旦被捉拿归案,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己还能活得成吗?此事非得与姐姐商议,由她出面才能挽回局面,好在姐姐素来疼爱自己,她总不忍心看着我死于非命。
想定主意,忙走进了后衙,见张氏坐在客堂之内,上前在张氏面前跪下,哭着道:“姐姐,小弟闯下了大祸,要姐姐救我,不然小弟我就死定了。”
张氏见弟弟如此狼狈,不知出了什么事,忙扶起他道:“好兄弟,为何这般惶恐,发生什么大事,对姐姐说来。”
张绪站起,立在一边,把他昨天在洞源灵瑞庵内,怎样看中韩玉琴,又怎样调戏她,欲奸不成逼死人命的事,细细向张氏说了。
张氏听毕,也不由得大吃一惊,沉吟道:“这事可真大了,你这活畜生,在城中闹闹已够了,怎的还要闹到乡下去!”
张绪又跪地哀求道:“此事非得姐姐与姐夫相救,不然,小弟要抵那姑娘的命了。”说着抱着张氏的双腿,痛哭不息。
这张氏本就非常溺爱张绪,今天见他哭得可怜,异常心疼。扶起他道:“你也不要过于着急,只要有为姐在,定会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安然无事的。你来得还算及时,姐夫他正在审理此案,如果他准了状子,下令追捕,这事就麻烦了,现在我即刻前去阻令,再请师爷前来设法救你就是。”张绪听了姐姐的话方放下心来,坐在内室,装着哭脸,等候姐夫童锡明。
却说张氏一面安慰好张绪,一面急急忙忙地来到大堂,见童锡明刚要发令捉拿案犯,为了弟弟,她竟做出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来,当众阻拦了丈夫的令牌,冒昧说家中快要死人。
童锡明见到小舅子,心中已知其意,但他还是明知故问地问张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张氏就把张绪逼死韩玉琴的事对童锡明详细地说了一遍。童锡明听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呆呆地看着张绪说道:“不出我所料,果然是你所为。有道是: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般重大的刑事,我怎好置之不理?若被上司知情查问,我定自身难保。”说着连连摇头叹息。
张绪听姐夫这样一说,急得倒在椅上大哭起来。张氏见了,怒容满面地对童锡明道:“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你可知我张家只有这根独苗,就这样眼睁睁让他去抵罪不成?你应该拍拍胸膛想一想,你的家资哪里来的?你的前程又是哪里来的?你总不能丢掉青竹棍,忘了讨饭时。身为一个七品知县,难道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童锡明道:“夫人,你说哪里话来,我岂有不想救小舅子之理!可是人证、物证俱全,又有兰溪名士章邦杰出首干涉,我怎能包庇得下?”
张氏道:“这个我自然明白,但当今世界,只要有钱,无论多重大的案件都可摆平,重的能够变轻,轻的可以安然无恙。权力在你手中,你就不能想出一个减轻罪状的法子来吗?”
童锡明道:“我现在心乱如麻,哪里想得出什么法子来。”
张氏见他确实无能为力,只好说道:“既然你无法解救,那就把师爷请来,和他商议,只要他能救我弟不死,就是多花点钱也是无所谓的。”
童锡明出于无奈,只得命人去把师爷请来。不多时,兰溪县衙的幕府师爷陈春林踱进内堂。这位师爷是绍兴人氏,为人鬼怪精灵、奸诈贪婪,并且诡计多端,和童锡明在兰溪县衙狼狈为奸。童锡明对他虽不十分信任,可是又少不了他,不论大小事情,都要与他商量。今天他知悉童锡明接到一件因奸不从逼死人命的大案,他估计这事可能就是童锡明的小舅子所为,也知道晚上童锡明必定要请他商议。正在暗暗思索用什么方法向他们索取钱财时,忽听得童锡明命人来请,便答应了一声,捧着旱烟袋,迈着方步踱将进来。见童锡明愁容满面,张绪眼泪未干,张氏夫人神色惊慌,就知道他们的内情,因此装着没事,坐在那里不言不语。
童锡明见他进来,忙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问他道:“师爷,刚才的案件,你看怎样处置?”
陈春林暗想,着咧!他果然问起我来了。就故作镇静地吸了口烟,皱了皱眉道:“老爷,这种案件,有何难审,听说人证、物证俱全,只要从这件血衣上着手,顺藤摸瓜地追查下去,定然能查出凶手。”
童锡明认为师爷还不知详情,这一番切合实际的行话,说得他无言可答。张绪又吓得泪流满面,张氏忍耐不住了,一把拖住陈春林道:“师爷,请你不要讲这些不中听的话了,今天我们请你目的是什么?你可知这凶手是谁?”
陈春林道:“夫人因何发怒,今天老爷叫我,是要和我商议这件案件。现在案件尚未审清,我如何知道凶手是谁呢?”
张氏指着张绪道:“师爷,这凶手不是别人,就是他所为。”
陈春林一听,假作惊讶地说道:“什么,这事是舅老爷所为!这? ?这可怎么办呢?”
张氏知他贪财,忙求着他说:“师爷,这件事情全仗你的大力了,只要你能想出个妙法,保得我弟不死,我当重谢于你。”说着,朝陈春林伸出两个指头。
陈春林一看,知道张氏是许他两千块大洋,心中虽然一动,但一想,一条人命只值两千大洋,太便宜了,就摇着头道:“这人命关天之事确实难办,我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
张绪一听,知他在卖关子,故弄玄虚,急着走到陈春林面前,哀求道:“师爷,你要救我一救,我自当另会给你这个数的。”说着,他又伸了一个指头。
陈春林一看又多了一千,心中一喜,但这个贪得无厌的绍兴师爷见还有一人没有表态,于是便对童锡明道:“老爷,不是不才想不出办法,只觉得这事非常难办。”
童锡明听他口气还要索钱,心中暗暗骂道,好一个贪心不足的老夫子,他的竹杠竟敲到我的头上来了,但碍于夫人的面要救小舅子,不得不破点私房钱了。忙向陈春林作揖道:“这事全仗师爷出力,下官自当有谢。”说着,也伸了一个指头。
陈春林见有四千大洋,暗想,这样也差不多了,自己随着童锡明这些年能赚多少?平时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把大把地将贿赂装入腰包,我从未得到过半点好处,今天有事求我,我不敲诈他还敲诈谁去?来他一个黑吃黑,也要从他的骨髓中榨点油出来,我已年过五旬,就要退职回家,等会给他出个馊主意,四千大洋一到手,就可回绍兴享福去了,以后即使有什么破绽露出、童锡明丢官,与我何干。越想心中越高兴,把那只旱烟袋吸个不停,熏得整个内堂烟雾弥漫、辛辣刺鼻。
张氏见他这样不紧不慢,早就不耐烦了,急着叫道:“师爷,怎么样呀,你究竟能不能想出个法子来?”
陈春林慢慢放下烟袋,慢条斯理地说道:“老爷,夫人,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人证、物证俱在,又有兰溪一流乡绅章邦杰参与此案,要想洗掉罪行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避重就轻的方法来减轻舅老爷的罪行。”
张氏急问道:“师爷,用什么办法可以避重就轻呢?”
春林道:“夫人,别慌,我且问你,现在是什么时候?”
张氏拿过皇历一看道:“今天是五月十九,再过几天就要小暑节气了,师爷,你问这个做什么?难道要减轻罪行,与气候也有关系吗?”
“对!要想卸掉舅老爷逼死人命之罪,这样的天气就有很大的帮助。”
听他这么一说,他们三个人都来了精神,但还不解其中之意,一齐围了上去问道:“师爷,卸罪和天气有什么相干呢?”
春林道:“我再问你们,这样的大热天,一个人死了几天不葬,尸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张氏抢着说:“这肯定有变化的,尸体要发胀,肚子要膨胀。”
“着咧!就是这个意思,”陈春林拍着桌子说道,“小暑前后,天气太热,人死了几天,尸体必定要膨胀起来,特别肚子发胀得最快。老爷你明天审案,说要下乡验尸,再用金钱买通仵作,说这女子已怀孕五月。你再审问舅老爷,舅老爷就一口承认韩玉琴与他通奸多时,由于身子有孕,到洞源灵瑞庵避嫌。这次你去灵瑞庵劝她把这胎儿打掉,她不肯就范,含羞自刎身亡。老爷你就假装大怒,说舅老爷是年轻不端,好色贪花,影响极坏,当众罚他几下板子,我再写一份供状,假意把他收监,把那两个推死老尼的公差判处极刑,这样不但减轻了舅老爷的罪行,而且在大众面前显示老爷你铁面无私、公正严明,这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吗?你们看如何?”
童锡明一听大喜道:“妙,妙。亏你这个老夫子,能想出这个办法来,就这样办吧。”
陈春林说:“慢!”
童锡明一愣道:“师爷,还有什么不妥当?”
陈春林道:“还有一事,老爷你必须再花些钱,对衙内的衙役、差人打点一下,封住他们的口,叫他们不要露出风声。”
童锡明道:“此事好办,只是下官不好亲自出面,还需师爷代劳。”春林道:“不妨,这事我替老爷效劳就是了。”
张氏听了问道:“不知要多少?”
春林算了算道:“不多,有一千块大洋就够了,但刚才说好许我的四千块,也就兑现了怎样?”
张氏为了保住弟弟的性命,只得忍痛取出四千块银票和一千块现洋,交给了陈春林。陈春林兴高采烈地接过银票和大洋,立马叫来一心腹衙役,和他两人把这些大洋分给了衙役和差人,叫他们如此这般办事。衙役和差人们收了贿赂,就欣然答应,照他的吩咐行事。不过他只分掉了八百块大洋,其余两百块进入了自己的腰包。
次日,章邦杰等人又到县衙喊冤,师爷传话,今天老爷下乡访查,衙门暂不理事,至于逼死人命之事,等验尸后再行定夺。章邦杰一听,觉得此事蹊跷,暗想,这样炎热的天气,应该把这事及早地了断为好。时间一长尸体就要腐烂发臭,知县他为什么偏要拖延时间呢?莫非其中有什么奥妙不成?百思不解地回到灵瑞庵,想与大家商议时,一个老妈走来对他说:“这姑娘的尸体停放在这里已有三天了,这样热的天气,再不及早处理,恐怕她的肚皮就要爆炸,你去看看,现在已胀得像鼓一样了,真可怜呀!”
章邦杰听她这么一说,心中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来,这正是知县的缓兵之计,天气炎热尸体停放数日,必然膨胀起来,而且肚子发胀得最快,他们验尸时就可说这女子平时不贞,因未婚怀有身孕而含羞自杀,这样就能替公差开脱罪责。
于是,他把这个推理和众人说了,大家认为这个推理完全准确,只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章邦杰沉思了一会道:“我有一个办法,大家去召集村里的中老年妇女,要她们各人准备菜刀一把,但要磨得锋利明亮,等明天县官来验尸时,大家装着来看热闹,把刀揣在怀中,不要动声色,看我的眼色行事。”大家虽然不知章邦杰是何用意,但素知他一向维护正义,足智多谋,喜打抱不平,加上激于义愤,就按照他的吩咐行事。
第二天,童锡明把仵作和接生婆秘密地请到内室,各给了他们一百块大洋,叫他们在验尸时只要如此这般做,大事成功后还有赏赐。仵作和接生婆接过大洋,点头应允。
随即,童知县带着三班衙役,及仵作、接生婆、书记等一行人,声势浩大地来到洞源。童知县在灵瑞庵内坐定,吩咐仵作开始验尸,仵作就装模作样地与接生婆验起尸来。灵瑞庵内外,看热闹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有几十个中老年妇女,各揣菜刀在庵堂外面等候。听里面的仵作和接生婆一唱一和地喊道:“头部,无伤。面部,无伤。颈上,有刀痕一道,长有两寸零两分,深为五分,喉管已断。”童知县喝道:“再往下验!”又听喊道:“臂上,无伤。胸部,无伤。腹部? ?”接生婆在女尸的肚子上按了一会喊道:“肚皮胀大,有五个月的身孕,可惜的是胎儿也已死亡。”
章邦杰一听恨恨地骂道:“该死的家伙,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朝大家丢了个眼色,只见几十个中老年妇女一齐从怀中抽出菜刀,高声喊道:“尔等验尸不公,胡说什么女尸腹中有孕,我等不信,若要验明真实,必须破腹,亲眼见到才得服众。”随着喊声大家一拥而上。童知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见进庵堂的全都是妇女,而且手中都握着雪亮的菜刀,有几个举刀对着女尸欲砍,衙役们拼命拦阻,这许多妇女的喊声犹如天崩地裂一般。
童知县见章邦杰横眉怒目,沉着坐镇,众妇女又是这般凶猛,慌得手足无措,想不到章邦杰已识破了他的阴谋,何况自己做贼心虚,如果真的被她们剖开肚皮,女尸腹中没有胎儿,按大清律例,错断命案,不是充军也要革职,哪里还敢和她们争执,连忙下位拖住章邦杰好言说道:“章绅士,请你阻止她们不可妄动,待本县回衙复审一干人犯,到时本县会传你等当堂对质,你等耐心等候。”说罢,就吩咐衙役起轿回衙。
谁知章邦杰等在家等了两日,不见任何动静,因天气炎热,尸体开始发臭。章邦杰知道童锡明故意拖延时间,他一面集资出钱买了二口棺木,把两具女尸入殓,一面写信派人赶往江苏常州,请章开璐想办法对付。不几天,前往常州的人员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把章开璐的一封书信交给了章邦杰。
章邦杰拆开看,信中言道:
叔父:来信已悉。深知案情重大,可惜小侄身居外省,家乡之事不宜过问,此案无权干涉。但我可向您提供一个消息,六月初,朝廷派遣浙江巡抚盛大人到浙中各地巡视,从衢州启程,听说乘船路过兰溪,到时您在江边等候,拦船告状。这位大人为官清正,又是小侄的宗师,他定然会为你们讨回公道。云云。
道光二十年五月廿五日,小侄开璐拜呈。
章邦杰一见书信,满心欢喜,派人每日沿江探听,如真有巡抚大人过境,立即报告于他,设法拦船告状。
且说这位盛大人原任衢州府知府,姓盛名国宗,任职以来为官清正,办事公道,铁面无私。他说话心直口快,做事雷厉风行,因此深得同僚敬重,大家叫他“盛大炮”,百姓都称他为“盛青天”。由于在禁烟、销烟中办事突出,深受朝廷重用,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命他到金华八县巡视禁毒之事。他选择了六月初三为黄道吉日,五更即起,不通知各县,秘密从衢州府启程,乘船前往金华。探听人得到这可靠消息后,立即报于章邦杰知道,章邦杰计算好时间,带着状子和章开璐的书信,与众人到城南马公滩等候。
六月初三这天下着小雨,满江雾露,经过一天的颠簸,盛巡抚感到有点困倦,坐在舱内闭目养神。官船通过横山,进入兰江,转头向婺江而上,快到马公滩时,朦胧中好像听到有年轻女子喊冤,声音十分凄凉。他感到奇怪,开出舱门,见江天一色,广阔的江面上愁云密布,惨雾茫茫,耳边隐隐约约似有女子哭泣之声。心想,难道这地方有什么冤情不成?问左右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左右道:“已到兰溪南门。”盛大人听说已到兰溪县城,吩咐手下挂起旌旗,鸣锣开道前进。手下不知就里,忙升起了旌旗,敲起了大锣。
不一会,在马公滩那边,忽然传来了众人喊冤叫屈的喊叫声。盛爷一听,果然有人喊冤,叫水手将船向岸边靠去。
中军出舱喝道:“你等是何方百姓,在江边拦截官船,骚扰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章邦杰忙跪地禀道:“中军大人,我们是兰溪洞源人氏,只因有天大冤情在身,无处上告,闻听得巡抚大人路过兰溪,因此我等斗胆拦船告状,望中军老爷恕罪。”
中军道:“既然告状,可有状子?”
章邦杰忙把诉状并章开璐的那封书信一并呈了上去,中军接过,呈于盛大人。大人首先拆开书信一看,笑道:“我道是谁透露消息,原来是他推荐我。既是他推荐,此事我不得不管。”说着就把状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拍案道:“小小兰溪,竟有这等事情发生,真是无法无天了。老夫暂且不去金华,首先把这案件弄他个水落石出,再作道理。”吩咐手下带章邦杰等告状之人,先到兰溪县府衙门等候,不要声张,然后命船工水手掉转船头,来到西门码头停泊。
下船后,盛大人坐了八人大轿,直到县衙。童锡明正在内堂和夫人商议此案如何结局,忽听巡抚大人突然到来,惊恐万状,连官衣官帽都来不及穿戴齐全,拖着鞋跑出来迎接。盛爷和他打了个招呼,叫他回避,便吩咐众衙役擂鼓升堂。盛大人在大堂坐定,命公差按照状子将有牵连的人员和案犯全部拿入公堂。
这一下可苦了张绪,他姐姐的保护伞失去作用,被公差们从后堂像抓小鸡一样丢进了公堂。其余两个公差也一齐拿到。章邦杰,以及韩荣坤夫妇、庵中小尼等有关人员都在堂下听审。
盛大人把惊堂木一拍,厉声说道:“张绪,你快把行奸不成逼死人命之事从实招来,倘有半句胡言乱语,立刻叫你身首不保。”
张绪出生以来,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严词,偷眼往上一看,见这位官员面似锅底,三绺长须,威风显赫,不怒自威,如同阎罗天子一般,吓得他胆战心惊,浑身颤抖。为了活命,还想把陈师爷的那根救命草拿出来试试看,底气不足地抵赖道:“青天大老爷,小人自小受父母教诲,姐丈、姐姐的培育,从来是遵纪守法,不做违心之事。只是去年在城隍庙会时,偶然遇到一位少女,我们一见钟情,我曾多次求姐姐托人撮合,但她的父母胆小怕事,不愿与衙门攀附,拒绝了这门亲事。可是我俩已情投意合,不肯分开,只得私下来往。三个月前,她对我说身子有孕,要去洞源灵瑞庵中避嫌。小人听后非常高兴,心想,她真的有了孩子,就不怕她的父母不接受我这个女婿了,就同意她的想法。在灵瑞庵期间,我曾到那里看望她两次,她都开开心心的,可是这次去看她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提出要把胎儿打掉,小的不肯,两下争吵起来。她提刀在手,说若不依她就要死在我的面前。小人以为她是在恐吓我,没有认真阻拦,不料她真会自刎身亡。我现在悔之不及,青天大老爷,奸情是有,但两厢情愿,人死是实,可不是我逼的,望青天大老爷明鉴。”
盛爷见他说得天衣无缝,句句在理,心中犹豫不定,不再问话,便命他跪在一边。继而传灵瑞庵小尼上堂,衙役把小尼带上公堂,盛爷问道:“小尼,你姓甚名何?今年多大?几时出家?”
小尼道:“师父捡小尼在襁褓之中,已有十六年了,没有取过姓名。但有一法名叫妙君。”
盛爷见她小小年纪,言语清晰,心中就有几分喜欢。便问她道:“韩玉琴到你庵堂有多少日子了?”
小尼答道:“有近半年。”
盛爷又问:“在这半年中,她有没有出现过妊娠反应?”
小尼道:“玉琴姑娘自到庵堂以后,精神一直很好,从未见她有什么反胃、呕吐等现象出现。”
盛爷指着张绪问她:“这人到灵瑞庵有几次了?”
小尼道:“这人小尼从未见过,这次他们突然耀武扬威地到来,把小尼吓得躲进厨房不敢露面,后来看见师父被另外两人推倒,这人从玉琴房中逃出后,小尼才敢出来。过去一看,见师父和玉琴姑娘都已身亡,小尼无可处置,只得报于章爷爷知道。”
盛爷点头叫她退下,只留张绪一人,拍着惊堂木喝道:“大胆奴才,好一张厉嘴,说得天衣无缝,本官险些被你瞒过,不上刑具,谅你不肯招出。”即喝令衙役把张绪拖翻,打了四十大板,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飞横,趴在地上爬不起来。
盛爷喝道:“快把****之事从实招来,倘再抵赖,莫怪本官用大刑。”
张绪忍着疼痛,呻吟着道:“通奸属实,但说我****,委实冤枉,叫我如何招认。”
盛爷知道他仗着姐夫是一县之主,不肯即时承认,自己公务繁忙,此地不能久留,如不速战速决,可能要引起别的事端,即吩咐大刑伺候。
即刻堂下咣当一声,一付三木夹棍丢在张绪面前。张绪一见,吓得屁滚尿流。盛爷惊堂木一拍喝道:“张绪,快些招来,免受皮肉之苦。”这个恶少自小娇生惯养,从未受过这般苦痛。刚才的四十大板,已够他受了,在这三木之下,如何忍耐得住。心里骂道,这个瘟官怎么这般铁面无私,姐夫、姐姐为何不送银子给他?左右又没有一个认识之人,如今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不如招了,免受皮肉之苦。于是叫道:“请大老爷手下留情,小人愿招。”就把他如何以催收钱粮为名去六洞山避暑游玩,路过灵瑞庵时如何看见庵内一小女子容颜美丽,就叫两公差守住房门,自己强行进房,抱住求奸,小女子不从,自刎身亡,两个公差如何推死老尼,他的姐姐如何教这些言语来搪塞,绍兴师爷陈春林如何受贿献计,用避重就轻之计污蔑玉琴身怀有孕的事,从头到尾都招了出来。
盛爷听张绪供毕,即命他画了供。当众对此案判决道:
张绪始窥少女之色,辄起邪心。强行求奸未能,逼死人命,情节恶劣,死有余辜,不杀不平民愤,决斩!公差两人助纣为虐,屈死无辜,决斩!童锡明审事不公,听妻谗言,包庇袒护,革职充发宁夏,不准取赎。妻子张氏随夫同往,家中一切财富,俱缴入官。师爷陈春林,诡计多端,贪财受贿,尽出邪念,杖一百,没收赃款,流两千里。将其赃款,作为受害之家抚恤。烈女玉琴,世人楷范,应由兰溪县府出资,章乡绅为首,给予隆重葬礼,为旌表烈女,在灵瑞庵立牌坊一座,以示世人。
此决。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三
众人一听,欢声雷动,一齐跪在大堂,高声呼道:“盛青天审案公正严明,为我们主持公道,使玉琴姑娘昭雪沉冤,真是包拯再世,令我等敬佩。”
盛爷谦逊地说道:“为官者,来自民间,领受朝廷俸禄,务必要替民作主,为朝廷分忧,否则算什么朝廷命官。而今烈女已洗清冤屈,下官就要启程上路。在我走之前,向尔等提出一个建议,下官看来,这小尼虽然没有十分的容貌,但做事非常乖巧,这次烈女冤情昭雪,她起了很大的作用。韩老先生失去令嫒,夫妻二人无依无靠,小尼又无父母,不如还俗,改名玉君,认韩老先生夫妇为父母,这样你们就可互相照顾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韩荣坤夫妇听了,悲喜交加,祝氏一把将玉君搂在怀中,哭着道:“乖乖,这次我女昭雪,全仗你的大力,不知你愿不愿意认我们这苦命的爹娘?”
玉君心想,自己从小被师父收养,如今师父已死,无处安身,有这样一个好去处,哪有不愿之理!于是她含着眼泪,拜过了爹娘。众人见了,皆大欢喜,对盛爷的安排赞不绝口。
盛爷看看天色将晚,便吩咐写好折本,命人连夜进京报于吏部,为兰溪派官。然后带着手下,别了众人,启程前往金华。
次日,在章邦杰的指挥下,隆重地安葬了韩玉琴和老尼。半月后,吏部派遣了新知县,这知县遵照盛爷的决定,由县府拨款在灵瑞庵玉琴墓前建造了两柱三层的石牌坊一座,旌表烈女。可惜的是,这座烈女牌坊已在“**********”初期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