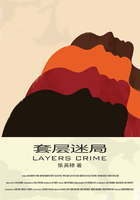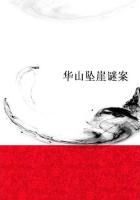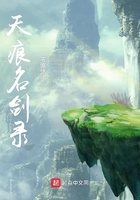梅花从炕上坐起来:“我不怕。诗文哥,咱现在就走。就是走到天涯海角,受多大的苦我都不怕。”
梅尚德把照片举过头顶,高声大笑起来。笑声突然停息,梅尚德一头从椅子上栽下来,头砰地撞在地上。
梅花躺在炕上蒙着头哭,薛蓉也跟着落泪。
梅广元说:“人还能一棵树上吊死?赵诗文有什么好的?天下的好男人不有的是,为什么单恋一个赵诗文?”
梅花也不答话,还是一个劲地哭。
梅广元说:“梅花,你娘像你一样大的时候,也有了意中人。你姥爷上山捧断了两条腿、一条胳膊,我给他接上,侍候了他三个月,他康复了,非得把已经订了婚的你娘许给我不可。你看爹这熊样,有哪点配得上你娘?我们结婚了,不照样过得挺好吗?过一天,我求求大油袖,唉!你看看,我都把大油袖住院的事给忘了。她娘,买点东西到医院看看油袖婶。梅花,我去求求你于莲姨,让她给你找一个比赵诗文好上一千倍的。”
“再好的我也不要。我就要诗文哥!”梅花哭着说。
赵诗文来了,梅广元把烟卷往地上一扔,用脚用力一踩,对赵诗文说:“你来干吗?我们的门槛没有他梅广慧家的门槛高,你快走!”
薛蓉说:“他爹,你这是干吗?既然诗文来了,肯定有话要说,就让诗文把话说出来。”
赵诗文说:“叔、婶,我对不住你们,更对不住梅花。我是喝醉了酒失去理智才做错了事。我真的是喜欢梅花,我对梅婷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您打我骂我都可以。”
梅广元说:“我打你骂你,又有什么用?打了你、骂了你,梅花心上的伤就长好了?”
薛蓉说:“诗文,这也不全怪你。”
梅广元说:“不怪他怪谁?难道怪我,怪梅花?”
赵诗文说:“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二老同意不同意?”
梅广元翻了一下眼皮:“你有什么办法,说吧!”
“走。”赵诗文声音很低,但很坚决。
梅广元说:“私奔?”
赵诗文点点头。
梅广元说:“不行。我可丢不起那个人。”
梅花从炕上坐起来:“我不怕。诗文哥,咱现在就走。就是走到天涯海角,受多大的苦我都不怕。”
薛蓉对赵诗文说:“不行。你走了,不是给梅婷带来伤害吗?再说,她已经是你的人了,你一走,不要她的命吗?”
梅花说:“这全怪她自己,不是诗文哥强占的她,是她强占的诗文哥,她这是自作自受。”
薛蓉说:“不管谁强占谁,都是出于爱。爱都是一样的。我看,诗文,你先回去,对于这事要慎重处理,千万别头脑发热。”
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大包裹来到梅庄,打听梅尚德的家。梅广济说:“往前走,过三个门,门前有棵老梅树的那家就是。”
那人来到梅琴家门口。门闩着,那人就敲门。梅琴以为是狗剩,就出来对着门外喊:“狗剩,你有完没完。你要是再胡闹,我就死给你看。”
那人说:“我是梅广隆的朋友,从东北刚回来。”
梅琴一听,满心欢喜地开了门。那人进来说:“你是梅琴吧,你哥给我提起过。”
梅琴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一副忠厚的模样,就问:“大哥是哪里人?贵姓啊?”
那人说:“我是黄河北牛头镇的。我姓秦,叫秦安。我和你哥在一个林场工作。”
“快屋里坐。”梅琴热情地让道。
梅尚德一听儿子朋友来了,高兴地坐了起来:“琴儿,快,快给客人倒水。”
梅琴把水端到那人面前:“秦大哥,请喝水。”
秦安说:“别客气。我是替你哥来看你们的。”
梅尚德说:“琴儿,快扶我起来!”
梅琴和秦安一起扶梅尚德起身,让梅尚德在椅子上坐下来。
秦安把带来的背包慢慢打开,拿出一件皮坎肩来:“这是广隆兄给大爷您买的,广隆兄弟说,爹穿上这件皮坎肩冬天就不冷了。”然后,又拿出一摞白手套来,“这些手套广隆兄弟一直不舍得戴。广隆兄弟说,妹妹从来没有穿过毛衣呢,他要把手套攒下来,让妹妹织件毛衣。”他又拿出一沓钱递梅琴,“这是你哥的全部积蓄。你点点,共三百二十一块两毛五。唉,你哥说,他借过一个叫大……大油袖的十元钱,记着,一定要还她。”
梅琴接过钱,问:“我哥他好吗?”
秦安说:“你看,你看我这个人,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梅琴。梅琴拿在手上,看到了哥哥梅广隆,在哥哥身边坐着一个秀丽的女人。梅琴指着照片上的女人,问秦安:“这是我嫂子吧?”
秦安说:“是。你嫂子也是工人。是林场里的一枝花。”
“琴儿,快拿来我看!”梅尚德伸着手要照片。
梅琴说:“爹,快看,我哥有媳妇了!”
梅尚德把照片拿在手里,手剧烈地抖动着。梅琴用自己的手稳住爹的手。梅尚德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的模样。梅尚德把照片举过头顶,高声大笑起来。笑声突然停息,梅尚德一头从椅子上栽下来,头砰地撞在地上。
梅尚德死了,死后,脸上依然挂着笑意。
初冬的小雨像一锅煮过了的面条,黏黏糊糊的。雨水湿透的土路特别泥泞,走在路上的人,鞋子陷进泥里,只好弯下腰,把粘满泥巴的鞋子提在手里,做起了赤脚大仙。
大油袖和吕凤英搀扶着吕瑞清,慢慢地走在风雨中的山间小路上。
那天,大油袖被狗剩推倒,紫穗槐茬扎进了她的太阳穴,好在扎得不深,没有要了她的命。梅广济把她送到医院,只做了一番清洗包扎,就出院了。
回到家,大油袖和吕瑞清抱头而泣。这时,吕凤英也来了,决意要和狗剩分手。三个人一合计,觉得还是离开小梅庄,去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
为了避开泥泞的土路,他们选择了光滑崎岖的山路。亦步亦趋,三个苦命的人被命运的绳索紧紧拴在了一起。无论风、无论雨,他们都要一路坚定地走下去。
“爹,你说,狗剩一个人咋过呢?”吕凤英心里惦念起了狗剩。
吕瑞清一听就来了气:“你还惦着他?”
大油袖说:“凤英的心是用枣泥做的。凤英啊,那狗剩真有良心的话,就会良心发现,去找我们的。如果他不找我们,我们也不值得惦念他。”
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三个人走得更加小心翼翼。大油袖尽力把伞往吕瑞清头上罩,自己的衣服全湿透了,小风一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这时,吕凤英突然脚下一滑,一下子从山坡上滚下去。
吕瑞清被带了个趔趄,但在大油袖的用力搀扶下,还是站稳了。他急切地叫着:“凤英,我的儿,你在哪里?”
“爹,我在这儿呢!”吕凤英从山下回应着,声音相当痛苦。
大油袖把伞递到吕瑞清手里:“拿好。”说毕,就顺着吕凤英应声的地方往下走。没走两步,大油袖也滑了下去。
大油袖被一棵树挡住,正好停在吕凤英身边,“凤英,抓住我。”
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大油袖用力把吕凤英背在肩上,用尽全身的力气往上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大油袖的额头上不知是汗还是雨。
细雨纷纷,北风凄迷,大油袖几乎用光了所有的力气。吕凤英叫了一声“娘”,这是大油袖活了这些年第一次听到有人喊自己“娘”,那样亲切,那样入耳,那样舒服。她终于从这声“娘”中,感受到了亲人,感受到了温情,感受到了人世间一种弥足珍贵的爱。
这声“娘”,一下子给大油袖心中注入了无穷的能量、无穷的温暖、无穷的力量。她竟背起了吕凤英,那双圆圆的鼓槌一样的小脚,稳稳地踏在陡峭的山坡上,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公社杨主任来了,召开了小梅庄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杨主任先讲了一通全国的大好形势,然而讲到了全县、全社的大好形势,最后谈到了小梅庄。他对小梅庄前期开展阶级斗争的情况给予了表扬,他特别提出对张卫东的高度赞赏。他称赞张卫东是革命干将,是全社的标兵,是小梅庄的台柱子。最后隆重地宣布公社革委会正式吸纳张卫东为公社革委会委员的决定。杨主任特别强调,今后小梅庄的工作,要以张卫东为主,梅主任要主动搞好配合,其他的党员干部要像狗剩同志一样给予张委员以大力支持。
张卫东也作了表态发言:“我决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才能目张。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小梅庄后进变先进,成为全社乃至全县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
“好!”杨主任带头鼓起掌来。
狗剩受到表扬,手都鼓红了。
会后,得到重任的张卫东和受到表扬的狗剩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又一次把棒子队集合起来。他俩突然又犯难了:阶级斗争要抓“纲”,梅尚德死了,大油袖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这“纲”没有了,怎么办?张卫东找到狗剩,征求狗剩的意见。
狗剩立时就想到了梅琴:“老地主死了,还有小地主。梅琴就是纲。”
虽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总得找出梅琴的一些“罪状”。张卫东叹了一气:“可惜,梅琴虽说是地主羔子,可她没有小辫子啊?”
狗剩把眼用力一睁:“怎么没有,她不是有两条长长的黑黑的辫子吗?”
“不是那个辫子,是、是罪恶的辫子。”
“罪恶?”狗剩立马想到了梅琴废自己的事,“张、张委员,你看看……”他脱下裤子,叫张卫东看。
张卫东踢了狗剩一脚:“娘的,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狗剩急忙解释:“梅琴她、她向贫下中农下毒手。”
“她向贫下农下毒手?”张卫东听狗剩这么一说,立刻来了兴致,“快说说看,她怎么下的?”
“她和大油袖搞串联……”狗剩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好!说不定这里面有大案要案。”张卫东说,“我们就拿梅琴开刀!”
哥哥去了东北,爹去世了,爱情也离她远去了,仿佛一下子把梅琴的生命都掏空了。
梅琴把诗稿一页页放进火里。她的痛、她的爱、她的梦、她一切的一切,都在火光里消散了。
这时,门外又传来砰砰的砸门声和“打倒地主息子梅琴”的呼叫声。她像一只被入围猎的兔子,随时都会中弹身亡。与其在这人世间受屈辱,还不如随爹爹一起走。
她找出自己最心仪的衣服,一件件穿在身上,又走到桌前,对着镜子用梳子仔细梳理着自己的头发。
一根细长的麻绳搭在了院内的老梅树上,绾一个死结。那绳套就是地狱之门,梅琴脚踏着凳子,两手抓紧绳子,把脖子伸向绳套……
赵诗文拿着酒杯喝着闷酒,突然,酒杯一下子从手里脱落。
“不好!”他突然意料到什么,拔腿就往外跑。
他用力推梅琴的大门,却怎么也推不动。他用力地拍着,大声地喊着梅琴的名字,但里面却没有一丝声响。赵诗文顺着墙外的一棵树爬上墙头,往里一看,梅琴吊在了梅树上。他跳下墙头,把梅琴抱下来,试试鼻吸,已没有了一丝气息。把手伸到梅琴的胸口,赵诗文感到了梅琴心依旧在微弱地跳动。他用双手按压梅琴的胸,一下、两下、三下……赵诗文感到梅琴的心跳越来越强烈。
赵诗文把梅琴抱进屋里,放在桌上,再往梅琴嘴里喂一点水。梅琴白皙而纤细的手冰冰的,像雪。赵诗文坐在梅琴的身边,用自己的手握住梅琴的手,把自己的温暖传递给梅琴。梅琴慢慢睁开眼睛,微微侧了一下头,看着身边的赵诗文,泪水一下流了出来。
“你怎么这么傻?干吗要去寻死?要为希望活着,为希望活着。好好活着才是啊!”赵诗文用手拭去梅琴的泪花,“我知道你心里苦,琴姑,你想哭就哭吧,有苦水倒出来就好了。”
“诗文……”梅琴内心的苦水像决堤的江河,奔涌而出。她抱住赵诗文的脖子,号啕大哭。“诗文,你干吗要救我,干吗要救我?”赵诗文把梅琴紧紧搂在怀里,用手轻轻地拍着梅琴的背。
梅琴的寻死,并没有阻止张卫东们批斗梅琴的想法。
张卫东严厉地指出梅琴是以死对抗无产阶级****,为了防止梅琴再度自杀,他下令把梅琴绑起来押到革委会,随时进行批斗。
两个队员上来扯梅琴的胳膊,赵诗文用力推开他们:“谁敢动梅琴一指头,我就和他拼命!”
张卫东走过来,对赵诗文说:“诗文,你最好别干扰斗争大方向。你这样做对谁都不好。”
赵诗文说:“我不管什么大方向小方向,今天谁要敢动梅琴一根毫毛,我赵诗文就不答应。”
狗剩说:“赵诗文她又不是你老婆,你干吗护着她?”
赵诗文说:“从现在起,她就是我的老婆。”
张卫东说:“如果梅琴是你的老婆,我们也无话可说;如果不是,她就是地主,我们照样批斗。不过,话又说回来,是不是老婆,不能凭嘴一说,咱们得看看结婚证。”
狗剩走到赵诗文跟前:“拿出结婚证来!没有吧?没有,我们可要抓人了!”然后一扬手,“抓!”那两个队员听到命令,又出手抓人。
“住手!”赵诗文大喝一声,“我明天就给你们结婚证!”
“好。我们等着。”张卫东把手一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