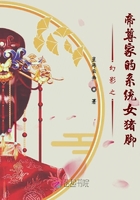七
美琳说“不知为什么,生活总没有起色?”真的,他们是毫不愉快,又无希望的生活到春浓了,这个时候是上海最显得有起色,忙碌得厉害的时候,许多大腹的商贾,和为算盘的辛苦而瘪干了的吃血鬼们,都更振起了精神在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之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做无厌的剥削,为涨满他们那不能计算的钱库。而且几十种报纸满市喧腾的叫卖着,大号的字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都是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都换了春季的美服,脸上放着红光,眼睛分外亮了,满马路的游行着,各游戏场的拥挤着,还分散到四郊,到近的一些名胜区去,为他们那常常享福的身体和不必忧愁的心情更找到些愉快。这些娱乐是只更会使得他们年轻美貌,更会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的生活满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们呢,虽说逃过了严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压迫却也同着长日的春天一起来了,米粮长了价,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他们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赢瘦了,衰老的不是减了工资,便是被开除了,那些小孩们,从来就难于吃饱的小孩们,只好去补了那些缺,他们的年龄和体质都是不够法定的。他们是太苦了,他们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天的新的消息不断的传着,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党,都异常忙碌起来,他们同情他们,援助他们,在某种指挥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深了,软的风,醉人的天气!然而一切的罪恶,苦痛,挣扎和斗争都在这和煦的晴天之下活动。
美琳每天穿了新衫,绿的,红的,常常也同着子彬在外面玩,但是心里总不愉快,总不满足,她看满街的人,觉得谁都比她有生存的意义。她并不想死,她只想好好的活,活得高兴,现在她是找不到一条好的路,她需要引导的人,她非常希望子彬能了解她这点,而且子彬也是与她一样,那他们便可以商商量量的同走上一条生活的大道。不过她每一观察子彬,她就难过,这个她所崇拜的人,现在是在她看起来成了一个不可解的人了。他仿佛正与她相反,他糟蹋生活,然而又并不像出于衷心,他思想得很多,却不说一句,他讨厌人,却又爱敷衍(从前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在人面前感到苦痛的),发了牢骚,又恨自己。他有时更爱她,有时又极冷淡。种种的行为矛盾着,苦痛着自己。美琳有时也同他说一两句关于生活方面的话,不过这只证明了她的失望,因为他不答她,只无声的笑,笑得使美琳心痛,她感觉到那笑的苦味,她了解他又在烦恼了。直到有一天夜晚,八点多钟的时候,家里没有客,他因为白天在外面跑了好久,人很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词,美琳坐在床头的椅上,看一本新出的杂志。床头的小几上,放着红绸罩子的灯,泡了一壶茶,这在往顺,真是一个甜蜜的夜。这时子彬很无聊,一页一页的翻着书,不时斜着眼睛去望美琳。美琳也时时望着,两人又都像故意的不愿使眼光碰着,其实两人心里都很希望对方会给一点安慰,都很可怜似的,不过他更感伤一点,她还有点焦躁,末后美琳实在忍不住了,她把杂志用力的摔开说道:
“你不觉得吗,我们是太沉默了,彬,我们说点话吧。”“好……”子彬无力的答着,也把书向床里掼去。
然而沉默还是继续着,都不知说什么好。五分钟过后,美琳才抖战的说道:“我以为你近来是太苦痛了。为什么呢?我很难过!”她用眼紧望着他。
“没有的事……”子彬又照例露出虚伪笑容,不过只笑了一半,便侧过脸去,长长的叹了一声气。
美琳很感动的走了拢来握着他的手,恳求的,焦急而又柔顺的叫道:
“告诉我,你所想的一切!你烦恼的一切!告诉我!”
子彬好久不做声,他又被许多纷乱的不愉快的杂念缠绕住了。他很希望能倒在美琳怀里大哭一场,像小时在母亲怀里一样,于是一切的重大的苦恼都云似的消去,他将再重新活泼泼的为她活着,将生活想法再慢慢的弄好。但是他明白,他咬紧牙齿想,的确的,那是无用,这女人就比他更脆弱,她受不起这激动的,他一定会骇着她。而且他即使大哭,把眼泪流尽了又有什么用呢?一切实际的纠纷的冲突与苦闷,仍然存在着,仍然临迫着他。他除了死,除了离去这相熟的人间,他不能解脱这一切。于是他不做声,他忍受着更大的苦痛,他紧紧握着她的手,而且显出一副极丑的拘挛着的脸。
那样子真怕人,像一个熬受着惨刑的凶野的兽物,美琳不解的注视着他,终于叫起来,快快的锐声的:
“为什么呢?你做出这么一副样子,是我鞭打了你吗?你说呀!唉,啊呀!我真忍耐不了!你如再不说,我就……”
她摇着他的头,望着他。于是他又侧过脸来,眼泪流在颊上了,他挽着她的颈,他把脸凑上去,断续的说:
“美,不要怕,爱我的人,听我慢慢的说吧!唉!我的美!唉!我的美!只要你莫丢弃我,我就都好了。”
他紧紧的偎着她,他又说:“唉!没有什么……是的,我近来太难过,我说不出……我知道,总之,我身体太不行,一切都是因为我身体,我实在需要休养……”
后来他又说:
“我厌恶一切人,一切世俗纠纷,我只要爱情,你。我只想我们离开这里,离开一切熟识的,到一个孤岛上去,一个无人的乡村去,什么文章,什么名,都是狗屁!只有你,只有我们的爱情的生活,才是存在的呵!”
他又说,又说,说了好多。
于是美琳也动摇了,将她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求进展的心抛弃了。她为了他的爱,他的那些话语,她可怜他,她要成全他,他总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她爱他,她终于也哭了。她不知安慰了他多少,她要他相信,她永远是他的。而且为了他的身体和精神的休养,她希望他们暂时离开上海,他们旅行去,在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环境之中,度过一个美丽的春天。他们省俭一点,去在流星书店设法再卖一本书,也就够了,物质上稍微有点缺乏有什么要紧呢?他们计算,把没有收在集子中的零碎短篇再集拢来,要七八万字,也差不多了。这旅行是并不难办,美琳想到那些自然的美景,又想到自己能终在与子彬遨游其中,反觉得很高兴了。子彬觉得能离开一下这都市也好,这里一切的新的刺激,他受不了。而且他身体也真的需要一次旅行,或是长久的乡居。于是在这夜,他们决定了,预备到西湖去,因为西湖比较近,而美琳还没有去过的。
这夜两人都又比较快乐了,是近来没有过的幸福的一夜,因为都朦朦的有一线希望,对着未来的时光。
五
第二天拿到了一部分稿费,买了许多东西,只等拿到其余的钱就动身。可是第三天便落起雨来了,一阵大,一阵小,天气阴得很,人心也阴了起来,盖满了灰色的云。美琳直睡了一天,时时抱怨。子彬也不高兴,又在书铺跑了一趟空,钱还要过几天。雨也就接连几天都潇潇的落着,像没有晴的希望。两人在家里都无心做事,顺子长得很,又无聊,先前子彬还常常为她重复一点西湖的景致,后来又都厌烦起来了。等钱等得真心急。不过在第六天拿到全部的稿费之后,子彬没有露出一线快乐的神气,而且只淡淡向美琳说:“怎么样呢,天还是在下雨,我看再等两天动身吧。”
这决不能成理由,雨下得很小,而且西湖很近,若是真想去得厉害,是可以马上动身。
美琳没有生气,也不惊诧,仿佛不动身,又再挨下来倒是很自然,既然去西湖并不是什么必需的要紧的事。这时日的拖延是将两人的心都怠惰起来了,而且又都重复沉在各人的过去曾被痛苦着的思想中去了。子彬时时还是可以听到一些使他难过的消息。许多朋友,许多熟悉的人,都忙着一些书房以外的事去了,都没有过问他,而且都忘记他了。这些消息最使他难过,他鄙视他们,他恨他们,但是他觉得他不应该逃避,他要留在上海,在看着他们,等着他们,而且他要努力,给他们看。假设他到西湖去,他能得个什么,暂时的安宁,暂时的与世隔绝,但是他能不能忘怀一切的得着安闲,还在不可知之间,而世界则真的将他隔绝了是容易的。朋友们听到了这消息,一定的总要嘲笑他,说他是怕了他们,怕了这新的时代,他躲避了。后来大家便真的忘了他,连他的名字都会生疏起来。再呢,他的那些崇拜他的人,那些年轻的学生,和那些赞赏他的人,那些硕学的有名的人物,都隔绝了他的消息,也慢慢会将。他所给与他们的一些好的印象,淡了起来,模糊了起来……这真是可怕的事。他不能像过去的一些隐逸之士能逃掉一切,他要许多,他不能失去他已有的这一些。他简直觉得到西湖去只是件愚蠢的事。他惟恐美琳固执着成见,他想即使美琳要去,也只好拂一次她的意,或是他陪她去玩两三天,立刻便转来,要住下是办不到的事。他看见美琳不像以前着急了,倒放一点心,后来是到非再做一次正式商量不可了,他只好向她说他的意见,理由是他有一篇文章要写,现在没有空,他觉得把行期再迟一个月也很好。他说得真委婉,还怕美琳不答应,或至少也要鼓着小嘴生气的。他还预备好许多温柔的,对付一个可爱的娇纵女人所必需的话。他说完的时候,将头俯在她的椅背上,嘴唇离那白的颈项不很远,气息微微嘘着她。他软声的问:
“你以为怎样呢?我还是愿意随你,依你的意思。”
美琳只懒懒答应了一句,于是事情便通过了,毫无问题。以后只应该安心的照自己所希望的去努力进行,这是说单对于子彬的一面。既然自己是一个写文章的人,又对于自己极有把握,生来性格又不相宜于做别的争斗的勾当,而且留在上海,原意便是为要达到自己的野心的完成,若是还要这么一个人关在小屋子发气,写点牢骚满纸的信,让时间过去了,别人越发随着时间向前迈进了,而自己真的便只有永远和牢骚同住,终一生在无聊的苦痛中,毫无成就可言,纵有绝世的聪明也无用。至于美琳,她是不甘再闲住了,她本能的需要活动,她要到人众中去,去了解社会,去为社会劳动,她生来便不是一个能幽居的女人。她已住得太久了,做一个比她大八岁的沉郁的人的毒子舳尸绎常导白尸眇讨妻害静了许名尸。
经会忧愁烦闷了一些,但还是不能了解她丈夫,这生活对于她是不相宜的。自从春天来,自从她丈夫开始了新的苦痛来,她就不安起来了,不安于这太太的生活,爱人的生活。她常常想动,但是她缺少机会,缺少引路的人,她不知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她烦恼,她又明白这烦恼是不会博得子彬的同情的,于是更不快乐。前几天还能一下会想到西湖去,当然还比较好,慢慢时间拖下来,倒又觉得别的许多人都忙着工作,而自己拿了别人的钱去陪一个人去玩,去消遣时日,仿佛是很不对,很应该羞惭的事。现在既然子彬已不愿去了,当然很合适,不过子彬说他不能去的理由,是因为没有空,因为要写文章,而自己则无论去留与否,在事实上看来,都是无关紧要,因为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事可做的人,她更加觉得羞耻。她要自己去找事做,她想总该有把握找得到,但是她想她应该不同子彬商量,而且暂时瞒着他。
九
出于意料之外的若泉接到一封短笺,是辗转经过了好几个朋友的手转交了来,而是在信面上便大大署了美琳两个字的。若泉不胜诧异的去打开它,满心疑惑到子彬身上,他八分断定他朋友是又病倒了。他心里有点难过,他想起他朋友的时候总是如此。可是信上只潦草的歪歪斜斜涂了不多几个字,像电报似的横着:星期日早上有空吧,千万请你到兆丰公园来一下,有要事。我等你。美琳。
这不像是子彬有病了的口气,然而是什么事呢,两人吵了架,但又从没有看见过他们有口角的事,若泉真怀疑,他还是觉得这至少是于子彬有关的,因为他想美琳决不会有事来找他,因为虽说是与她相熟了两年,还始终没有同她生过一次比较友谊的关系,他也不十分知道她的历史,也从没有特别注意过,只觉得她还天真,很娇,而且决不是难看的一个年轻女人。他想到朋友,他决定第二天早上跑那么远,到上海的极西边去。
七点钟的时候,他预备动身,拿了一把铜子,两角洋钱,拍了一下身上旧洋服的灰尘,于是便匆匆的离了住处,他计算着到兆丰公园时,大约是七点四十分,美琳她们是起身很迟的人,不见得就会到,但他无妨去等她的。他有大半年不来这里了,趁这次机会来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也很好,他近来觉得他的肺部常常不舒服。转乘了三次电车才到公园门首,他买了票,踏到门里去,一阵柔软的风迎着吹来,带着一种春日的芳香。若泉挺着胸脯,兜开上衣,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立刻便觉得舒适了起来,平日的紧张和劳顿,都无形的滑走了。人一到了这绿茵的草地上,离开了尘嚣,披靡着春风,亲炙着朝晖,便一概都会松懈了,忘记了一切,解除了一切,只任自己的身体纵横在这自然中,散着四肢,让这宁静的四周享乐自己,一直到忘我的境界。
园里人不多,几个西洋人和几部小儿车,疏疏朗朗的散在四方。四方都是绿阴阴的,参差着新旧的绿叶。大块的蓝天静静的覆在上面,有几团絮似的白云,耀着刺目的阳光,轻轻的袅着,变幻着。若泉踏着起伏不平,波样的草地,懒然的走了好远,他几乎忘记他是为什么才来到这里了,只觉得舒适得很,这空气正于他相宜。在这时他听到近处他背后的草地上有着塞率塞搴的响声,他掉头望时,他看见美琳站在他背后,穿一件白底灰条纹的单旗袍,上罩一件大红的绒坎肩。他不觉的说道:
“啊,我不知道你来了,啊,你真早啊!”
美琳脸上很平静,微微有点高兴和发红,她娇声的说:“我等了你许久!”但立即便尊重的说道:
“你不觉得无聊吗,我想同你谈谈,所以才特地约了你来,我们找个地方去坐坐吧。”
于是他随着她朝东走,看见她高跟的黄漆皮鞋,一步一步的踏着,穿的是肉色的丝袜,脚非常薄,又小,现得瘦伶伶可怜似的。他不知道还是她的脚特别小,还是脚一放在那匠心的鞋中才显得那么女性,那么可怜。他搭讪的问道:
“子彬近来怎么样,身体好吗?”她淡淡的回答:
“好,他在开始写文章了。”他又继续问:
“你呢,也在写文章了。”“不。”
他看见她脸扭了一下,做了一个极不愿意的表情。
在一个树丛边的红漆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靠左边又有一大丛草本的绣球花,开得正茂盛,大朵大朵的,吐着清香,放着粉红的光。他不知怎么先开口,他还是关在闷葫芦里,不知她到底要谈什么,而且到底不知子彬近来怎么了,或是同她的关系。
她先望着他茫然的脸笑了一下,然后说:“你奇怪吧,当你接到信后,一直到这时?”“没有,我不觉得奇怪。”
“那你知道我要你来这里的缘由了。”他踌躇的答:
“不很知道。”
于是她又笑了一下说:“我想你不会知道的,但是我必须告你,原因便是我很久来了都异常苦闷……”她停顿了一下,又望了他一下,他无言的低着头望草地。于是她又再续下去,她说了很多,又常常停顿,又有点害羞似的,不能说得很直截痛快。但他始终不做声,不望她,让她慢慢的说完,她把她近来所有的一些思想,一些希望,都零碎的说了一个大略,她觉得可以停止了,而且她要听他的意见,她结束着谠道:
“你以为怎样呢,你不会觉得我是很可笑吧?我相信我是很幼稚的。”
若泉有一会没有做声,望着那嫩腻的脸,微微含着尊严与谦卑的脸好久。他没有料想这女人会这么坦率的在他面前公开她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她的大胆的愿意向社会跨进的决心。他非常快乐,因为这意外的态度,更鼓舞了他。隔了好一会,他才伸过手去,同她热烈的握着,他说:
“美琳!你真好!我到现在才了解你!”她快乐得脸也发红了。
于是他们都又更不隐饰的谈了一些近来所得的知识与感觉。他们都更高兴,尤其是美琳。她在这里能自由发挥,而他又听她,又了解她,而且还帮助她。她看见光辉就在她前面。她急急的愿意知道她马上应怎样开始。他又踌躇了一会儿,他答应过两天再来看她,或者可以介绍她去见几个人,帮助她能够有些工作。
一。
美琳回到家来,时时露着快乐的笑,她掩藏不住那喜悦,有几次她几乎要说出来了,她仿佛觉得应该告诉子彬,但是她又忍耐住了,她怕他会阻止她,破坏她。子彬没有觉察出,他在想一篇小说,在想一些非常调皮嘲讽的字句去描写这篇的主人翁,一个中国的吉诃德先生。他要他的文章动人,他文章的嘲讽动人,他想如果这篇文章不受什么意外的打击,就是说他不再受什么刺激,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写两星期,那一个十万字的长篇,便将在这一九三。年的夏季,惊人的出现了。谁不会惊绝的叫着他的名字,这作者的名字。他暂时忘去能苦恼他的一些事实,他要廓清他的脑府,那原来聪明的脑府,他使自己离开了人众,关在家里几天了。
可是美琳却不然,她在第三天下午便出席在一个文艺研究会上了。到会的有五十几个人,一半是工人,另外一半是极少数的青年作家和好些活泼的学生。美琳从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她只觉得兴奋,同时用着极可亲的眼光遍望着这所有的人,只想同每个人都握一次热烈的握手,和做一次恳切的谈话。这里她除掉若泉以外,便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是她一点也不感觉拘束,她觉得很融洽,很了解,她和他们都很亲近。她除了对于自己那合体的虽不华贵却很美观的衣服微微感到歉仄外,便全是倾心的热忱了。这是一次大会,所以到的人数很多,除了少数的工人为时间限制着不能来,几乎全体都到了。开始的时候,由主席临时推举了一个穿香港布洋服的少年做政治的报告,大家都很肃静,美琳望着他,没有一动,她用心的吸进了那些从没有听过的话语,那些简单的话语,然而却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情形很有条理的概括了出来,而且他批判得真准确。这人很年轻,决不是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后来若泉告诉她,这年轻人还是一个印刷工人呢,不过也曾在大学念过两年书。美琳说不出的惭愧,而且她觉得所有的人对于政治的认识和理解都比她好,也比她能干。在她听了其余许多人的工作报告之后,他们又讨论了许多关于社务的事。这在美琳都是不知应怎样加入那争论之中去的,因为她都还不熟悉,而那主席却常常用眼光望着她,征求她的意见。这使她真难过,她又坚决的相信,在不久以后,她一定可以被训练得比较好些,不致这样完全不懂。最后他们又讨论到××怎样行动的事。这里又有人站起来报告,是另外一个指导的团体的代表。于是决定了,在“五一”的那天,要全体动员到大马路去,占领马路,这时大家都正情绪更紧张激昂的时候,而会便完了,在分别的时候,大家都互相叮咛的说道:
“记着:后天,九点钟,到大马路去!”
美琳还留在那里一会儿,同适才的主席,便是那在工联会工作的超生,和若泉,还有其他两三个人谈了一会,他们对她都非常亲切和尊重,尤其是一个纱厂的女工特别向她表示好感。她向她说:“我们呢是要革命,但是也想学一点我们能懂的文艺,你们文学家呢是也需要革命,所以我们联合起来了。不过我们真没有时间,恐怕总弄不好,过几天我把我写的一点东西给你看看吧,我听超生说,你是个女文学家呢。我也是刚刚学动笔,完全是超生给我的勇气,心里是想得很多,就是写不出来。下星期一能抽空,我还想写一篇工厂通讯,因为若泉说他们要有用呢。”
美琳说她也不会文学。她还说她也想进工厂去。
于是那女工便描写着那工厂里的各种苦痛,和列举着一些惨闻,她又说如果美琳真的愿意,她可以想法,不过她担忧若果美琳进去,怕那劳顿和不洁的空气,将马上使她得病。超生也说,进去是容易,而且他希望这社里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要进厂去,去了解无产阶级,改变自己的情感,这样,将来才有真的普罗文艺产生。不过他也说恐怕美琳的身体不行。美琳则力辩她可以练习好的。因为美琳比较有空闲,她被派定了每天应到机关上去做两个钟头的工,他们留给了她一个地址。还说以后工作时间怕还要加多,因为五月来了,工作要加紧,而且内部马上便要扩大,有许多工人都自愿参加进来,这里需要训练得很。她刚刚跨进来,便负了好重的担子了,她想她应该好好努力。
是五月一日的一天了。
子彬从八点钟失了美琳的时候起便深深的不安着,他问娘姨,娘姨也不知道,他想不出她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开始发觉近来她是常常的不在家,而且她没有告诉过他她是到什么地方去,他并且想起她是同他太说得少了。他等了她好久,都不见回来,他生着很大的气,他冲到他书房去,他决定不想这女人的一切了,他要继续他的文章,那已写好了一小部分的文章。他坐到桌边,心总不定得很,他去翻抽屉,蓦然的却现出美琳留给他的一封信。他急急看下去,像恨不得立即便吞灭进去似的看,信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写着:子彬:我真不能再隐瞒你了。当你看到这信的时候,我大约已在大马路上了,这是受了团体的派定,到大马路做运动去。我想你听了这消息,是不会怎样快乐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而且向你解释,因为我原来是很爱你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希望你不致对我有误解,所以我现在先作这样一个报告,千万望你想一想,我回来后,我们便可作一次很理性的谈话,我们应该互相很诚恳很深切的批判一下。我确实有许多话要向你说,一半是关于我自己,一半也是关于你的。现在不多说了。
美琳晨留子彬呆了半天,连气也叹不出一口来。这不是他的希望,这太出他的意表了。他想起许多不快的消息,他想起许多熟悉的人,他想美琳……唉,这女人,多么温柔的啊,现在也弃掉了他,随着大众跑去了。他呢,空有自负的心,空有自负的才能,但他不能跑去,他成了孤零零的了。他难过,想哭也哭不出,他惨惨的幻想着这时的大马路,他看见许多恐怖和危险,他说不出的彷徨和不安,然而他却不希望美琳会转来,他不愿见她,她带回了许多痛苦给他,还无止的加多,他真不能忍受有这么一个人在同一个屋中呼吸。他发气的将信扯碎了。他最后看见那还只写了薄薄几张的稿纸本大张着口,他无言的,痛恨的却百般悼惜的用力将它关拢了,使劲的摔到抽屉里。他叹出了一口长长的叹息。
1930年查找的。
在家的那方,那隔断了家的那堵不知名的山,慢慢的已经又从黑得不分明的里面,显出紫褐色来,而且在那染上了红霞的透亮的天空上,画着很分明的却是柔和的线。又一阵寒冽的晨风从荒凉的田地上打来,扫过这几间红砖的小屋,又迈步到对面的树丛,夜来的像似虎啸的狂吼,已经低到只是像猫头鸟的咻咻的就过去了,却也还是冷得刺骨。张大憨子耳里听到风已走过了好远,便又用背把抵住他背蹲着的王阿二撞了一下,便像是自语似的咕哝了一句:
“天亮了呢。”他已经把他那烂了边的红眼睛,从拱着手的袖口边移出了一条细缝,黯黯的望着红的那方,在那方,正有着家在那儿。
粗草鞋套在烂棉鞋上的一双偎在他腿边的大脚,也抖了抖伸开站起去了。伛着腰在他前边走了一步便又停住了,说道:
“该快来了,说了是天亮的那班……”他没有说下去,却又伛着腰坐了下来,接着又打了一个冷噤。
草鞋的大脚便又伸在张大憨子的腿边。另外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走到墙的转角去,溲溲的小便着。这时天更亮了起来,满天都是彩霞,红房子的那一端,一个可怜的瘦雄鸡,也抖了抖翅膀,伸着颈格格的叫了起来。小便的人走了回来却不蹲下去,靠着墙又去揉眼屎。那盏悬在眼前的电灯,还无力的射着一粒淡淡的黄光。不知从什么地方又闯来了几个乡下人,都提着大包裹,像是做小生意的人。来的人把他们望了一望,便站在那一边互相说着什么。他们懂得车一定快来了,也有两个人又站了起来,试着把蜷得麻痹的手脚伸了一伸。
那个穿制服的可怜的瘦小伙子,夜晚看到他几次在车来车去忙碌的跑着的,又咳嗽着走出来了。他打了一个圈子,望了望嵌在墙上的钟,便朝这群土老儿,几乎在这冷风里挨过大半夜的一群投过了一个眼光,带点怜悯也带点不屑的神气,于是他说道:
“来呀!”
而这时那个镗镗的钟声也响起来了,他们在这里是听到第三次的钟声了。
他们便都站了起来,伛着臃肿的身躯,跟着那穿制服的人走到那买票的小门边。那人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就走了。他们都望着那小门,没有听他。
“四等,六角大洋!一个一个的来!”门洞里一片灯光落在一个小柜台上,卖票的人穿着一件布棉袍,耸着肩,红着一双没有睡够的眼睛,不耐烦的说。他那旁边正放有一把破嘴的小瓦壶,似乎正冒着热气,把每个买票的人都羡慕的送过眼光去。
一块雪白的大洋往台上一丢,响声打到了心里,不说话,揣着找回的四角大洋票,算也不必去算,得,左右不过……便走开了。“管他娘,横竖几个钟头便到了……”张大憨子看乔老三忧愁的按着他装钱的褡裢袋,便安慰他这样说。他觉得他这句话也把自己安慰了一点儿。
“唔!”乔老三也跟着走进了月台。月台上又多了几个不曾见过的人,也有一个穿长衫的,大约就是学生吧。
奔
太阳已经吐出了一线火红。远的稀的树枝间也吐着滚滚的浓烟,而跟在那后面,便传来了巨大的轧轧的车轮声。突突的汽笛锐叫了两声,火车便喘息着,流着汗,一步一步,拖着滚来,滚去,而停在小的月台上了。
有人朝一个车门口奔去,其余的便跟着去挤。车上也有被推出来的人,都拦在那一个小门口,有的就嚷起来了。又有着大声音喊:“那边去,这是三等!”于是这一群更慌作一团,掉转身急忙的,张着呆笨的眼光,胡乱的又朝另一个门口奔去,终于挤上了一个车厢。
旧的,脏的车厢里面,挤着一些破的烂的布堆,而又在这布堆上排列着不整齐的人头,歪着的,挂着的。有些正咧着黄牙大嘴,从那大嘴里送出浓的臭味,还从那些张着的鼻孔里,一声一声的吐着鼾声。有些是把好久没修剃过的头发蓬乱的倒着,而口涎便长长的垂到胸际。有些也张开了睡眼,望望车外也望望进来的这一群,不动也不说。
“张大哥!这里有位子!”
“去,那边去,那边还好挤一个!”
被闹醒了的,移了一下身子,便又睡去了。有些便也揉着眼睛去望那关着的玻璃窗,窗上浮着一层雾。
车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用着快步在跑了。
“吓,这个什么火车,倒真了不得,阿二,你来看,山呀,树呀,像鬼旋磨,旋着旋着就跑去了。”
王阿二真的就扭着头把眼睛伏在玻璃窗上,老龙的衣袖已经揩去了一块玻璃窗上的雾。他们都因为车厢上的暖气和车外的奇异的景致弄活泼了一点儿。太阳也斜斜的在车里画上好多条黄光,好些人都为这黄光伸直的坐了起来。
乔老三又摸了摸他的褡裢袋,他想到他的家财。那袋中所有的一切,使他有点茫然,因为他的跟在这群人之中到上海去,完全是由于他老婆的怂恿,他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他又重复着他已说过了好几次的话来说道:
“张大哥!到了上海,你可别丢开我不管,我比不得你们,有亲戚熟人,好歹要替我找个落脚!你知道我身上只有这一点盘缠……”
“我身上会比你多吗?还不是那一点阎王债,一块光洋和四张毛票,什么事都到了上海再讲,莫那么短气!”李祥林把缺着嘴唇的嘴挤了进来插着这么说。
“对的,找着他们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们家里,阔人多得很,找在把饭还不容易吗?”张大憨子又把那烂眼皮朝家的那方挤了几挤,想着这是烧早粥的时候,又想着借来的那斗米和剩下的两簸箕糠,吃总是不愁的了。于是他又接下去说道:“只要找得到事做,总不怕他那孙二疤子,妈的这东西,到夏天我们归账时,一人三石谷算在一块,便宜点,二亩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只要归得上,再多点也不要紧,就怕……”乔老三说着就把头低下去了。
老龙这时已从在袋里掏出一个干馍啃着,另外也有人啃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粗粝的大饼,而谈话就又加上了一些生气。
“到底也值得,大半夜的老西北风,吹在咱们身上不算个什么,六角大洋,嘿,就是好几天的粮,冷总还熬得住,饿可不成。”
“三等四等一个样,要有五等咱们就坐五等,再打个对折。”
“到上海几个钟头五个,还不贵五个钟头要花上六角大洋,合钱是两千了……”
坐在旁边的那些同车的不认识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他们也有些是去上海的,但是对上海的情形也是不熟悉。大家互相交换了一些家乡的苦难,和旅行的目的,大抵都相差不远。于是又谈到年成,又谈到行市,车里慢慢的更热闹起来了。有几个娘儿们也坐在那一端,敞开了胸邑,口袋似的垂着的大奶便塞在哭了的婴儿的嘴中。太阳这时已经从每一个窗邑投了大片的阳光进来,因着车身的震动,在那些干糙的脸上和脏的布衣上跳跃的荡着。而这群人,这群在冷风里蹲在墙边蹲了大半夜的人,因了暖热的空气,加之胃囊里又渗入了一些粗的麦粉,昏昏的瞌睡,便慢慢的爬上了眼皮,谈话减少下去了,新的鼾声又在一些睡醒了的人旁边发了出来。
“嘟!嘟!”汽管子嘶着尖锐的喉咙,接连的叫着,黑的浓烟,白的蒸汽,在车身边扫着,轮轴发狂似的在引擎下滚着,车上的乘客都骚动起来了:“看,看洋房子呀!看那些烟筒,那就是工厂呀……”车到了上海了。
长的列车驶进了火车站,停在第六条月台上。几十个车门里,吐着那从各乡各镇汇流了来的人群。这群土老儿,紧紧的六个人挤在一块,跟着人群朝出邑奔。扛运夫杂在穿皮大衣的粉脸太太里,太太们又吊在老爷的手上,老爷们昂首在乡下人旁边,赛跑似的朝出口处奔去。大人们不知在喊些什么,小孩子也跟着在喊。也有跑在前面去了的人又打回奔……“妈的,乖乖!”他们之中谁是这样的说了。
慌张的,胆小的,从人里面又闯到人里面,紧紧的挤在一块,又来到了街上。
“猪猡!”开车的伸出头来朝他们骂着。黑色的汽车擦着身走去了,差一点没有轧在那轮下。
看到对面飞来的黄包车,回头就让,又刚巧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在后边,血红的嘴里便吐出锐声的一句骂:“作死呀!”
土老儿便站在街的一角去商量了起来。商量了一会便又往前走,他们推举张大憨子打头里走,问路。张大憨子便用力睁着他的烂眼边,扭着一个笑脸,看见有和气点的人,便走上去问:
“请问乌家角往哪走?”
有的回答是摇一摇头,有的回答是:“大概是往西吧,走过去再问问。”
“嘿,看那群人,土里土气,”小娘儿们走过身时总要悄悄的指点着说。
“嘿,老龙!你看那边,那个赤身的小囡就像活的一样,有钱时买个小的回家去供在橱柜上倒不坏,”一些百货店里的东西,花花绿绿,真是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时时惹得他们去看,看着看着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走呀!走呀!找到了再说吧!”“嘿,乔三哥!上海的娘儿们才真怪模怪样,学的洋鬼子打扮找?”又有人说了起来,忘记了忧愁似的。
走过了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从比较热闹的地方走到卵石的马路,两边只剩一些低矮的瓦屋的地方来了。街的边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摊,摊的旁边,围着一些脏的孩子,揩着鼻涕,用眼钉着那摊上的花生。有更多的,罩一顶破帽的,顽皮得怕人的孩子们,在街心上揪着滚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车,推煤渣的小车,推粪的小车,吱吱呀呀,孔孔孔的小心的让着这群野马似的孩子们走过去。间或来了一部运货汽车,孩子们便叫啸着,跟着车后边追着跑,跑了一阵才又跑回来。这里也有脱毛的老狗,像没有家的,瘪着肚皮无力的躲在一边用着生疏的眼光来望过路的人。
他们又问,知道快到了,一缕高兴又升了上来,他们看到他们的一些希望,这希望也走近了一些,而太阳正高高的照着他们,走在头里的张大憨子便又说了起来:
“三年没有看见了,我姊夫真也是条好汉,下田做活,一个人当得两个人。也是运气不好,碰着过兵,拉去当了半年佚子,等他逃回来,东家的田早转把别人了,横竖田里也没有多少油头,盘缴不来,他一狠心离了家,带着老婆来上海,总算找着了一条出路,听说他也有十多块钱一月,我要有这门一个事也心满意足了。只是这时到他们家里去怕他不在家,不过我姊姊一定在家的。”
“张大哥!你找好了生意,可别丢开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是靠在你们身上的了……”乔老三又担心的说。
“哪里的话,咱们一块儿出来,当然有饭大家吃,我要先上工,我就借一点给你,你莫急。”张大憨子慷慨的说。
“要是你姊夫不在家,我们就去再找赵四爹。老龙,你娘舅住在哪块?”
“娘舅住在哪块我也弄不清,我晓得他是在东洋纱厂做工,到厂里一问终归就会明白的。”老龙这时忽然才想起,那年为一篮番薯,他同赵四爹打架,把赵四爹的头都伤了一大块,现在他却来到上海,求赵四爹替他找事情,怕不十分靠得住吧,于是他悄悄的悔着,同时又安慰着自己:“舅舅终归是舅舅,他总不好看着我饿死。”他们又问着,转进了一条小衡,衡后有几个院子,错综的立着三家小瓦屋四家小茅屋,虽说是冬天的太阳,也把那些院子里的垃圾晒出好些臭味来。
跨过了一个积水小潭,站在一个篾篱笆的门边,张大憨子便直着喉咙先喊了起来:
“李永发!李永发!”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的脸便从晒在竹篙上的尿布边伸了出来,鼓着诧异的大眼呆呆的望着,稀稀的黄发把那脸更弄得难看了。厢房边也伸出一个蓬发的头,在那头边的窗门上,也不知挂了些什么。房子两边杂乱的堆着一些破洋瓶,破瓦罐,破布条。房子里也好像有脚步走动,却没有人理睬他们。
“李永发!李永发!大姊……”
“阿发哥!阿发哥!好像有人找你!”是那蓬头发的声音。
从东边的房里走出李永发来,他赤着身,一手还举着短棉褂,他的赤色壮健的农人的胸脯,已经干瘪,他深陷的脸的轮廓也使张大憨子认不出了,可是他还认得张大憨子,他衣服也不穿上便摇着他的枯瘦的臂膀走了过来,抖着,笑着叫了起来:
“啊!憨子!你来啦!”
但是他马上便停住了笑声!他望见了憨子后边的一群,他不说话了。而憨子却说着,憨子以为自己会笑的,却没有笑,这改变了形象的姊夫,不只使他觉得生疏和同情,几乎是一个大的打击,他笑不出来,只说道:
“不认得你了,老啦,你害过病吗?大姊呢……”
“进来吧!你们一块来的吗,这是王阿二,我还认得你,唉,我却变了!做田到底还好点,进屋子里来吧!”他穿上短棉衣就引着进去。
外边屋子里摆了一屋子东西,床铺,煤炉子,刚好有一条走路通到里间。里间便是李永发花两块钱租来的一小间房。这一群人一走了进来就塞实了,习惯在阳光底下的眼睛,这间房更显得黑暗。李永发拖出了一条长板凳边让着又边问道:
“刚刚来上海吗?”
床上,蜷在乱棉絮里的一个妇人也哼着问了:“憨子吗?”
憨子走到床边去,这群人一句话也不说,有一些东西,一些未曾有过的东西来压在心上了。
“唉,憨子,你来得正好。你大姊天天都在念你们,想得要命,说是能看到屋里一株树也好,要是弄得到盘缠,早就和她回去了。去年的收成听说很好,不晓得回去弄它几亩田种种弄得到不?”“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并没有病过,就是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不消,机器把一身都榨干了,没有让机器轧死总算好,不过这条命……憨子,你们来做什么的?”
“憨子,家里还好吧,饭总该有得吃,我又小产了,那天厂里闹罢工,我摔了一跤。”妇人从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来,像个老女巫的面孔。
“唔,还好……”
“憨子!我们还是想回去,你帮忙替我们打听点生意好不好?上海实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来就两个多月。她又睡在床上。憨子!你们到底干吗的?”
张大憨子答应不出来,咬着嘴,望着这一对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亲戚的脸发气,已经找不到一点可以安慰他们的东西给这对快饿死的男女,而且他恼着他们,他把许多应该大发雷霆的罪过都加在这一对夫妇身上。他以为他们骗了他,骗了他们来上海,说是怎么容易找工做,怎么好赚银,他又恨他们的失业,他只想打他们一顿,或是把同来的人打一顿。但是同来的一群,也野兽般制住野性似的来恼着望他,像要同他相打似的,只有乔老三这时却忍不住在这些眈眈的虎视之中哭起来了。
晚上来了,太阳已经昏昏沉沉的落到一些屋子后边去。这群人还在街上奔着。同着他们一块儿奔着的,是那些放了工的走回家去的人们。他们用着羡慕的眼光去望着他们,而那些无力的挂倒着头,拖着疲倦的脚步的人们,只凝着痴呆困乏的灰色眼珠,茫然的望着前方,他们不能计较到身外的物事了。夹在这里奔着的,一还有那些苍黄的不像人样的女人们,头发上,衣服上都黏着从厂里带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从那些头上飞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他们望着望着,反觉得可怜他们起来了。可是薄弱的同情,抵不住自身的恐慌,于是又更焦躁了起来,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老龙叱道:“只晓得东洋厂,东洋厂,你不知道上海是有这样多的东洋厂吗?”
“我不晓得,你晓得!他从来就只说东洋厂……”
“不要吵,不要吵,还是找个地方喝口水,吃点东西吧,明天同我过浦东去。我叔叔前些日子来过信的,他准有生意,吵也没用。”李祥林排解着说。
“好吧,好吧,”张大憨子便跟着他们走到一个小菜馆,心里一边便想起了他睡在床上的姊姊,她小产了,只有一点小米粥吃,她很想买一块烧饼,烧饼里是夹得有点猪油,而他姊夫却不能让她满足。他想:“替她买几块吧,我身上总还有一元四角大洋……”他们坐在茶馆的一角,泡了一壶茶,各人从各人的包裹里掏出那剩下的一点干馍来啮着。空虚的肚皮就更空虚了起来似的,少量的麦粉填不满那比饥饿还厉害的欲望,王阿二又不耐烦的说了:“你叔叔住在那块,你清楚吗?”
“浦东贾家场,离英美烟厂不远,他在那里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约可以……”
“他就有生意,也不能养我们,他就替你找得到生意,不见得也替我们找得到,你没有看见他姊夫,就是个榜样,他那外边的两家人不也是坐着吃吗?”乔老三抢着来说。
“******,东洋厂,东洋厂……”老龙更握紧着拳头,他同赵四爹久已消溶的仇恨,又来在他心头,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来几然的望着前方,他们不能计较到身外的物事了。夹在这里奔着的,一还有那些苍黄的不像人样的女人们,头发上,衣服上都黏着从厂里带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从那些头上飞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他们望着望着,反觉得可怜他们起来了。可是薄弱的同情,抵不住自身的恐慌,于是又更焦躁了起来,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老龙叱道:“只晓得东洋厂,东洋厂,你不知道上海是有这样多的东洋厂吗?”
“我不晓得,你晓得!他从来就只说东洋厂……”
“不要吵,不要吵,还是找个地方喝口水,吃点东西吧,明天同我过浦东去。我叔叔前些日子来过信的,他准有生意,吵也没用。”李祥林排解着说。
“好吧,好吧,”张大憨子便跟着他们走到一个小菜馆,心里一边便想起了他睡在床上的姊姊,她小产了,只有一点小米粥吃,她很想买一块烧饼,烧饼里是夹得有点猪油,而他姊夫却不能让她满足。他想:“替她买几块吧,我身上总还有一元四角大洋……”他们坐在茶馆的一角,泡了一壶茶,各人从各人的包裹里掏出那剩下的一点于馍来啮着。空虚的肚皮就更空虚了起来似的,少量的麦粉填不满那比饥饿还厉害的欲望,王阿二又不耐烦的说了:“你叔叔住在那块,你清楚吗?”
“浦东贾家场,离英美烟厂不远,他在那里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约可以……”
“他就有生意,也不能养我们,他就替你找得到生意,不见得也替我们找得到,你没有看见他姊夫,就是个榜样,他那外边的两家人不也是坐着吃吗?”乔老三抢着来说。
“******,东洋厂,东洋厂……”老龙更握紧着拳头,他同赵四爹久已消溶的仇恨,又来在他心头,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来几槌。
隔座的几个人也在那里谈得很起劲,一个小伙子,穿一身破夹衣,灰色的脸,灰色的头发,最多也不过十六岁的身架,却一副苍老的面孔,他用力把他左手上的香烟吸了一口,右手画着圆形,便接下去说道:
“我听到一声口笛,心就一跳,知道不好了,果真啪啦啪啦啪啦的,哼,你知道死了多少,几十个工人就躺在地下啦,起码总有四五个活不转来。妈的,叫开枪的就是小王啦,他是副厂长,打死几个工人算什么,你要闹,他就索性把厂一关,看你几千人到什么地方去找饭吃。现在闹罢工啦,要凶手偿命,要抚恤金,要医药费……我说,都是空的,打死工人又不是刚有的事,罢工也不知罢过多少次了,从来还不是因为肚皮不争气,又复了工。我说,干脆打死他们,咱们自己难道不会开厂吗?”
另外一个年纪稍微大一些,也是灰色的脸和灰色的头发,他镇静的问道:“你打死谁?你要一动手,毛还没有挨着他一根,你就得吃生活,什么事都得慢慢来。现在还有些人信东家是好人,有些人宁愿饿死不敢动,有些又被资本家买去了当走狗来陷害工人,所以一切都得好好的来,坐在这里喊是没有用的,就是杀死几个厂长也还没有用。现在应该要让工人个个都明白,齐心起来站在一块拼命,所以要提条件,还不许开除工人,小五子,你莫要急,终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