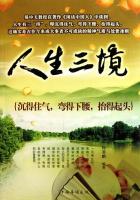凡耳聪目明的正常孩子,差不多都是在长辈的故事中长大的。其中就有我本人。
儿时,听着奶奶的“条帚疙瘩炊帚苗”(类似于《狼外婆》、父亲的《三侠五义》……)这些故事渐渐长大,渐渐懂事。先人们把他们的善恶观灌输给我,把忠孝节义的优良传统随便给我,直到我能独自“走路”——能独立从书本上索取我需要的知识。处世以来,我会按照古人的善恶标准来接人待物,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周围的人群里,拥有了比较不错的口碑。如此算来,像一位老作家说的,他是吃民间文学的奶长大的,此话不假,我也是。
以后就开始舞文弄墨。从文后,仍然接触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在写小说、诗歌之余,也搜集一些故事发表出去。同时,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些民间遗产。我感觉,老了,实在有些老了。故事是实用型的,它比不得文物。文物似乎是以历史久远为美,它的价值是由稀少难得所决定,无论它的样子到底美与不美。比如,周朝当时用鼎煮饭,而假如今天只要你用鼎煮饭,恐怕比起电饭锅、微波炉要差得多。为什么仍然崇拜鼎呢,因为鼎已经不再用来煮饭,而是有更重要的价值了。由是,鼎如有任何改装行为,可能贬值成废铜烂铁。故事却不然。故事要受众接受,必以能激起对方的审美快感为前提,这样才能让人家有耐心倾听。所以故事不是文物,那么,如套用文物的保管方式来传承故事,那无疑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在今天,奶奶那个“条帚疙瘩炊帚苗”的故事,连5岁的孩子也没有兴趣听下去,他们宁肯看《喜羊羊和灰太狼》。
那么,抱残守缺可能葬送故事,那可是祖祖辈辈下来的宝贵遗产呀。
于是,我决定改变故事,让故事的内容与形式都与时俱进,让它从奶奶或者父亲讲述的局限中超脱出来,带上创作者的智慧和时代的理念,这样,它才可以被读者接受,读者接受了,它才能完成其灌输某种理念,即所谓教育意义的任务。
当然,与时俱进不是某个人的发明,这是大势所趋,我等改良故事的作家,无非是被潮流推动而已。
于是,磕磕绊绊中,我创作,发表了一两百万字的传统故事。不是我有意颠覆故事的套路,我是不断揣摩着读者的心理或者说编辑的心理,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这种改良的。
感谢故事养育了孩童时代的我。感谢故事充实了成人阶段的我。
这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三本传统故事集。在当下传统故事写手中,有一两百万字的作者不会很多,但发表多少只是个量的观念,它不是质。假如能留下点精品,那才是我的追求。去年春节,得杂咏七首,录其一,以志。诗曰:
羞煞当年懵懂时,错将浮浅作才思。
狂吟妄吼七千步,不及陈王一句诗。
此是我的观点。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抵得上半句陈王曹植的诗作,能在读者中流传开来,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