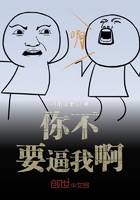就在远难和十里一徘徊饭馆老板说话这功夫,远难用钓鱼的铅堕打死两个便衣的现场,又来了四个便衣和一条警犬,那条警犬从渔具店到现场走了两个来回,又转身边嗅边向日升旅馆走去,在距离日升旅馆十来丈远的时候,先前发生在那两条警犬身上的一幕又重复再现了,那条警犬用前爪抓挠一阵它的鼻子后,转身往回就跑,任凭训犬的警察怎么引导,怎么诱使,它就是不干了,它也干不了啦,因为它废了。
四个警察把警犬放在一边,冲进了日升旅馆,一会的功夫,把刘福和远难丢弃的衣服连同店小二带出了门外,一个警察问店小二:“那两个人往哪个方向走了?”店小二一指十里一徘徊饭馆说:“就那个方向。”
四个警察留下一个看护警犬,三个警察就向十里一徘徊饭馆的方向巡查过来,来到十里一徘徊饭馆门口的时候,正赶上刘福远难从屋里往外走。两伙人,不,是查与被查,抓与被抓的两伙人,刚好碰了个照面。三个警察站下了,刘福和远难也站下了,送出来的饭馆老板也竖在那了。
双方对视了一会,谁也没服谁。远难开口了:“有鼓快打,有锣快敲,有屁快放,有话快说,别挡了我的财路。”领头的警察这时候说话了:“哈哈,你还挺横。说,你们两人是干啥的?”远难一摆手说:“错,仨。”领头的警察问:“那个哪?不是后边那个吧?”“那个打前站安排住处去了。”“哈哈,还挺有谱呢。你还没说呢,干啥的!”领头的警察把后边干啥的三个字说的挺重,口气也更硬了。“干粗活、怕累,干巧活、不会,干细活、心碎,干俏活、不会献媚;做买卖、怕赔,想跟班、不会溜须,充混混、怕遇鬼,做土匪,怕后悔;想讨饭、怕遭罪,想发财、没福气,做慈善、没财力,做损事、怕打雷;当孙子、怕跪,当爷、怕驼背,当快腿、不会说媒,当差、怕说没心没肺;干你们这行,路子不对,想当官,皇上没招我东床为婿;你再问我干啥?都是眼泪。”远难一口气叨念完了,领头的警察笑了:“嘿嘿,照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能再问你了,油腔滑调的,想你也干不了那种杀杀砍砍的事,走吧,唱你的戏去吧。”
上梁的绳子,烈日下的鼓,两牤子刨地,熊遇上虎。这么紧紧绷绷的事,这样一触既发的瞬息,让人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让人的血都要凝了。可这样雷鸣电闪的事,这样黑云盖地的境遇,让远难这么一说,就浓阴转大睛了。远难一拱手说:“谢了。”说着就前走,刚迈出一步,”“站下,”警察喊完站下,接着又说话了:“这么简单?不行,我今晚非要看你的戏,有票吗?”这个领头的警察还不拉倒了。远难只得顺杆爬的说:“有,在我管家手呢,一会给你送去,哪个局子?”“好了,北市场警务分局,我叫杨贵恩。我们走了,记住喽,我在局里等你的戏票。”
三个警察走了。饭馆老板这才加了两步,走到刘福和远难面前说:“哎哟,把我的屁都吓凉了。”他又指了指远难说:“你这一大套,把那三警察眼睛都听直了,哈哈,还要看你的戏呢。”
刘福、远难和十里一徘徊饭馆的老板告别后,两人溜溜达达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刘福停住了脚步,他问远难:“咱上哪去呀?不能这么漫无边际的走哇。”“大哥,找个地方,咱先住下,明天和刘祥见了面再商量下一步。”“行。”
两人往前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一个旅馆前,见匾额上四个字刻写得雅致融情,这四个字是瑞气祥天。“字好,名也妙,就住这。”刘福说完,两人进了大堂,被人领到房间门口,进去了一看,远难说:“这个房间吗,比那个强多了。”刘福说:“天下没有花钱的不是,花啥钱享啥福。”远难说:“大哥,就享受享受吧,钱我来弄。”“哎呀,老弟呀,你可悠着点吧,这家伙的,没点胆的,心都蹦到肚皮外边去了。”正说着呢,这时候有人敲门。“谁?”远难边问边打开门,一看是服务生。服务生问:“先生,我是您房间的服务生,有事您吩咐,我会做得让您满意的。”远难说:“正想问你呢,沈阳哪家戏院好?”“人和呀。”远难吩咐说:“买五张戏票去。”“行。”“等一下。买完戏票,找个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一不认识谁的,把戏票给北市场警务分局的杨贵恩警官送去。记住,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认识谁。”“放心,这事我会办。”服务生接过钱走了。
刘福和远难哥俩住下后,也没出去,晚上要了盒点心就着开水吃了。这俩天过的,也没着消停啊,远程奔窜,躲避查问;不知去哪,身无分文;为恨出手,杀了五人;老天保佑,还算安稳。这阵折腾,乏了,累了,疲了,困了。哥俩的脑袋一挨上枕头,就合上了大眼睛,打起小呼噜;心在梦里,身在雾中;糊天罩地,越睡越沉,越睡越香;身在沈阳城,一觉到天明;等到哥俩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照腚,升起一杆子高了。
十里一徘徊饭馆的斜对面,有个茶馆,叫茗气东来。刘福和远难一早爬起,拉撒干净,洗漱利落,穿戴齐整,迈着方步走进了茗气东来。找了个临街靠窗能看清十里一徘徊饭馆的位置坐下。要了一盒点心,一碟干果,一盘五香牛筋,一壶陈年普洱茶。哥俩漫不经心,漫无边际的边吃边唠边看。
刘福和远难如今已经是满沈阳的军警宪特翻箱倒柜,翻江倒海,翻天覆地查找的超级杀手和刺客。如果是一般的人,早就躲出去十万八千里了,而且是躲的越远越好。这些个小常识谁都懂。可刘福和远难不能躲,也不能走。刘家烧锅大院眨眼间,三百几十口人被日本鬼子杀绝了,阴差阳错,分散南北,各去东西躲过了劫数的三个大命之人,鬼使神差般的又相见于离家五百多里外的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而且见得突然,分得迅速,好多话没说,好多事没问,好多的怎么办没商量没确定,刘祥却意志坚定的走了。今天是三人双方约定见面的日子,而且具体时间没确定。所以,刘福和远难哥俩一早起来就商定早去早等,免得错过机会。原来约定在十里一徘徊饭馆,可昨天在那杀了两个日本军官,离开后又重返过去了,要命的是还管人家饭馆老板要了钱。草活一身绿,树活一层皮,花活一朵艳,人活一张脸。十里一徘徊饭馆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暂时是不能进了。眼下只能选茗气东来了,这个茶馆档次高,闲人少,好躲藏,看得着。
刘福和远难从日上三杆到日升中午,再到日头偏西,哥俩是边吃边喝,边唠边等,身子不离桌,屁股不离坐,屎不敢多拉,尿没敢多撒,不敢错眼珠的盯视着十里一徘徊饭馆的门。屁股疼了,抬抬;腰坐板了,扭扭;脖子沉了,转转;眼睛酸了,揉揉。可就是没看见刘祥的影。
桌面上同样的东西上了三遍,好水喝了九壶。眼瞅着天黑了,灯亮了,可哥俩想看的人一直没看着。
茗气东来茶馆里的服务生,起初以为这俩人是吃早茶点的,后来又看出来是等人的。干这种营生的,都有这个心理,花钱不多,长期占桌,他烦。可又不到万不得以,找借口撵的话,又不能出口。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伙计是后锅的水,响(想)开了,清楚了,知道了,等伙计明白的时候,吓得他们直伸舌头,庆幸自己没把撵的话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