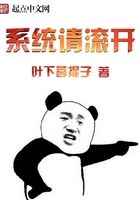开会突然想起张老太过世前些日子的那个傍晚,文炳藏在麦地里,浑身战栗的说他看见有个黑影从麦地里一闪而过,莫非那是去拿张老太魂魄的黑无常?开会把文炳叫到身旁,神情严肃的问那天晚上看到的黑影到底是啥样,文炳却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开会更莫名其妙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该问吗?
“我怕你们骂我,就编出来吓你们的。”说完就很得意的跑开了。
开会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庆幸,文炳从会说话会走路开始就诡计多端防不胜防,他和慧芳经常被儿子耍得团团转。
队里已经把阴阳先生请到位了,阴阳先生并不是圆眼镜老先生,他只是到处晃荡着给人算命赚些零碎钱,顺便再给人牵牵红线做做媒,他算命准不准先不说,但他一直在接触外界,获得了更多人的信息,比如给福顺和芸香算姻缘,或许这两人的结合有他催化的功劳,但逢上这种连环的凶死事件,岂是他掐掐手指头动动嘴皮子就能降服的?
请来的阴阳先生是远近有名的,做法事也很灵验。他吩咐队里的小伙子们要在今夜趁着天黑去偷一盘磨回来,然后用这盘磨下咒语镇住作怪的妖孽。
下午时分,队里闲着无事的人都来到了王大年家,阴阳先生正趴在桌子上写符字,人们自告奋勇的替他研墨铺红纸,他右手执笔轻轻一挥洒,一纸漂亮的符字就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有人发出啧啧的称赞声,阴阳先生只是淡淡一笑。符字是和对联差不多的,都是在红纸上写下笔迹清晰刚劲有力的黑墨毛笔字。但接下来画的桃符就不一样了,阴阳先生换了支细细的软笔,在裁成细条的红纸上照着泛黄书页上的模板画了起来,像画画,又像写字,但没人知道具体是什么。
终于等到了晚上,阴阳先生挑了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福顺、开会、福生,还有又高又壮的杀猪匠学徒二愣子,阴阳先生再三交代偷石磨时不能被主人发现。经过一番协商,他们把偷磨的地址选在河对面的那个生产队,一是对这个生产队的村民布局情况基本熟悉,二是离做法事的场地近,一口气就跑回来了,省得浪费时间和力气。
夜已三更,对面生产队各家各户陆续的关上灯,进入了熟睡状态,这一夜没有月亮,天阴沉沉的,两面山皆是一片暗黑。二愣子打头,福生紧随其后,开会走第三,福顺走最后面,一路上四个人轻声细语的商量着偷磨时的注意事项,比如怎么偷,偷完以后怎么搬走,谁和谁先抬,谁和谁后抬。二愣子在前面感慨道:“没想到这辈子还会这样光明正大的去偷东西!”
“莫乱说话,又不是让你去偷磨搞玩意儿,这种时候应该严肃,你看我,现在大气都不敢出。”开会一本正经的说道。
但是,人有时候嘴巴争了气,身体却献了丑,开会的身后传出“吥”的一声,此刻周围特别安静,他故作镇定的解释道:“哎,小豆(红豆)好吃,容易漏气。”
“有些人这会儿是在羞先人!”二愣子幸灾乐祸的说。
开会不理二愣子,但奇怪的是福顺竟然没取笑他,换做往日,早就把他嘲笑得都不知道羞耻是什么了,这会儿福顺一句话不说反而激发了他心中的羞耻感,他终于忍不住问道:“顺子,你咋一句话都不说?”
福顺张着嘴畅快的换了一口气,“这种时候应该严肃,我连气都不敢出。”
轻车熟路的走进一户石磨安在吊脚楼下的人家,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远处的两只看家狗在对着狂吠,屋里传出男主人滚雷般的鼾声。开会小心翼翼的抬了一下石磨,然后打着手势比着口型示意二愣子过来帮忙,二愣子弯腰拾起一根手腕粗细的木棒,穿进磨眼里,两只手稍微一用力就将木棒扛在了肩上。福生感叹说:“这饭没白吃啊!”
前面福顺开道,后面福生压阵,二愣子单肩轻松的扛着石磨就回来了。
阴阳先生开始请神,他神态虔诚,口中念念有词,偶尔端起一杯白酒洒在燃烧着的用百元人民币一拃一拃印好的钱纸上。而后就是招魂,要把那些作怪的以及凶逝者的魂魄招回来,阴阳先生面前放着一只碗,盛了半碗水,他的口中依旧念念有词,一边念叨一边往水中放置燃烧着的钱纸,终于,一只飞蛾径直扑向了水中,瞬间就被淹死了。阴阳先生提醒大伙儿要保持安静,他马上就要将这化作飞蛾的鬼魅封死在这碗中。人们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的盯着那只碗,只见阴阳先生拿起钱纸,突然将碗口封死了,人堆里传出一声惊呼——“快听”,人们都放大了瞳孔竖起了耳朵,似乎是从尖子山山腰上的悬崖下传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但很快就消失了。阴阳先生把写着咒语的桃符依次贴在石磨上,然后指挥着小伙子们将石磨和被钱纸封死的碗埋在一个地势开阔的地方,保佑每一户人家都平安顺畅,并标上记号,叮嘱人们不能挖掘这一小片土地,谁碰了鬼魂谁家就会被祸害。
而后的日子,人们路过这里都会上去狠狠地踩上几脚,恨不得把这些鬼魂踩得永无翻身之日。下镇的消息慢慢的止住了谣言,乡民们也不再天黑就闭门不出,而且陆陆续续的,队里添了三个女娃娃,分别是巧捷、文炳和琳琳的妹妹。文炳妹妹文静出生的时候,文炳激动得坐立难安,趴在紧闭着的门上边敲打边哭喊着:“开门,我要进去看我妈生妹妹,开门呐!”屋外的亲戚把他抱过来,他手抓脚踢地挣脱下去,两三步跑过去又贴在门板上哭喊起来。
说来也神奇,自从阴阳先生整治以后,竹坪坝又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