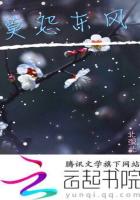妈妈?!
相思猝然抬头,迎上他的目光,一颗心倏然被提到了头顶,她突然觉得喘不过气,半晌,才有些迟钝的问:“你,是谁?为什么,为什么会认识我妈妈?”
尹西南放下手中的茶杯,目光依稀渗出些慈悯,他重重的叹息,口吻却柔和下来,“如果你真的是他们的孩子,那我,便是你的伯父。”
“啪!”的一声脆响,相思手中的茶盏翻落在檀木长几上,滚烫的茶水还冒着氤氲的热气,那灼热的温度却不像是溅在她手背上,反而像是一杯热茶倾盏而下,滚烫的沸水直直浇在她心尖上,疼的整个人都簌簌发颤。
他是——,心里有呼之欲出的答案,她却说不出一个字。如何能信?怎样去相信,眼前的这个人,这个仅有过一面之缘,叱咤风云的男人,竟自称是她的伯父,那么,他的手足,他的兄弟,便是她的——父亲?!
那个在她生命中从未出现过的称呼,那个她活了二十多年,也从未触及过一分一毫的人,现在就这样被推及到面前,她如何能信?
尹西南看出她眼中的惊慌和错愕,起身走到办公桌后面的保险箱,输入密码,然后探身取出里面的物件,交到她手上。
相思恍惚低头去看,是一幅画卷,和一本手札小册。
她指尖拂过那蓝色的小册,竟是微微发抖,不敢翻开。
“打开看看吧,这全是他……是你父亲写给你母亲的信笺,只是从未寄出,经年累积,才装订成册的。”
相思坐在那里,呼吸渐渐沉缓,她的父亲,她的爸爸,那样近有那样远的一个人,这是他的东西,是他写给妈妈的信。这些年的痴盼与等候,最终,只换来了这一册厚厚的手迹。
她只觉得脑子混沌不堪,似是要不能思考,终于,缓缓翻开扉页。
霍然映入眼帘的不是字迹,竟是一帧夹在手札首页的老照片,或是时隔久远,照片一角已经落落泛黄,像是岁月的水纹缠绵而过,留下让人嘘唏的痕迹。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一眼便认出来,照片上抚琴的女子眉目低垂,侧颜温婉娴静,穿着一袭月白色旗袍,嘴角噙着一丝浅笑,那是年轻时的妈妈!
眼泪汹涌而出,模糊了视线,但相思还是忍不住去看那个站立在妈妈身边的男子,她从未见过他,从小到大更没有从旁人口中听得过丝毫有关于他的描摹,今天见了这张照片,才知道,他竟是那样一个男子,犹如玉树兰芝,眉目轻浅,却淡薄风雅自顾风流。
这就是他?她,父亲?
照片上的二人眉眼如画,宛如佳偶天成,伉俪情浓。
眼泪“吧嗒吧嗒”的成串坠落,碎在照片上,化开一片水迹,她慌忙用手擦拭,小心妥帖的将照片重新夹在手札中,却再没有勇气去翻看那本子上的字迹。
本是这样的一对璧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能长相厮守?最后徒留照片上的女子守着回忆,望断一生?
她不敢去窥探,只怕那照片背后的故事会让人心悸绝望,不管曾经是如何的月下花前,魂梦相通,这结局,终是她母亲枯荣一生,可郎心似海,这一腔痴情他到底是辜负了。
尹西南将纸巾递到她面前,一贯沉稳的声音掺杂了不易察觉的哀凉:“现在你相信了?相思,我是你伯父,这照片上的男人,是我的弟弟,你的父亲。”
“这几年,我一直在四处探寻你们母女的下落,但是却一无所获,直到上次在C市偶然遇见你,我几乎便一眼认定,你一定逸桓和素盈的孩子,是我的侄女,你和你妈妈年轻时长得太像了,几乎是一模一样……”
是了,素盈,那是妈妈的名字,如同她的人,她的一生,素雅盈淡,深情永默。
她只是从来不知,她的父亲,那个她臆想过无数次也怨怼过无数次的人,竟唤作逸桓,逸桓,尹逸桓。
她终于抬起头,目光哀切悲凉,问:“他人呢?”
尹西南想要开口,却顿住,面色一时颓败,许久才说:“他,早年被查出胰腺癌,三年前,过世了。”
整个世界像是被按了暂停的唱机,安静的再没有一丝声响,相思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是没有温度,一下下,反复却麻木的在胸膛跳动,一下下,再一下下,仿佛旷野的响过的闷雷,生生锤击在心口,迟钝却快意的疼痛。
她几乎要失笑出声,命运的际遇果真是滑稽可笑,最终控制不住,还是笑了出来,尹西南见她面如纸白毫无血色,眼神却凉薄讥诮,心中只觉得疼惜。虽然此前的人生并无交集,更无亲近可言,但这毕竟是他弟弟唯一的女儿,他唯一的侄女,血浓于水,他无法不垂爱呵护,他甚至不敢想象这些年她是怎样与母亲相依为命,饱尝世间人情冷暖,犹如荒漠戈壁上生长的嫩芽,如何坎坷却顽强的长大。
她似是花了好大力气才堪堪止住笑,语气中的嘲弄却是掩盖不住,她睫畔还残留泪珠,却迟迟不再落下。相思伸出手指点了点桌上的手札小册和那幅未曾展开的画轴,问:“去世了?三年前?那这些呢?你现在给我看这些,有什么用呢?缅怀?追念?未免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