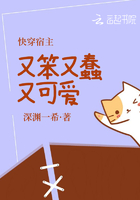更进一步说,心的旅行也不以存在的世界为限!上帝的乐园,它是要去的;阎罗的十殿,它也是要去的。爱神的弓箭,它是要看看的;孙行者的金箍棒,它也要看看的。总之,神话的世界,它要穿上梦的鞋去走一趟。它从神话的世界回来时,便道又可游玩童话的世界。在那里有苍蝇目中的天地,有永远不去的春天;在那里鸟能唱歌,水也能唱歌,风也能唱歌;在那里有着靴的猫,有在背心里掏出表来的兔子;在那里有水晶的宫殿,带着小白翼子的天使。童话的世界的那边,还有许多邻国,叫做乌托邦,它也可迂道一往观的。姑举一二给你看看。你知道吴稚晖先生是崇拜物质文明的,他的乌托邦自然也是物质文明的。他说,将来大同世界实现时,街上都该铺大红缎子。他在春晖中学校讲演时,曾指着“电灯开关”说:
科学发达了,我们讲完的时候,啤啼叭哒几声,要到房里去的就到了房里,要到宁波的就到了宁波,要到杭州的就到了杭州:这也算不来什么奇事。(见《春晖》二十九期。)
呀!啤啼叭哒几声,心已到了铺着大红缎子的街上了!——若容我借了法朗士的话来说,这些正是“灵魂的冒险”呀。
上面说的都是“大头天话”,现在要说些小玩意儿,新新耳目,所谓能放能收也。我曾说书籍可作心的旅行的向导,现在就谈读书吧。周作人先生说他目下只想无事时喝点茶,读点新书。喝茶我是无可无不可,读新书却很高兴!读新书有如幼时看西洋景,一页一页都有活鲜鲜的意思;又如到一个新地方,见一个新朋友。读新出版的杂志,也正是如此,或者更闹热些。读新书如吃时鲜鲥鱼,读新杂志如到惠罗公司去看新到的货色。我还喜欢读冷僻的书。冷僻的书因为冷僻的缘故,在我觉着和新书一样;仿佛旁人都不熟悉,只我有此眼福,便高兴了。我之所以喜欢搜阅各种笔记,就是这个缘故。尺牍,日记等,也是我所爱读的;因为原是随随便便,老老实实地写来,不露咬牙切齿的样子,便更加亲切,不知不觉将人招了入内。同样的理由,我爱读野史和逸事;在它们里,我见着活泼泼的真实的人。——它们所记,虽只一言一动之微,却包蕴着全个的性格;最要紧的,包蕴着与众不同的趣味。旧有的《世说新语》,新出的《欧美逸话》,都曾给我满足。我又爱读游记;这也是穷措大替代旅行之一法,从前的雅人叫做“卧游”的便是。从游记里,至少可以“知道”些异域的风土人情;好一些,还可以培养些异域的情调。前年在温州师范学校图书馆中,翻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目录,里面全(?)是游记,虽然已是过时货,却颇引起我的向往之诚。“这许多好东西哟!”尽这般地想着;但终于没有勇气去借来细看,真是很可恨的!后来,《徐霞客游记》石印出版,我的朋友买了一部,我又欲读不能!近顷《南洋旅行漫记》和《山野掇拾》出来了,我便赶紧买得,复仇似地读完,这才舒服了。我因为好奇,看报看杂志,也有特别的脾气。看报我总是先看封面广告的。一面是要找些新书,一面是要找些新闻;广告里的新闻,虽然是不正式的,或者算不得新闻,也未可知,但都是第一身第二身的,有时比第三身的正文还值得注意呢。譬如那回中华制糖公司董事的互讦,我看得真是热闹煞了!又如“印送安士全书”的广告,“读报至此,请念三声阿弥陀佛”的广告,真是“好聪明的糊涂法子”!看杂志我是先查补白,好寻着些轻松而隽永的东西:或名人的趣语,或当世的珍闻,零金碎玉,更见异彩!——请看“二千年前玉门关外一封情书”,“时新旦角戏”等标题便知分晓。
我不是曾恭维看报么?假如要参加种种趣味的聚会,那也非看报不可。譬如前一两星期,报上登着世界短跑家要在上海试跑;我若在上海,一定要去看看跑是如何短法?又如本月十六日上海北四川路有洋狗展览会,说有四百头之多;想到那高低不齐的个儿,松密互映,纯驳争辉的毛片,或嘤嘤或呜呜或汪汪的吠声,我也极愿意去的。又我记得在《上海七日刊》(?)上见过一幅法国儿童同乐会的摄影。摄影中济济一堂的满是儿童——这其间自然还有些抱着的母亲,领着的父亲,但不过二三人,容我用了四舍五入法,将他们略去吧。那前面的几个,丰腴圆润的宠儿,覆额的短发,精赤的小腿,我现在还记着呢。最可笑的,高高的房子,塞满了这些儿童,还空着大半截,大半截;若塞满了我们,空气一定是没有那么舒服的,便宜了空气了!这种聚会不用说是极使我高兴的!只是我便在上海,也未必能去;说来可恨恨!这里却要引起我别的感慨,我不说了。此外如音乐会,绘画展览会,我都乐于赴会的。四年前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曾到上海市政厅去听“中西音乐大会”;那几支广东小调唱得真入神,靡靡是靡靡到了极点,令人欢喜赞叹!而歌者隐身幕内,不露一丝色相,尤动人无穷之思!绘画展览会,我在北京,上海也曾看过几回。但都像走马看花似的,不能自知冷暖——我真是太外行了,只好慢慢来吧。我却最爱看跳舞。五六年前的正月初三的夜里,我看了一个意大利女子的跳舞:黄昏的电灯光映着她裸露的微红的两臂,和游泳衣似的粉红的舞装;那腰真软得可怜,和麦粉搓成的一般。她两手擎着小小的钹,钹孔里拖着深红布的提头;她舞时两臂不住地向各方扇动,两足不住地来往跳跃,钹声便不住地清脆地响着——她舞得如飞一样,全身的曲线真是瞬息万变,转转不穷,如闪电吐舌,如星星眨眼;使人目眩心摇,不能自主。我看过了,恍然若失!从此我便喜欢跳舞。前年暑假时,我到上海,刚碰着卡尔登影戏院开演跳舞片的末一晚,我没有能去一看。次日写信去“特烦”,却如泥牛入海;至今引为憾事!我在北京读书时,又颇爱听旧戏;因为究竟是“外江”人,更爱听旦角戏,尤爱听尚小云的戏,——但你别疑猜,我却不曾用这支笔去捧过谁。我并不懂戏词,甚至连情节也不甚仔细,只爱那宛转凄凉的音调和楚楚可怜的情韵。我在理论上也左袒新戏,但那时的北京实在没有可称为新戏的新戏给我看;我的心也就渐渐冷了。南归以后,新戏固然和北京是“一丘之貉”,旧戏也就每况愈下,毫无足观。我也看过一回机关戏,但只足以广见闻,无深长的趣味可言。直到去年,上海戏剧协社演《少奶奶的扇子》,朋友们都说颇有些意思——在所曾寓目的新戏中,这是得未曾有的。又实验剧社演《葡萄仙子》,也极负时誉;黎明晖女士所唱“可怜的秋香”一句,真是脍炙人口——便是不曾看过这戏的我,听人说了此句,也会有“一种薄醉似的感觉,超乎平常所谓舒适以上”。——《少奶奶的扇子》,我也还无一面之缘——真非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不可!上海的朋友们又常向我称述影戏;但我之于影戏,还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呢!也只好慢慢来吧。说起先施公司,我总想起惠罗公司。我常在报纸的后幅看见他家的广告,满幅画着新货色的图样,真是日本书店里所谓“诱惑状”了。我想若常去看看新货色,也是一乐。最好能让我自由地鉴赏地看一回;心爱的也不一定买来,只须多多地,重重地看上几眼,便可权当占有了——朋友有新东西的时候,我常常把玩不肯释手,便是这个主意。
若目下不能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或到上海而无本钱去开先施公司,则还有个经济的办法,我现在正用着呢。不过这种办法,便是开先施公司,也可同时采用的;因为我们原希望“多多益善”呀。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没有绘画展览会;但我和人家借了左一册右一册的摄影集,画片集,也可使我的眼睛饱餐一顿。我看见“群羊”,在那淡远的旷原中,披着乳一样白,丝一样软的羽衣的小东西,真和浮在浅浅的梦里的仙女一般。我看见“夕云”,地上是疏疏的树木,偃蹇欹侧作势,仿佛和天上的乱云负固似的;那云是层层叠叠的,错错落落的,斑斑驳驳的,使我觉得天是这样厚,这样厚的!我看见“五月雨”,是那般蒙蒙密密的一片,三个模糊的日本女子,正各张着有一道白圈儿的纸伞,在台阶上走着,走上一个什么坛去呢;那边还有两个人,却只剩了影儿!我看见“现在与未来”;这是一个人坐着,左手托着一个骷髅,两眼凝视着,右手正支颐默想着。这还是摄影呢,画片更是美不胜收了!弥爱的《晚祷》是世界的名作,不用说了。意大利Gino的名画《跳舞》,满是跃着的腿儿,牵着的臂儿,并着的脸儿;红的,黄的,白的,蓝的,黑的,一片片地飞舞着——那边还攒动着无数的头呢。是夜的繁华哟!是肉的熏蒸哟!还有日本中泽弘光的《夕潮》:红红的落照轻轻地涂在玲珑的水阁上;阁之前浅蓝的潮里,伫立着白衣编发的少女,伴着两只天矫的白鹤;她们因水光的映射,这时都微微地蓝了;她只扭转头凝视那斜阳的颜色。又椎冢猪知雄的《花》,三个样式不同,花色互异的精巧的瓶子,分插着红白各色的,大的小的鲜花,都丰丰满满的。另有一个细长的和一个荸荠样的瓶子,放在三个大瓶之前和之间;一高一矮,甚是别致,也都插着鲜花,只一瓶是小朵的,一瓶是大朵的。我说的已多了——还有图案画,有时带着野蛮人和儿童的风味,也是我所爱的。书籍中的插画,偶然也有很好的;如什么书里有一幅画。显示惠士敏斯特大寺的里面,那是很伟大的——正如我在灵隐寺的高深的大殿里一般。而房龙《人类的故事》中的插画,尤其别有心思,马上可以引入到他所画的天地中去。
我所在的地方,也没有音乐会。幸而有留声机,机片里中外歌曲乃至国语唱歌都有;我的双耳尚不至太寂寞的。我或向人借来自开自听,或到别人寓处去听,这也是“揩油”之一道了。大约借留声机,借画片,借书,总还算是雅事,不致像借钱一样,要看人家脸孔的(虽然也不免有例外);所以有时竟可大大方方地揩油。自然,自己的油有时也当大大方方地被别人揩的。关于留声机,北平有零卖一法。一个人背了话匣子(即留声机)和唱片,沿街叫卖;若要买的,就喊他进屋里,让他开唱几片,照定价给他铜子——唱完了,他仍旧将那话匣子等用蓝布包起,背了出门去。我们做学生时,每当冬夜无聊,常常破费几个铜子,买他几曲听听:虽然没有佳片,却也算消寒之一法。听说南方也有做这项生意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宁波是其一。宁波S中学现有无线电话收音机,我很想去听听大陆报馆的音乐。这比留声机又好了!不但声音更是亲切,且花样日日翻新;二者相差,何可以道里计呢!除此以外,朋友们的箫声与笛韵,也是很可过瘾的;但这看似易得而实难,因为好手甚少。我从前有一位朋友,吹箫极悲酸幽抑之致,我最不能忘怀!现在他从外国回来,我们久不见面,也未写信,不知他还能来一点儿否?
内地虽没有惠罗公司,却总有古董店,尽可以对付一气。我们看看古瓷的细润秀美,古泉币的陆离斑驳,古玉的丰腴有泽,古印的肃肃有仪,胸襟也可豁然开朗。况内地更有好处,为五方杂处,众目具瞻的上海等处所不及的;如花木的趣味,盆栽的趣味便是。上海的匆忙使一般人想不到白鸽笼外还有天地;花是怎样美丽,树是怎样青青,他们似乎早已忘怀了!这是我的朋友郢君所常常不平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在上海人怕只是一场春梦吧!像我所在的乡间:芊芊的碧草踏在脚上软软的,正像吃樱花糖;花是只管开着,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杨贵妃一般的木笔,红着脸的桃花,白着脸的绣球……好一个“香遍满,色遍满的花儿的都”呀!上海是不容易有的!我所以虽向慕上海式的繁华,但也不舍我所在的白马湖的幽静。我爱白马湖的花木,我爱s家的盆栽——这其间有诗有画,我且说给你。一盆是小小的竹子,栽在方的小白石盆里;细细的干子疏疏的隔着,疏疏的叶子淡淡地撇着,更点缀上两三块小石头;颇有静远之意。上灯时,影子写在壁上,尤其清隽可亲。另一盆是棕竹,瘦削的干子亭亭地立着;下部是绿绿的,上部颇劲健地坼着几片长长的叶子,叶根有细极细极的棕丝网着。这像一个丰神俊朗而蓄着微须的少年。这种淡白的趣味,也自是天地间不可少的。
天地间还有一种不可少的趣味,也是简便易得到的,这是“谈天”。——普通话叫做“闲谈”;但我以“谈天”二字,更能说出那“闲旷”的味儿!傅孟真先生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一评里,引顾宁人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说“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谈天”大概也只能算“不及义”的言;纵有“及义”的时候,也只是偶然碰到,并非立意如此。若立意要“及义”,那便不是“谈天”而是“讲茶”了。“讲茶”也有“讲茶”的意思,但非我所要说。“终日言不及义”,诚哉是无益之事;而且岂不疲倦?“舌敝唇焦”,也未免“穷斯滥矣”!不过偶尔“茶余酒后”,“月白风清”,约两个密友,吸着烟卷儿,尝着时新果子,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等到兴尽意阑,便各自回去睡觉;明早一觉醒来,再各奔前程,修持“胜业”,想也不致耽误的。或当公私交集,身心俱倦之后,约几个相知到公园里散散步,不愿散步时,便到绿荫下长椅上坐着;这时作无定向的谈话,也是极有意味的。至于“‘辟克匿克’来江边”,那更非“谈天”不可!我想这种“谈天”,无论如何,总不能算是大过吧。人家说清谈亡了晋朝,我觉得这未免是栽赃的办法。请问晋人的清谈,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且不说,我单觉得清谈也正是一种“生活之艺术”,只要有节制。有的如针尖的微触,有的如剪刀的一断;恰像吹皱一池春水,你的心便会这般这般了。“谈天”本不想求其有用,但有时也有大用;英哲洛克(Locke)的名著《人间悟性论》中述他著书之由——说有一日,与朋友们谈天,端绪愈引而愈远,不知所从来,也不知所届;他忽然惊异:人知的界限在何处呢?这便是他的大作最初的启示了。——这是我的一位先生亲口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