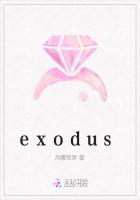蔡学利
平坦如坻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陇塬,在五月金色的季节,穿上了金灿灿黄艳艳的绚丽衣裳。
麦子黄了,大地上一片片金黄色的海洋,微风过处,掀起一层层金色浪潮。正在拔节的玉葱儿样半人高的玉米苗和一棵棵一簇簇青翠碧绿的树木,映衬的麦黄浪潮汹涌逼人而来。火辣辣的太阳暴躁起来,农人们心热起来,走路的脚步声快得能擦出火星,上集买扫帚、连枷、镰刀,早早地割几斤肉,做成肥肥的臊子,称上十斤上好的胡油,炸一大缸油饼,放在屋角当零食吃,磨好柔柔的白面,洗好衣服……一切都在为割麦做准备,邻里互相招呼都是麦事,“(麦)黄了吗?”“快了!快了!”一边急急地答,一边快快地走。
农家院中比平日寂静了许多。两只芦花鸡孤独地在树荫下翻着粪堆,大黄狗悄悄地卧在门洞中伸展着舌头纳凉,连平常爱哼哼的老母猪也静静地躺在圈中休息,它知道这时就是再哼哼也没有人顾得上理它,老黄牛在树荫下慢悠悠地反刍,它正在安然地享受一个短期假日。
太阳早早地就从东边麦梢上射向高空,把亿万颗热烈倾泄向大地上的一切,农人们心里热乎乎地洋溢着一股喜悦,火辣辣的天气才是割麦的好天气,以前冒雨耕种泥里水里的一塌糊涂,为地畔犁沟和邻居打架,为种什么种籽和妻子吵嘴,赊化肥,灭虫,除草,施肥,灌水等等,生得那些疙里疙瘩气呀,都因为麦收在即而变得有意义起来。
爷爷起得最早,开门看天色,麦地里看成色,嚓嚓嚓地磨镰,磨了一把又一把,最后还找出一把早已不用的老镰刀也磨了磨,那是给14岁的孙子准备的,能割几把是几把,眼看孙子个子窜起来了。
儿媳妇听见公公起来,赶紧起床烧开水,泼下一盆浓浓的黑豆茶、凉好一罐清热降暑的地椒茶,趁男人还没醒,紧赶紧地蒸出一锅暄暄的大馒头,又挽起袖子擀了一大剂子面,这才叫丈夫,“狗娃,狗娃,起来吃饭,他爷把镰都磨好了。”
丈夫起得是有些迟,不过要是看表的话也才七点多钟,四个大馒头下肚,囫囵咽下两个热鸡蛋,一大缸子黑豆茶喝了,狗娃爸这才往地里走去,这时正是下镰的好时候,再早就有反潮的露水。男人的脚步声是深沉有力的,走在麦地上发出嚓嚓嚓的脆响,进麦地,弯腰,只听嚓——一镰刀过去,画出一个优美的长方形,干活还得靠男人哩,爷爷看着儿子有力地挥动着胳膊,分明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把浑身的甜蜜全裂在了缺牙的嘴角上,寻了一块倒伏的麦地慢慢地割起来,力气明显不济了,基本功却好,看老人割过的麦地,分明是一位手法稔熟的剃头匠在给大地剃光头呢。
女人风风火火地喂了猪,喂了鸡,拴了狗,给牛添足了草,才急急忙忙地往地头赶去,脚步轻盈,如同久练武功的高手,飞燕般地向丈夫那儿赶去。
儿子跟在爸爸的后面,试着割了一阵,不断线的汗珠弄得口干舌躁,胳膊被麦叶刷的血红,尘土和洇出的汗水又蜇的疼痛难忍,急急地跑到树荫下端起母亲凉在那儿的椒茶罐猛喝一气。爷爷笑着说,“‘一等麦客只吃不喝,二等麦客连吃带喝,三等麦客只喝不吃,’你还不赶紧好好念书。”
田边地头的树荫是割麦人小憩的最好场所,树荫这时候最温柔妩媚,骄阳下,碧绿的浓荫撑起一片阴凉爱心,爷爷敞开紫红的胸膛,爸爸干脆光着脊梁,小孙子已经知道爱美了,脸上滚着细汗还是穿着短袖不愿脱下来,浓黑的头发略微有些长了,别人看了都觉有些热,他却觉的美呢,急急地又喝了一气地椒茶就躺在树荫下睡着了。女人把割下的麦捆一一立起来,让它们趁着好天气晒晒,一边走一边拾了几根遗在地里的麦穗,才走到树荫下,喝了几口水,又拿起针线给男人纳鞋垫,看着女人那因太阳过分暴晒而红紫的脸庞,一丝笑意浮上了男人微张的牙齿。
月亮升上来了,天还是瓦蓝瓦蓝地亮,农人们将割下的麦子一车一车地往场里拉。孙子已经睡意蒙胧了,当爸的还在用力拉着沉甸甸的架子车,爷爷喊着,“快点拉,完了让狗娃睡去”,当爸的记起自己小时候受累的那一刻,让儿子也锻炼锻炼,就没有搭腔,天黑前妻子回去做饭去了,无论回去多迟,总有那光洁柔长的面条、酸如后味悠长的浆水汤在等呢。碰见邻家,问麦子收成,谦虚着说自家的麦子不太好,邻家的麦子才叫好呢,其实心里那个美哟。
拉到场里,还要垛成麦垛,爸爸有些急,垛茬没压好,垛到一人高,麦垛塌了,忙碌了一天的爸爸有些生气,上前将倒塌的麦垛踢了几脚,“算球了,不垛了”。爷爷笑了,说,“还是垛起来吧”,爸爸当然知道还得垛起来,要是晚上下一场暴雨,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