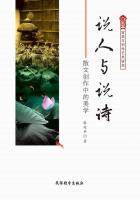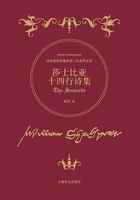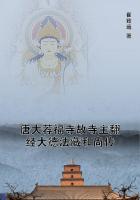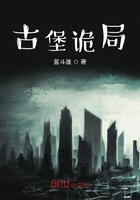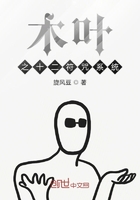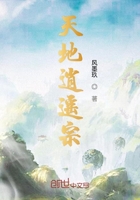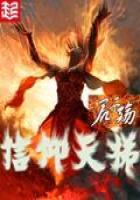杂耍之事自古以来便是百姓心头的最爱。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荡后,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杂技艺术在这一段时期同样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隋唐时期,杂技更成了宫廷和民间共享的一种艺术形式。
唐朝时期依旧把杂技称之为杂耍,言语中总带着些轻蔑的成分。而此时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女艺人的出现。这是一个社会风气空前开化的年代,技艺高超且美艳动人的女艺人为杂耍行当赢来不少喝彩声。而杂耍的杂技种类也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不禁有"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等传统内容,又因为马戏和幻术也很受欢迎,所以唐王朝时期的杂技艺术巧妙地将多种表演形式杂糅在一起,这更能充分展示出杂耍之人超凡入圣的技艺。
不论是宫廷表演,还是街头卖艺,杂耍总是无处不见。诗人陆龟作了一首《杂技》,说的便是当时盛况:
拜象驯犀角牴豪,
星丸霜剑出花高。
六宫争近乘舆望,
珠翠三千拥赭袍。
诗中讲述的是专为皇宫中的帝王和妃子表演的一场杂技。既然是帝王享受,也自然和民间花拳绣腿的套路完全不同。再看眼前,那身躯庞大的大象竟然懂得行跪拜之礼,甚至连愚笨的犀牛也通了不少人性。令人赞叹的是,和这些动物们角力的斗士们如此勇敢,他们身边挤满了凶猛的野兽,在他们竟寻不到害怕之情。又有表演投掷弹丸的人只是把手臂轻轻一挥,就只见一道亮光如同流星闪过,毫无偏差地正中了目标。这边的表演还没有结束,另一边的舞剑也已经用舞起来的银霜把自己遮盖住了。只见得寒光点点,却看不见舞剑之人究竟在何处。
这一场表演如此惊奇,以至于宫中那些足不出户的妃子们都想要近前一步看个究竟,甚至连皇帝本人也都看得目不转睛,完全被这场杂耍吸引住了。只是帝王之家在羡慕着舞台上的光怪陆离,杂耍之人却在心底羡慕着帝王身边左拥右抱的珠玉翡翠一般的宫女。
人们实不知,你我都只是各人眼中的戏子,全都在上演着一处彼此看得欢喜的好戏。
于是,诗人张祜写道:
热戏乐
张祜
热戏争心剧火烧,
铜槌暗执不相饶。
上皇失喜宁王笑,
百尺幢竿果动摇。
这是要从李隆基还是亲王的时候讲起。
那时他的府中有一个杂耍班子,只因帮着李隆基消灭了武韦政治集团而颇得了些权势。及至玄宗称帝后,这个杂耍班子自然也就成了皇家御用,由此又多出几分横行之态。玄宗看在眼中,把这些行径也都一一记在心中。这一日,玄宗和兄长宁王一起观赏杂耍表演。为了能使表演更精彩,更为了表达兄弟间的和睦情,玄宗特意把宁王府中的杂耍班子也请了过来。本意是想要让两个班子一比高低,多的是那份娱乐,输赢也均是有赏赐的。
当时,人们把这样一种比试称之为"热戏",说得再透彻一些便也有了些角逐的味道了。宁王府的杂耍班子先上场表演。只见一位艺人头顶着百尺长的竹竿登场了,这一边皇家的班子却故意寻出一根更长的竹竿顶在头上,丝毫不肯落了下风。本以为自己因此便占优势,谁知玄宗本是不希望自己家的杂耍班子取胜的,否则在兄长面前便要落得难堪。所幸,一位脑筋灵活些的老艺人揣摩到了玄宗的心思,他故意在长竿上做了些手脚,致使表演中竹竿突然折断,这才把整件事情敷衍过去。
这一场表演,张祜也该是在现场的。他说,表演双方的热戏真像是火山浇油一般,不把对方比下去谁也不肯善罢甘休。若是不加制止,恐还要起一场更大的争执。但玄宗又不能把自己心中的意图明着说出来,眼看宁王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玄宗心上却似火烧一般。忽然只见得舞台上自己的杂耍戏班头顶上的长竿折断了,这便表明是自己一方输了比赛,他这才敢偷眼瞧宁王,见他重又微笑起来,玄宗七上八下的心也才稍稍地平复下来。
虽说是一场竞争,杂耍之人只一味晓得要赢了对方,玄宗却只以此为名号而暗度陈仓。台上演戏认真,台下的勾心斗角也不输分毫。最后反倒越来越弄不清楚究竟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了。
这虽说是一出黑色幽默,却也总是可从中一窥帝王之家的多少无奈。但无奈再多,也只消一次杂耍,便可以趋走心中的阴暗。这份喜爱,是断舍不掉的
因而在开元年间,唐明皇曾下令各郡县举行戏法、杂技、歌舞等选拔比赛。从下到上一级级的比过去,最后获胜的人便能得到极多的奖励。又有人传言,帝王举行此比赛仅仅只是为了贵妃爱看杂耍的嗜好。帝王一句话事小,却因此忙坏了各地官员。
不想,嘉兴县中竟有一名命狱囚自称懂得绳技。众人不屑一顾,均认为绳技并不是什么罕见事。该狱囚却口口声声说自己的表演与他人不同,他说只要一根五十尺长的绳子,如手指般粗细,向着空中一抛,自己便能顺着绳子爬将上去。不听便罢了,这一听人们就议论起来。早有人把此奇人奇事报告给管事之人,管事人同犯人商定,隔日就在刚刚落成的戏场一展绝技。
这一天,连县太爷都亲自到场了。只见犯人把百尺长的绳子绕在身上,随后又向四周人群作揖表示感谢,这才不紧不慢地表演起来。他拿住绳子的一头,只轻轻向着空中一抛,便有两三尺长的绳子直立在半空中。如此一点点抛上去,最后竟再也看不到绳子的终端到底高到哪里。犯人见时机成熟,只顺着绳子纵身一跃,便如飞鸟一般到了半天空中。人们这才如梦方醒。县官忙命人把绳子扯下来,可待一团烟雾飘过后,连人带绳子再找不到踪影。
这件事最后还传到了唐明皇耳中,自此又闹得天下之人皆知。人们只是不知,这逃出生天的技法却是著名的"江湖四大套"之一,实则也只是糊弄人的戏法。虽并没有人知晓其背后的手段,却也让绳技盛极一时。
相传,绳技乃是由西域传入。天竺国人舍利,不但是魔术祖师,更是绳技的祖师爷。当年舍利还曾训练了"倡女"踏着绳索歌舞。唐代诗人刘克庄曾写了一首诗来介绍绳技:
绳技
刘克庄
公卿黠似双环女,权位危于百尺竿。
身在半天贪进步,脚离实地骇傍观。
愈悲登华高难下,载却寻橦险不安。
谁与贵人铭谇右,等闲记取退朝看。
这是绳技表演时的盛大场面。说来说去,人们惊异的也只不过是半空中走钢索的人。这便是卖油翁当初说的那一句话了,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只因天长日久地训练着,"唯手熟尔"。可观众们并不这么想。人们对奇异的事情总是着迷,尤其是自己力所不及的"奇迹"。在他们看来,只于一根钢丝上行走却如履平地的杂耍之人必定有着非一般的绝技,这才呼朋引伴竞相观看,惟独不知道这些表演者为了一时的辉煌而受过多少悲苦。
只是谁也不愿意去听那些磨难,单单眼前的娱乐就足够了让人欢喜了,何苦还要再提背后的伤心事?又或者,谁的生活就简简单单了?只不过各人有各人不同的难处罢了。
浮沉一笑,看得穿又放得下才是豁达。一曲逍遥叹,一回聚和散,一生也就有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