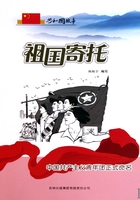头发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随身证件之一。它与内脏、骨骼、皮肤等物一样,同是人体的有效组成部分。但它与其他的人体器官相比,显然又有着不同的个性,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独特体征。
首先,它的新陈代谢过程绝对是可见的。不象内脏,总是藏在身体的深处暗暗衰老,也不象皮肤,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的脱落皮屑。它总是很高调地显示着自己:或者,在很短时间内就长了一寸,使得漂亮的发型完全走样;或者,在不经意间就霜了鬓角,使得久别重逢的老友乍见不敢相认。就它的这个特性来说,浑身上下也许只有指甲可与之相类。但是指甲的重要性与头发相比又算得什么!指甲的位置只在于手脚的末梢,且面积甚小,如其相不雅,是很容易隐藏的。而头发则不然。除了在严冬的室外戴帽子比较自然以外,只要是在盛夏、在室内戴着一顶帽子,那好吧,你就是不摘下来,人们也一望可知:你是个秃子!
其次,它的新陈代谢过程人们必须参与。文明社会,谁也不能任由头发愿长多长就多长,愿长甚么样子就甚么样子。古人遗训中这一条最可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意思是说连剪发都是一种自残行为,剪了即为不孝。所以清人入关时欲一统天下发型,甚至发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令,天下真个为头发掉脑袋的人也不在少数。李白有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虽然是浪漫的极言,但是想来天下人若从出生起都不剪头,一直从胎发留到成年乃至去世时为止,那不说人生中千奇百怪的其他“愁”,单说头发,也愁死人了。见过有个什么“吉尼斯记录”,世界上头发最长者,竟有两米多,堆在头上似乌云压顶,拖在身后如溪水奔流,真个了得!就是洗一回,也得站在凳子上,请好几个人来帮忙。不说美观与否,首先给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就不可尽言了。想我等众生,若留头一生,纵然不一定人人都能似吉尼斯记录者那般壮观,留个三尺五尺想来无问题。古中国地广人稀还好说,若似今天这等街上人流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后面的人必定踩了前面人的头发,弄不好会象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片皆倒。光是由此引发的争斗和纠纷,也足以使得交通堵塞、派出所里人满为患了!可见头发这东西,“受之父母”不假,“不敢损伤”却实在不是一个恰当的恭维。再说,世上三百六十行里少了“理发”这一行,弄作个三百五十九行,说起来也拗口不是?
第三,在人体各器官中,它是最容易伪饰的。头发白了可以染黑、染黄、染彩,头发稀疏乃至秃发可以戴假头套、植假发。人的发型和头发颜色确实对人的外在气质有着一定的影响,无怪现在随着化学工业的精进,各类美发产品争奇斗艳、层出不穷。人们总是对自己得之于遗传的体貌有所不满而希图着改变,变了越不满而又图再变,总之欲试尽天下所有人种的所有体肤特征,开发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这种心理不是出于过度的自卑就是过度的自信,总之一个“过”字是难逃的。过,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其祸不远。直接的后果就是,在试了又试中,头发日稀、年龄日老、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没见谁因为发型的变化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倒有人因过频染发患上皮肤癌,提早过世。就说那些戴假头套的,虽然遮挡了让人发笑的秃头,感觉上不出气不透汗,却比戴帽子更加难受。笔者单位就有一秃士,先变帽子为假发,后又变假发为帽子。可见头发一事,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笔者小时候,有一头非常浓密的褐发,马尾、羊角辫全不适宜,只好紧紧地编成两个又粗又长的麻花辫子垂在背后,跑起来“啪啪”地敲得背上隐隐作疼。那时候洗发没有专用的洗发水、护发素什么的,用的是阳泉市出的一种“春泉牌”洗衣膏。大抵青春无敌,洗衣膏洗出的头发,却如绸缎般柔顺光亮。夏天的时候,洗完了头发,就搬个小凳坐在阳光下,然后把所有的头发往前面梳,让它瀑布一般垂挂下来,就这样在毒烈的日头下曝晒,一个中午的时间,晒到头晕脑瓜疼,才能干得了。要是冬天,就只能在晚上洗头,第二天早晨醒来,头发尚半湿。等走到学校去,辫子往往冻成了硬棍。随着岁月流逝,洗发用品由“春泉”变成了“飘柔”、“潘婷”、“索芙特”,发型也由长发变成了短发,头发却渐渐稀薄了。想起电视里的美发水广告,动辄就找倾国倾城的美女来拍,那瀑布般柔顺光泽的长发,其实是青春的功劳,又与洗发水何干?他的产品,古稀老人用了能洗得出那样的效果,那才算优秀,才算本事。嘿嘿。
一派荒唐言,几行无聊字。今天晚上洗头的时候忽然心有所感,遂录而成文。一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