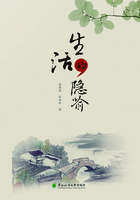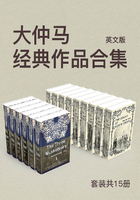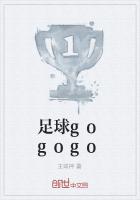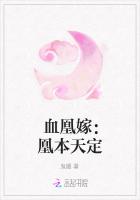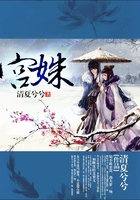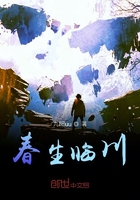长篇小说《李自成》中,对张献忠娶有九房妻妾倒不曾回避。农民造反打天下,原是为了当皇上,目标是后宫佳丽三千,岂止是霸占八九个女人而已。何况,张献忠拥有女眷,向来也不止百十;而且每逢战事不利,必要首先屠杀女人。自己不能占有,也绝不容许女人们活着被敌人占有。打了胜仗,攻城掠地,再来搜罗金珠美女,转眼间又是妻妾成群。
张献忠杀人,手段也格外残忍。明朝朱家天子曾使用过的活剥人皮的惨绝人寰的行径,张献忠就全套学了来。活剥人皮,剥下的人皮要完整,缝合起来里面充以干草,这皮人儿要展览号令;剥掉皮的人核儿必须存活三天以上,否则剥皮的刽子手就要反坐,也得被剥皮!
所谓双雄,李自成率先攻入北京时,张献忠尚在四川湖北一带。李自成进京,兵卒杀人抢劫强奸不在话下,虽有军令却禁而不止;更其下令拷打掳掠前朝文武大臣,逼索钱财毒刑用尽。哪里有一点执掌天下的正大气派。至于张献忠,听说李自成已然立起了大顺朝,索性开始疯狂杀人。他的理论是:你既然当了皇上,总得有老百姓来统治,我把老百姓给你杀完宰光,看你这皇上怎么当!如此地灭绝人性,有多少生灵惨遭屠杀啊!这就是“农民起义”,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无不歌颂称赞这样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真叫人欲哭无泪。
逝去的历史,皆成陈年旧账。但背负了数千年沉重历史的当代人,不应该背一本糊涂账,更不应该制作新的糊涂账。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血不应该白流,至少在歌颂农民起义时稍微慎重些。
而我,则已固执地认定,农民起义破坏性极大,张献忠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纯属杀人魔王。明朝,以朱天子剥皮始,以张献忠剥皮终。台上与台下争夺江山的双方,都是封建文明没落时代的产儿。活剥人皮的行径背后,也都有文化的心理的支撑。
婊子怎生多牌坊
关于婊子,鲁迅先生有许多或是不经意涉及的议论,堪称高明。先生论及唐诗,曾说道: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我们几乎可以照搬这一句式说:像样的杂文差不多被鲁迅先生写绝了。
先生论及婊子,第一:说婊子是婊子,不算骂人;第二:卖血和卖淫的钱都是血汗钱。我记忆较深的主要有这么两点。
婊妓面首,这些依赖出卖男女色相为生的行当,其产生出现存在的历史几乎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社会有对男女色相的需求,无论这种需求在理论上合理与否、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判断人道与否,这需求就总要呼唤市场。皮肉生意因而兴隆,乌龟王八因而产生。说我们的社会挂了某种招牌,就没有吸毒卖淫等社会问题,那只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在贫困乡野、偏远地面,民风淳朴而礼教疏松,光棍跑腿子多,雄性需求强大,风流女人应运而生,或者说是市场创造出了所谓“破鞋”。在繁华都会现代城市,暗娼禁而不止,变相的和赤裸的色情服务彼彼皆是,公款嫖妓时时在报端曝光。嫖客在人前往往最是正色俨然大骂婊子,可谓无耻之尤。好比那些贪污公款监守自盗的各级公仆,作廉政反贪报告最是义正辞严。堪称感人肺腑,足以催人泪下。盛大的假面舞会长演不衰,因而有道是: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
与嫖客骂婊子的官场文化相比,倒是卑俗的民间文化还多少朴实些。
民间谣谚有比较客观地陈述事实的段子。我们山西流传着所谓的“三大怪”:
坷垃垒墙墙不倒,和尚跳墙狗不咬,女儿接客娘不恼。
特定地域的特定情况造成了特定的地域文化现象。和尚们有钱要花,四周村社贫寒苦焦,互通有无自然而然。佛门弟子广结善缘,佛法原来慈悲。
还有理直气壮大声疾呼的口号。比如陕北榆林,历来是军事重镇。驻兵众多,商贾云集,偏生四外沙丘环抱,草木不生。皮肉生意因而兴隆,畸形繁荣。熟客们嘲笑当地婆娘不守贞节,婆娘们抗声反诘:
榆林城,四面沙,不卖身让我吃啥?
是啊!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为吃饭为活命不得不卖淫,锦衣玉食者根本无权说长道短。卖淫者如果取得合法身份——旧时所谓乐籍,并且照章纳税,那么她的行当不是一种社会职业是什么?她的劳动所得不是血汗钱是什么?
有幸不曾沦为妓女者或没有接客能力而操别种行业者,实在没有多少自鸣得意的道理。
但是,婊子毕竟是婊子。在我佛眼中,众生平等。而在世俗社会里,婊子妓女和诰命夫人到底不能平等。说省长和掏粪工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大约也只在理论上辉煌。省长和掏粪工人都知道这是那种伟大的谎言。婊子们,由于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操了皮肉生意,在这种行当里浸染久了,其普泛道德水准会相对低下。皮肉既已卖了,脸面名声信义廉耻便也可能统通抛却。好比老百姓说的:自从讨了饭,不怕人说穷。讲婊子特别仁义正如讲刽子手格外仁慈,除了个别特例,这说法只能是一种反讽。在一般意义上,在约定俗成的观念里,在世俗价值的天平上,婊子几乎就是无耻的具象。中国人骂人,骂“婊子”和骂“王八”的概率大致相当,而且都是常骂常新。
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在与俗文化相对应的所谓雅文化中,文人学子对婊子题材抒写之多,对婊子妓女歌赞之烈,也达到惊人的程度。唐有李娃、薛涛,宋有李师师、梁红玉;明代那就更多,李香君、柳如是,秦淮名妓誉满全球;清初有个陈圆圆,清末甚至还出了个赛金花来凑热闹,以显功德圆满。这些婊子们名头响亮,书之竹帛,无疑皆是仰仗了文人学士特别是文豪名士们的生花妙笔。结果,文以人传,人以文传,中国历史至少是文化史上就为众多婊子们赫然树起一座座牌坊。不说触目惊心,堪称蔚然壮观。
文人学士描摹妓女生涯,或纪实或传奇,首先是有这样的生活。狎妓载酒,名士风流。李白、杜牧、白居易,直到苏东坡、侯方域、钱谦益,都有这般嗜好。大名之下,不拘小节,狎妓甚至成为名流不可缺少的点缀花边。风气使然,相当一个时期,江浙文人不拥妓命笔,文章便难成佳构。据清人笔记载,曾有一山西籍大员督抚江浙,痛恶学风淫靡,禁绝读书人狎妓,会考结果一向冠绝天下的江浙地区竟大大落后,录取人数不及往年二分之一。
文士们有这样生活,而且成一种风气,被视为风雅,当然就要大书特书。平心而论,在众多描摹妓女生涯的作品中,不乏佳作。不乏一些透露出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叙述与刻画。从《杜十娘怒沉百宝葙》到《桃花扇》,确有名篇。
但是,墨写的文章从来不足以反映血写的历史。歌赞婊子的作品之所以出现,首先在于承认卖淫制度为合理的前提。好比说,宣传鳄鱼皮制品如何豪华高贵,首先已认可了人类屠杀鳄鱼为合理。何况,文人学士描摹妓女生涯多半是在卖弄自己的风流,自叹自赏。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廉价的同情、闲雅的怜悯,吃得太饱之后悲悯一回路边的乞儿。
我们当然无权苛求古人。卖淫有如吸毒、赌博和暴力,种种社会问题或负面存在几乎与生俱来伴随了人类的整个文明史,有如疾病困扰着人类。所有这些,是人类的原罪?抑或是文明的负产品?因而,近代以来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是为“社会学”,专门研究任何社会所无法避免的问题。众所周知,社会学这一学科在我国五十年代曾经设立,包括马寅初先生的人口学说曾在社会学领域有最初的建树。后来,这一学科被粗暴取缔,可以奈何!责备古人嫖妓,或者诅咒古时中国怎么会有卖淫那样肮脏的行当,只能说明我们幼稚可笑。
值得注意或曰只是引发了我个人注意的一种现象是:卖淫嫖娼在我国屡禁不止,它能否仅仅用行政手段禁绝得了。而有关部门着力扫黄兴师动众、屡扫屡兴屡有收获的同时,电视屏幕上为婊子树碑立传甚或就是大立牌坊的节目却也格外地多起来。前几年有李香君、柳如是粉墨登场,再早有杜十娘沉宝、苏三起解南腔北调,炒得火暴一时的《水浒》中,与潘金莲偷汉相映成趣大肆渲染李师师接客。这位婊子卖淫,上卖与皇帝老儿,下卖与造反强盗,可就卖出超一流的水准来了。
不是在扫黄吗?不是大声疾呼弘扬民族文化吗?多部多集替婊子树碑立传的电视剧覆盖荧屏到底符合哪一条?或者说,荧屏节目如同众多文艺创作在事实上已不完全受命于行政指令,这也许不是坏事。剧作者热心于这类题材,写便写了;观众喜欢看这类节目,看便看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我的意思只是:抛开行政干预宣传口号约束的前提,平等地研讨问题,荧屏上频频播映关于婊子的节目,这凸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态?
如果说,古代文人状写婊妓生涯,是有那样的风雅经历,熟悉那样的世象境况;当代剧作者津津于捡拾古人余唾,出于什么创作动因?除了猎奇犯险、投合低级趣味,也许只剩了对古代风流名士的艳羡。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嫖娼宿妓只是当年故事,今天的普通百姓已多半无有此种公然买笑豪华享受的可能。大家在荧屏上观看一些当代美女脱肩露臂扮演的婊子乔乔画画、作张作致,也许就获得了一些窥探的满足。文学艺术固然有着宣泄疏导的功能,这功能在这儿如此体现也许正是这类作品的本来格调。
至于此类作品为了歌赞妓女,替婊子树碑立传,不惜人为拔高、胡编滥造,把婊子写得关心民间疾苦、深晓民族大义、疾恶如仇、慈悲善良,简直就是圣母显身菩萨下凡,则未免太过荒唐滑稽为所欲为了。国人历来有女人误国的传统共识,翻案文章一出,又翻到婊子爱国救国,哪里还有一丝艺术的严肃性。
或曰,这类替婊子立牌坊的节目本来就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本来就是拒绝严肃的玩意儿。认真不得,更不宜抬到学术论坛上来研讨。那就是我反倒学究气了。为各种各样男女婊子立牌坊自古及今何尝少,你又何必大惊小怪!你要大惊小怪,是你少见多怪,怪不得你的文章叫什么《今古奇谈》!堂堂知名作家、号称广有见识,为此浪费笔墨,这本身也称得上是一段今古奇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