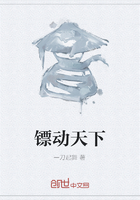“上帝终于对贾平凹微笑了”:恭喜你《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读着《秦腔》,我不时想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在农村的生活,辽阔的空间跨度,勾人回归纯朴的向往。时间的跨度。更是漫长。清风街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夏家家族的变迁演变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仅白家与夏家两代人贯穿整个现当代历史还有余头,难怪有人说它是史诗,鉴定为史诗又要怎样?以时间的跨度而论,我们的长篇小说有几部不是史诗?只是这史诗须得作“文学化的历史”解。
不怪作家也不怪评论家,我们的文学从来是就史的附庸。文化更是古代默客的自喻,就《秦腔》而言,它的使命感更多的是反映现实——明天的历史。孔子作《春秋》,孔子成了历史学家。文学却有它独立的品格。不是去说明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以自身的价值填充历史。
不必否认《秦腔》是史诗。至少作者有史诗意识,他要以一部小说,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反映那个漫长的时代。
史的文学观,决定中国作家的创造心态,写短篇还不要紧,一到写长篇,首先萌生心头的便是那史诗意识,要反映时代,自然要捡大的长的,贾平凹的使命感更强。显示的当然就更象史诗。评论界认为:《秦腔》是“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评论家们慧眼独具。言之不诬。
人皆可为圣贤,人皆可以为尧舜,谁也不甘于平凡,总得出众人一头地。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据说也是全人类的共性。
作家要成为圣贤,成为尧舜,当然就得写伟大的作品,而伟大的作品又莫过于史诗,写史诗当然经得存下史诗的意识。史诗的意识说到底是伟人的意识。
作品可以确立作家的存在,得这个奖赏那个头衔,受到众人的爱戴,但意识属于人格,在人格上作家与普通百姓绝无两样。
在叙事分式上,《秦腔》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述往事的,也就是从现时的感受中寻找记忆中的形象。比如作品中的“我”,对白雪的暗恋并上树看到白雪,来寻找某种平衡和快感。《秦腔》对从前乡村生活是自恋的。清风街人多地少,日子极度贫困,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被全部捋光了,一李姓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愿望是能吃上一碗包卷掺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颗热红苕。
贾平凹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象乌鸡一样,那是乌在骨头里的。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大国,土地供养了我们的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而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历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人民吃饭问题解决后,国家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腾着往前拥着走,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秦腔》中的清风街似乎也度过了它短暂的欣欣向荣的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在提高,而化肥、种子、农药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地。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没了,像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不定地吹,农民脚步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走出,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穿村镇的土地。铁路也将所有梯田和牛头岭劈开,盆地就那么小,交通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公路边。
贾平凹是一位智者,他有才华,也有理念,但更有责任。才华可以表达思想。而责任可做成一切。失去自家回首往事的述说。清风街失去的村庄更多的是理智,加上庄边环境和思想情感的暌违,使《秦腔》成为才华囊就的理念的塑像,倒也灿烂辉煌。
最为理念的还是书中夏风为爹立碑的事,“二叔英武了一辈子,他又是这么个死法,才应该给他的碑上刻上一段话,可这话我概括不了,而就先竖个白碑子。等到夏风回来,咱在刻吧。”死去的人会立的一个“白碑”不合常理,作者不知何意,这倒让我认为:文学不是附庸,也不应是哲理的妻妾,文学作品中的哲理应当让人去体味。直白的说出来便成为理念,理念使人文意豁然开朗,同时也使文学的意味荡然无存。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是蓬勃向上的,也是积极健康的——他走的原本是一条正道,一条有才华的的作家几乎是必然要走过的正道。《秦腔》里表述的一种东西必须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体。思想性共同于政治性,势必要致文学创作的浅薄和概念化。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应当是一个文学的概念,不应当是一个政治概念,对艺术伤口的分析,就只从分析艺术入手。正象政治可以涵盖一切政治概念,艺术也可以涵盖一切艺术的形象和概念,包括它的思想性,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玄奥的哲理,都必须是艺术的有机成份,与情节浑然一体,互为表里,绝不仅仅是什么艺术表现出来的事而已,艺术不光是手段它也是目的。
这儿说不是怠慢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了么?不是的恰恰是对思想性尊崇,真正的尊崇。一部文学作品,除了文字和标点符号组成有点乏味的格式而外。还有一种洋溢于作品之上,回荡于字里行间的东西,古人称这为意境,而思想则是艺术的升华意境的凝聚。意境使文学作品区别于一般的文牍,思想又使文学作品有了高下之分,我们使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有思想的,不正是对这个作家和这个作品的赞美么?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说,作为文学概念的思想,只存在有与无之分,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正确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那是另一个范畴的事、应由别的概念来作质的规定。
《秦腔》如此众多的人物,如此繁杂的事件,这倒让我想了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这部小说里,以叶子的婚事为之又揉进了转让土地,买公房,闹社火一个接一个,如过马灯一般多是事件的附进,少有场面展开。《秦腔》中,对众多事件描述,显示了作者对待事件的冷峻态度。张家的老五,当年是劳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现在脑中风了,流着哈喇子走过来,他喜欢望着我笑,给我说话,但我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娘糊涂了,在炕上拉屎拉尿挂在墙上。关印还是贪吃,当了支书的他,他的侄子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却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地死了……
或许是个人的气质的原故吧,平凹作品中的女人都是情种,男人都是此谦谦君子,即使在事来上百折不挠,在女人面前总是那么木讷和腼腆。平凹作品的笔调主要表现在他的叙述语言上,质朴自然倒是其次,难得的是如苏东坡所自评的那样,“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尽意”。
(转引自钱钟书《宋词题注》)
较之筠有的明确流畅《秦腔》则显得凝重深厚,甚至有些凄凉——这或许正是老辣的标志,当然一以贯之,还是那种自然的情致。这里请看一节报表,其实在小说里很不习惯出现这样的东西,然作者恰恰做了一份报表。
基本情况
清风街位于苗沟水库西南,北有苗沟水库主干渠(设计流量12m3/s)。全村现有土地面积一千亩,其中滩地300亩,湿地500亩,坡地200亩,全村410户2120人,人均不足0.5亩。
引洪淤地可行性分析(略)
经济效益分析
地淤成后,以种玉米为主,收获玉米500kg/亩,秸杆500kg/亩,玉米价0.6元/kg,秸杆价0.2元/kg,每年纯收入138万元。
以上报表是平凹有意安排,还是失误,不去考证。
我并不是说,平凹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不是的,他是有自己一贯执著美学追求的。在同时代中年作家中,他是较早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在作扎扎实实的努力,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就象出西安往东,只会看到骊山华岳、黄河和中原大地。若是看到大漠和天山,那倒是奇怪了。从《秦腔》里可以看到,平凹心境怡淡,处事平和,该是最有文心、最宜于在艺术田园里耕耘的。
平凹作品的力,不是来自故事的曲折,情节的逼真,而是来自感情的激烈,楔入谈者的心扉,使你不能不接受。热情和激愤,是成功一部作品必具的条件,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涵的对于平凹来说,因为这热情和激愤更多的是外在的,他需要的不是飞扬和铺排,而节制,我说的不是压抑和删节,违拗性情,削足适履,乃是“走了眼看”使成那种冰层覆盖下的激流的汹涌。他似乎不太懂得感情与语言艺术只是一味地倾泻。
热情了还要再热情,激愤了还要再激愤,再接再厉,步步紧逼,遂造成那种类同獭祭的同义词语的连缀。若有关反差,比如说越是炽烈的感情越是用冷峻的语言,越是严肃的事件越是用那种不那么严肃的叙述方式。《秦腔》经历了这种语言的变化。
“后沟里有人吵架,一个说:你张狂啥哓,你把老子X咬了?那一个把,帽子一卸,竟然扑上来就咬X,反X咬了下来,村镇外打工的几下个人,男的一来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来在省城里捡煤,捡破烂,女的的外面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个白公鸡送回来,多的赔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打架坐牢的三个,因赌搏被拘留过十几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
平凹的作品,最初只是一味地写、写、还是写,著作之丰赡,令人咋舌瞠目。从九二年后,他的作品带有预言性;而恰被他言中,这就像初期他写少女为多,而后来写少妇为多,当年那群待字闺中的姑娘出阁之后,已成为体态丰盈、风姿绰约的少妇,业已步入中年的形象,那支多情的笔紧追不舍,如实地描摹下他们的忧愁和欢乐。
少妇较少女有更多的文学性,在平凹的作品里看待甚为分明。朱自清曾说过:“最宜于艺术的国土的,物中有杨柳燕子,人中便有儿童和女子”。(《子恺画像跋》)儿童的天真烂漫,女子的温柔多情,确抒写不尽的。
《秦腔》的成功之处,我想大堤是提出了一个很凄凉和令人留恋的问题;土地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村镇没有了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
最后,我用平凹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评论;
树一块碑子,并不是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子,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