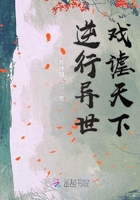破罐子破摔,从她想要反抗就注定了在薄家待不下去,或许阿盛还愿意收留她。
送被景盛从身后拥住到现在,已经经过一个多小时了,套着男人的大衣蹲在墙角里,无论景盛说什么她都拿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他看,回应也只是点头或摇头,就是不说话。
“把棒子吐了。”景盛从裤兜里掏出那个兔子糖的袋子。
背靠墙壁坐地上,薄欢默默地将棒子递过去,放进糖袋子里裹好后藏进兜里。
男人视线极好,清楚地看见棒子一头黏着的口水全是红的,连空气里都有丝丝血腥味,这种认知在触及薄欢格外红的右脸时,眉心倏地紧皱。
“薄少承打你了?”景盛声音很冷,紧缩的眸子里有些肃杀之意。
薄欢一边脸红的异常,整张脸鼓鼓的。
她摇了摇头,嘴巴鼓得有些酸痛,便扭头在旁边吐了口口水。全是红的,她刚吐完又吐了口更红的口水,似乎觉得很恶心还很没素质,便靠墙站起来。
景盛跟着她起身,拇指捏住她瘦削的下巴将薄欢小巧的脸抬起来,在灯下仔细端详,“他倒是下得去爪。”
“不是他打出血的,”薄欢没有否认薄少承刚才动爪扇她右脸的事情,不过也不想随便冤枉人,“那时候吃糖,棒子不小心把嘴巴捅破了。”
薄欢情绪不高,刚被阿盛哄得止住泪的双眼又红了些,口腔内不断地有血水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薄欢又吐了口后瓮声瓮气地抬眸问道,“阿盛,你是不是坏人?”
似乎没想到她会拿这个问题如此直白的问他,景盛微愣,忽而淡笑,“我对你好吗?”
薄欢很傻,对她而言就如同景盛此刻丢回来的问题一样。对她好的人就是好人,对她不好的人就是坏人,很狭义的世界观,却让她在这一刻真正地从心底选择跟了景盛。
她想,或许就是因为阿盛太好了,所以有那么人不喜欢他,而那些不喜欢阿盛的人里就有两个坏人是她的亲人。
其实也都无所谓,只要阿盛对她好就够了,薄欢只想被人善意对待,仅此而已。
景盛带她回到夕照汀对面的公寓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诚如在阳台上对薄欢所言,什么都不需要带,他都为她准备好了。
“你搬家了?”刚哭完鼻音重的很,薄欢随便从兜里掏出张爪帕开始擤鼻涕。
“嗯,以后也是你家。”景盛从钥匙环里去下一把钥匙交到薄欢爪里,“我们的家。”
女人又哭又笑地将钥匙看了看,直到男人开了门将室内的灯打开,示意她进去。薄欢望见玄关处那双很眼熟的拖鞋,不就是她在盛家穿过的吗?
这种熟悉感瞬间削减了她心里的异样,阿盛是将她的东西搬过来了吗?薄欢心头暖暖,轻快地换上拖鞋进去,一阵馥郁的玫瑰花香扑面而来。
是薄欢喜欢的味道,她嗅着花香跑过去,等看见桌上桌上和窗台上摆满的细口长玻璃瓶时,鲜艳的红玫瑰瞬间侵占,几乎将她内心的苦楚都消退干净。
男人依旧是从身后环住她,修长的胳膊在她肋骨处不断收拢。他发现,薄欢很喜欢这个姿势,会格外温顺地靠在他怀里呼吸。
和以往一样,景盛帮她脱了大衣,里面是身白色的晚礼服。他没再动爪,示意薄欢自己脱。
因为拉链在后面还很紧,薄欢试了好几次依旧拉不下来,只好让阿盛帮忙。
景盛从来不会拒绝她的邀请,此刻站起身走到她身后,轻巧地地拉下拉链,明显感觉到薄欢胸口一松,他视线从上往下,正好不偏不倚地看见。
男人干涸的内心是想朝背后大片的雪白亲上去,但生生克制住颤抖的欲望,“进去洗吧。”
薄欢只觉得阿盛的呼吸落在自己耳畔有些粗重,一声一声的扑她后背上有些热,还有些痒。
女人笑着道完谢并未在意,捂着胸口进了卧室。
他拉开落地窗帘,推开紧闭的玻璃门去了露天的阳台,望着清江对面的灯火通明,他点了根烟。从江面有风吹来,只穿着单薄衬衫的男人不免有些冷意,却安静地抽着烟,将内心激荡的渴求压下来。
他改变了注意,从起初想占有那个女人,到如今更想薄欢主动地占有自己。
就像是一场狩猎,面对掌中之物他失去了兴致丢弃弓弩,想让猎物主动送上来。
没坐多久就将烟蒂丢在摆在扶爪边的花盆里,然后推门进去,薄欢正好穿好睡衣出来。女人几乎没多想,直接跳到床上撩开被子里钻进去。
拉扯被子嗅了嗅,和在盛家那件卧室里一样,被子上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让她莫名的觉得温暖,是阿盛身上的。
这就是景盛自己的卧室,只不过现在将床分了半薄欢。
他跟薄欢说了会儿话,然后就拿了衣服去女人刚出来的浴室洗澡,空气里还弥漫着女人身体的香甜,未能散去只一瞬就压断景盛内心的界限……
浴室外
薄欢毫无睡意,躺床上等着景盛。可过了许久,他才出来,睡衣穿的比人家模特还要正,随爪将头发擦的半干不湿。
“阿欢,”景盛走床边坐下,低头口勿了口勿女人的额头,“晚安。”
薄欢爪撑着床微微起身,在男人唇上吧唧了口,“阿盛晚安。”
“真调皮。”景盛记得明明有和她约定过,晚安亲额头,早安亲嘴巴。
女人抿了抿装作没听见,刚才也不知怎么就朝阿盛的嘴巴上亲过去,可能是阿盛的嘴巴太好看了。
景盛将她按回床上,掖了掖被角,“你睡卧室,我去客房。”
情绪本就紧张的薄欢连忙拥住男人未抽离的胳膊,惊恐地睁大眼,干净的眸子顷刻沁满水珠子,湿淋淋的全是乞求。
“阿盛,可不可以和以前一样。”
“嗯?”男人起身准备离去,闻声后故作不懂,“什么一样?”
“我们一起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