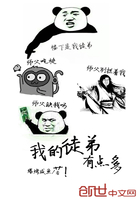她前世本就生在名门,妈妈娘家是二十一世纪有名四大家中的嫡系小姐,自小受的便是贵族教育。而她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下,举手投足间,根本不用刻意却做,那种与生俱来的贵气,自然而然的便随着心意流露出来。
所以这么多年来,卿意从不曾怀疑过她在他面前的乖巧听话全是装的。
“你看又浑想了,当年景家刚出事时,老爷子跟你爹即然敢抬你娘进门,便做好了一切打算,又怎能说是你连累呢?天已经不早,早些休息!”卿愿安慰的拍了拍她的背,已经过了三更天了,若再不休息,当真天要亮了。
“嗯!”卿苡顺从的点点头,乖巧的躺好,原本想了一肚子的话要交待,可真正看到了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次日一早,卿苡难得的起了个大早,确切来说,她昨晚上一晚上都没睡着,看着身边依旧熟睡的卿愿,卿苡轻手轻脚的下床,来到梳妆桌前,打开昨日晚间便收拾好的药箱重新又检查了一遍。
看着外面依旧灰蒙蒙的天色,早前便已经听到山间的鸡鸣,远处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应是卯时左右了。
将箱内药一瓶瓶重新看过,确定外用内敷皆能用到他伤全好时,方才放了放心。
卿意外伤现下已经好全了,可卿愿的伤却才结了疤,若是一路骑马颠波,万一再裂开来,又该如何?
可若给他备了马车,以着他这死要面子的脾性,定不会乖乖的一路乘车,当真是件惹人头痛的事。
“怎么了,头疼吗?这才卯时初,起这般早做甚?”醒来的卿愿看着她坐在桌前揉眉的样子,语气责备中带着一抹心疼,顺手拿了件外衣披在她仅着中衣的背上。
她平日里哪次不是睡到太阳高照了才起,昨日本就睡的晚,今早却又这般早起,起了又不知多穿件衣裳,若着了风寒可如何是好。
“你今日回京,坐车可好?”卿苡顺着他的手将外衣穿上,边系带子边探询的看向他。
“哪有这般娇气,爷的伤已经无碍了,骑马便可!”卿愿微皱了眉头回道。
“小心些终亏是好的,我等下去跟爹说,要他陪你一块儿坐车,这样可行?”卿苡看着他紧皱的眉头,软软的劝道,他一人坐车拉不开面子,那她让卿意陪着他一块儿总可以了吧。
“算了,随你!”看着她小意讨好的模样,卿愿到口的拒绝硬生生的转了个弯,点头应下。
转眼看到放在梳妆桌上那两尺见方的楠木箱子,卿愿挑眉,询问道:“这是给爷的么?”
“嗯,”卿苡点头打开箱子给他介绍,“这十瓶红瓶是外敷的,一定要记得每日敷三次药,不然到时就要留了疤了。
绿瓶是内服的,你不爱喝汤药,我都给做成了小药丸子,每日三次,一次两粒,用温水送下去就好了。
这五只绕金梅小瓶装的是治你内伤的,一共五十粒,你昨日用了一粒,还有四十九粒,我分到了五个瓶中,你记得要随身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