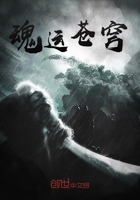过了许久,方梓龙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他瘫坐在地上,目光迷离地看着张治。张治道:“怎么样?我的朋友,正宗的爪哇货。”方梓龙道:“好是好,就是太少了。”忽然,他一纵身,将张治的包从他手里夺了过来。
张治哈哈笑道:“兄弟,那里面没有了。我今天走得匆忙,就带了这些。”
“你混账,你不是说要给我带一大包的吗?”方梓龙一把将包摔在张治的脸上,气恼地说。
张治一把抓住方梓龙的头发,大声吼道:“可是,你答应我弄到大红袍茶苗的,你弄到了吗?!”那一刻,张治一向温文尔雅的脸变得十分浄狞和恐怖。
方梓龙胆怯地看着他,道:“你放心,我会搞到的。”
三月的天心永乐禅寺,宁尘禅师正在打坐。忽然,山涧中传来一两声鹧鸪鸟的叫声。宁尘禅师皱了皱眉头,双手在自己膝盖上轻轻一拍,站了起来。然后,他推开禅室的门,飘然而出。
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石头轻轻滚动的声音。禅师定睛看去,只见一个人影正在长着大红袍的悬崖上吃力地蠕动着。禅师不说话,轻轻从地上捡起一粒石子,朝那人的臂膀上掷去。只听啊的一声,那个在悬崖上蠕动的身影不见了。
山涧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似在欢呼。
天色渐亮,小和尚在寺院中打扫。他看了看宁尘禅师禅房黑洞洞的窗户,摇头道:“师父还说让我们早起,他都这时候了还不起床。”
小和尚说着,一转身,朝另一个方向扫去。
山雾弥漫,晨雾中,落英缤纷。小和尚从左边扫到右边,又从右边扫到左边,忽然,他站住了,他看见宁尘禅师在寺后的山岩上站着,一动不动地眺望着远方。
禅师目光所及之处,是苍茫的武夷群山。
阳春三月的下梅格外明媚。三月初三这天一大早,人们看见陈家大宅斑驳的大门在晨曦中悄悄地打开了。几个仆人抬了许多箱子出来,还有几个丫鬟模样的人,正把一包一包的东西朝当溪里停泊的船上放。
“哦,看来陈家大小姐要走了。”对面的老铁匠放下手中的活计。
许多村人围拢来,人们一边和陈家的仆人打招呼,一边打听着去广州的行程。当他们知道此去广州要走一个月的时候,都感叹陈盈天作为一个女人的勇气。她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
对于陈盈天来说,这只是她生命中的又一次旅行而已。自从去了泉州,自从协助丈夫赵修打理赵家的茶叶生意之后,她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奔波,因为,整个大清朝所有的茶商都是如此,她也必须如此。漫长的旅途充满了绝望,然而,漫长的旅途也让人坚强。
老宅的厢房里,陈盈天正在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
那里有她做姑娘时穿的绣鞋,有她给舜瑾纳过的鞋底,还有在草堂先生那里读书时临摹的旧画。忽然,她的手触摸到一只精美的匣子。
盈天认得这只匣子,听父亲说,里面装着一只茶盏。小的时候,盈天一次不小心从父亲床下的箱子里翻出这只匣子,父亲看见之后脸色大变,盈天只好乖巧地将匣子放下。后来,她长大了,不再和盈地玩过家家的游戏,就再也没见过它。现在,它怎么在这里?
盈天用布拂去匣子上的灰尘。这是一只黄花梨木的匣子,三十多年了,依然木色油亮,在窗口的阳光下泛出尊贵的光芒。盈天抚摩了一下匣子上漂亮的花纹,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匣子打开。
“哦,怎么是它?”盈天惊呆了。
原来,这匣子里装着一只鹧鸪盏。三十多年了,鹧鸪盏星星点点的光芒仍然在漆黑的碗底上闪烁着,就像新的一样。盈天将盏取出,盏中光影忽现,似乎照到了从前。就在那时,她发现匣子的下面放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上面是陈运德熟悉的字体:
盈天盈地,不论将来你们两个谁读到这封信,我都希望你们能以平静之心读下去。此匣中所装之物乃史上名盏建窑鹧鸪盏,釉体细腻光洁,鹧鸪光斑油亮闪烁,为建窑珍品。据盏底“御供”二字考证,此盏极有可能是宋徽宗当年所用之物,实乃不可多得,稀世之珍。
关于此盏的来由,乃家父平生一大丑事。当年,陈方两家在武夷山茶行之中双雄争霸,为父偶然听说方家私藏朝廷重犯,又无意中将此事传与当权者。旋即,事出,方家遭受重创,家破人亡。为父知罪孽深重,以五万两银子买下方家此盏,不求宽恕,只求亡羊补牢也。
此盏虽在陈家,实系方家之物,若非为父利欲熏心,不会落入我手。望你二人知道原委后,替为父将其送还方家,而为父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难道,这就是茂瑾说的那只鹧鸪盏吗?”盈天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盈天当年曾经听茂瑾对她讲过,方家之所以对他如此器重,就是因为一只鹧鸪盏。
“对,一定就是那只鹧鸪盏,世上再也找不到这样完美精致的茶盏了。况且,父亲说过盏是从方家买来的,方家又是从庞家买来的,那这盏,就一定是庞家的了。”盈天不觉把盏抱在怀里。
早上盈天起床的时候,发现那盏还在她怀里抱着。
她站了起来,门外是下人们匆忙的脚步声,很多箱子被搬了出去,尘埃在老宅中游来荡去。~、
“夫人,该起程了。”小丫鬟走了进来,焦急地看着她。
“哦,好,这就来。”盈天说着,站了起来。
现在,该怎么处理这盏呢?给方家?还是……盈天在老宅里来回踱着步子。忽然,她笑了:给方家还是给庞家有什么分别吗?现在,方家和庞家就是一家呀。庞茂瑾的夫人不就是方梓然吗?
这样想着,她将匣子抱在怀里,披起一件衣服就走了出去。
现在,是该有一个了断的时候了。
陈盈天走到庞家的时候,那里的大门敞开着。
盈天径直走了进去。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三月的风在高高的马头墙上倏地一下飘过。然后,她跨过门槛,脚下的方砖上有湿滑的青苔,她险些跌倒。第一进院落十分宽阔,石槽做成的鱼缸里金鱼正在悠悠地游着。一树玉兰掠过鱼缸昂扬向上,白玉似的花瓣正在枝杆上不可遏制地怒放。往前看就是正堂,一副对联悬挂两侧,上面写道:“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看来,这是庞家待客的地方。可是茂瑾呢?为什么家里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盈天暗自疑惑着,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忽然,第二进院落里传来一声惨叫,接着,一个声音大吼道:“方梓龙,你快放下她,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那是茂瑾的声音。
盈天吓了一跳,快走几步闯了进去。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
只见二进院落里错错落落站了十几个人,站在最中央的是方梓龙,小妞被他夹在腋下,动弹不得,而方梓龙正用一把短剑抵着小妞的脖子,只要小妞一动,立刻就会血流如注。
茂瑾在一把藤椅上坐着,怒目看着方梓龙。而在他旁边,方梓然扑倒在地,绝望地看着哥哥手里惊恐的孩子。院子里站着庞家上下十几个丫鬟和仆役,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大家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疯狂的方梓龙。
“哥,你是孩子她舅啊一”方梓然说着,泪如泉涌。
“我连爹都没了,我连家都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他妈的什么都不是。”方梓龙说着,狠狠地瞪着茂瑾。
“你放下他,我跟你去天心,宁尘禅师会把大红袍茶苗给我的。”茂瑾看着他,神情严肃地说道。
“茂瑾,你不能,宁尘禅师不会把茶给任何人。”盈天厉声喊道。
“陈盈天,臭婆娘,你给我滚开!”方梓龙对盈天喊。
“你把孩子放下,我有办法,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把孩子放下。”盈天说着,走上前。她先将怀里装鹧鸪盏的匣子放到几案之上,然后找了个椅子不慌不忙地坐了下去。
“我才不信你呢,你爹害死我爷爷,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方梓龙道。
“你住门!”陈盈天厉声说。
“今天,我们谁都不许再提老辈人的事儿。方大哥,你不是要大红袍吗?你听我好好跟你说。”陈盈天说着,顿了顿。
宅院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看着她。方梓然几乎要朝盈天扑过去,然而,茂瑾紧紧地拉住她的衣角。
盈天扫视了一眼众人,接着道:“听我娘说,果因禅师在世的时候,将我爹视为知音,所以偷偷告诉我爹,除了天心之外九龙窠的后山上还有一个地方有大红袍。你们都知道,我爹可是茶痴一个,后来他就偷偷将那茶苗移植下来,种在下梅后山一个山凹里。他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一个人,连我娘都没说。你要是听我的话,就把孩子放下,你跟我去找。”
“我才不信你呢。”
“信不信由你,反正宁尘禅师不会把大红袍给任何一个人。不行的话,你也来拿刀顶着我好了,我要是不给你茶,你一刀就能把我结果了,我不信你连我这个女人都看不住。”盈天说着,人已经站到方梓龙面前。
茂瑾神色大变。
舜瑾也急了,朝前走了几步。
方梓龙大喝道:“你们谁敢上来!”说着,他将刀朝小妞脖子上轻轻一挑,一股鲜血一瞬间流了出来。
整个宅院里霎时间没了声音,连方梓然都停止了啜泣。
“呵呵,”方梓龙大笑着将刀从小妞脖子上放下。他一只手缓缓地放下了小妞,迅速把盈天拉了过来。
小妞哭喊着奔向茂瑾,梓然扑上去,一家人拥抱在一起。
而这时,盈天已经被方梓龙死死地抓在手里动弹不得。她朝茂瑾看了看,看见茂瑾在小妞头上狠狠地亲了一下。
茂瑾猛地扬起头,难过地看着盈天喊道:“盈天,你不能。”
盈天没有说话,现在的她脑子很清醒。她必须坚决,而且,她知道她不会输的,因为,她怀里藏着一样东西一那只精美的小手枪。这是赵修走的时候留给她的,她曾经见他用这把枪轻而易举地射落了高墙上的一只花瓶。
“哦,有什么不能的,他要什么我给他什么就是了。”说着,盈天抬起头,像是领着方梓龙一样,从庞家的二进宅院里走了出去。
刚走到门口,盈天回过头,对茂瑾一笑道:“茂瑾,收好桌子上的那个匣子。这是我爹还你的。”
茂瑾没有回头,而是迅速地追了出来。然后,舜瑾、英瑾还有庞家的家人都追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