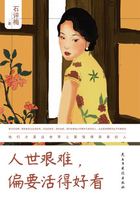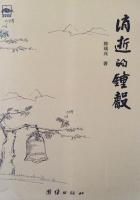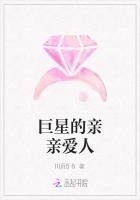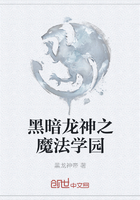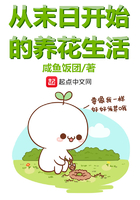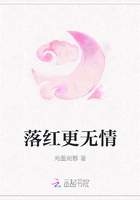我和姐姐从父母的出生地和名字中各取出一个字,组合成“景静”和“宁瀛”,作为我俩的笔名,通信和写诗互赠,就用笔名落款。我内心里还有别样的兴奋,童年时我随父母直呼姐姐其名,被母亲多次纠正。这下好了,我可以理所当然地称呼姐姐为“景静”,和她平起平坐了。
从前可不是这样。我正在为从幼儿园晋升到小学而兴高采烈时,却发现姐姐已经趾高气扬地敲上队鼓了。其实我也就晚她出生三年,加上姐姐早一年上学,小学时我俩相差四年。可这四年却让我足足地矮她一大截,总在后面追着跑。但这四年也让我尝足了甜头。同龄人还在看连环画小人书,我已经看小说了;此外,我用“九宫格”学毛笔字、学着吹口琴、毛笔字练“柳”体等等,都比同伴们超前。这些少年时的奋进都是源于追赶姐姐、模仿姐姐。
然而特殊的年代加快了缩短我俩之间差距的速度。
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赶上了缩短教育的头班车,不到十年工夫,就拿到了掺和着水分的高中文凭。高中时我只比姐姐晚了一届。高中毕业我俩先后插队,姐姐先一步回城当了工人。恢复高考,我俩齐头并进,一同考上大学,成了同届校友。
20世纪80年代,我俩相隔四天结婚,后来又前后脚到了美国。
20世纪90年代初,我俩读完书,各自开始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并先后晋升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如今,她仍然做卫星研究,我仍然做工程设计。
用“景静”和“宁瀛”互称的兴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从那时起,我俩真正开始了人生的体验。从插队农村见识中国农村社会,到一夜之间金榜题名,头戴七七级光环;从再次“洋插队”的磨炼,到如今在美国文化中的自如自在;从懵懵懂懂的少女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历了十月怀胎的喜乐,也饱尝了失去父母的哀痛。三十余年中的跌宕起伏,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责任和奋进耗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夜深人静,当我脱去全职女性的行头,卸下为人妻人母的盔甲,放松疲惫的身躯之后,在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不能让我遗忘的角落。在那属于自己的角落里,藏着我和姐姐年轻时的梦想。
李玫
2008年3月30日写于宁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