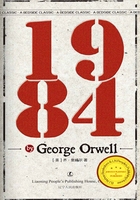她依然是手握大权的临邛王的爱女,皇后的亲侄女,即使不再掌管内务,太子府中也无人敢对她无礼。
只是众人的眼神不再如从前那般虔敬驯服,而是如看到瘟疫般的避之惟恐不及的躲闪。
特别在许思颜身边那些没有名分的侍姬们被太子妃雷厉风行扫地出门后,众人看她的目光更是怪异。
谁都知道为了那些缠着太子的通房丫头,她明着暗着说了多少次,甚至当着许思颜的面委屈哭了好几回,许思颜都以他一惯的温柔安慰了她,然后宽容了那些被她暗中打压后竟敢反击的贱婢们。
她掌管太子府九年,都没能把那些苍蝇似的盯着太子的女人赶走。
因为太子的风流性情,那些敢于觊觎他的女人甚至越来越多。
她以为呆在太子身边,注定了这辈子都得和这些女人斗下去。
可萧木槿正式权掌太子府才几天,问都没问太子一声,便干净利索地把对手赶得一干二净,并成功地将太子从书房直接扯去了凤仪院。
如今太子身边的女人,只剩了有品阶有封号的慕容依依和苏亦珊。
苏亦珊对太子妃很恭敬,且她兄长苏落之曾在伏虎岗搜救过太子妃,于是木槿不但没为难她,还封赏了她好些东西,包括若干珍贵纸笺,几方老坑端砚,以及许多狼毫、羊毫、紫毫等各色毛笔……让她继续安安份份地呆在她的猗兰楼里,过她吟诗弄画的才女生涯。
她当然也没为难慕容依依。
只是慕容依依若继续呆在慕容府,说不准便被她找出什么借口来,把她的蟾月楼都给拆了。
”郡主,这样不行呀,我们太被动了!“
张氏十分着急。
慕容依依踌躇良久,说道:”上回让父亲预备的人,该用上了。不过,且让我再试一试吧!伤人一千,自伤五百,我也不想自寻烦恼。“
张氏咬牙切齿,”太子妃要容貌没容貌,要温柔没温柔,心机深,手段狠,太子到底看上她哪点?“
慕容依依垂眸,是小鹿般惹人爱怜的温驯,她慢慢道:”除了不够绝色,她其实并不差别人什么。有心机有手段,正是她最狠的地方。“
她捏紧了手里的帕子,”她其实从来不呆不弱,却蒙蔽众人三年,便是在等待时机,一举收拢太子的心和太子府的权!她……做得太利落了!“
张氏恨恨道:”以前真是小瞧她了!如今……郡主连个傍身的孩子都没有,万万不能输给她!“
慕容依依不说话,洁白的贝齿将淡色的下唇咬出了浅紫的痕迹。
这日许思颜照例很晚才回府。
许思颜下了马车,一对绫纱宫灯在前引着,也不用他吩咐,便熟门熟路引向凤仪院。
猜着木槿应该已在凤仪院里备好了晚膳等他回去,虽疲倦了一天,他的脚步不觉轻快起来。
沈南霜跟随在他身后,惴惴地看着他,”太子,近来你看着有点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太子看着公文,有时半天都盯着一页不动弹;好容易闲了片刻,喝着茶看看风景,还会突然笑起来……“
”笑?“
许思颜脚下不觉一顿。
他有这般失态吗?
近日因谋逆案游走于众臣之间,看着形形色色的笑容,听着真假难辨的话语,不得不打足十二分的精神,给些高深莫测的回应,当然很是吃力。
如今被沈南霜一提,才觉自己虽累,但心情却很不错。
前方隐忧重重,迷雾阵阵,他辛苦一日回来,居然还有兴致调戏他的小妻子。
仿佛每晚唤几声”小槿“,看她一改白日的骄矜伶俐在身下婉转娇吟,泣泪求恕,他便能心情大好。
忆及夜间的无穷乐趣,许思颜忍不住又唇角扬起,”我常笑又有什么不对劲了?倒是你,总是心事重重的模样,整天皱着眉,也不怕年纪轻轻便长出皱纹来!“
他拍了拍沈南霜的肩,正笑着时,却见沈南霜的面庞着了火似的泛起红晕。
猛地便想起兵乱之夜两人的狎昵,以及他事后的承诺,他的笑容便不由得有些异样,忙缩开了手去,再不肯过于亲近。
若被木槿知晓,也不知下一个被她逐出太子府的,会不会就是这个老实巴交的沈南霜。
”太子殿下!“
正沉吟之际,前方忽有人唤道。
许思颜抬头,便见慕容依依纤弱身影袅娜而至,款款行礼。
他扶过,微笑道:”依依,你不是病着吗?这入夜天凉,怎站在这风口里?“
慕容依依柔声道:”太子日夜劳碌,不辞辛苦,妾身着实放心不下,又好些日子不曾见到太子,着实牵挂,所以过来瞧瞧。“
她打量着许思颜,”气色倒还好,只是还是瘦。回来这些日子,也不曾补上来么?“
许思颜道:”还瘦么?我自己倒不觉得。“
张氏在后笑道:”太子这是只顾牵心国事,忘了保养自己吧?良娣倒是日日牵挂,每日做了太子喜欢的羹汤备着。可太子近日贵人事忙,想来早将良娣抛诸脑后了吧?“
慕容依依眼圈一红,低低制止张氏道:”嬷嬷,住口!太子自然当以国事为重,岂可一味将儿女私情萦挂于心?“
许思颜垂眸瞧她,”何尝没记挂你?只是你既病得不轻,自然需好生静养,哪能无事过去扰你?“
慕容依依便浅浅一笑,”近来并无俗务缠心,倒也养得差不多了。因清闲得紧,这几日的确每晚会做些寻常咱们爱喝的羹汤。恰我父亲的老部下前儿送了一对山鸡,傍晚令人收拾了,还是用上回的那几味补药炖了,这时候火候正好呢!“
她仰脖看他,细巧的脖颈颀长而优雅,剔透得让人忍不住想伸出手来温柔抚触。
她对着镜子试过很多次,这模样神情如天鹅般柔美婉媚,说不出的惹人怜爱,却又不失大家风范,最能牵动人心。
许思颜的黑眸里映着她的脸,果然抬起手来,却只将她被风吹散的衣衫拢了拢,笑道:”好,回头去尝尝依依手艺。今日说好与太子妃用晚膳,只怕我不回去,她会饿着等我。“
他拍拍慕容依依的肩以示安慰,转身便欲离去。
慕容依依忍无可忍,叫道:”太子心疼太子妃,怕太子妃饿着,原是情理中事。可妾身跟了太子九年,太子怎不问妾身有没有等着太子用膳,等得饿不饿?“
张氏则在一旁落下泪来,”太子,良娣一直说太子情深意重,如今病着,便是分身乏术,必定也会每日过来瞧上一眼,哪日不是算好太子快要回来的时辰,早早预备好晚膳?可每天都等不到太子身影!良娣忍着不说,可背地里落了多少的泪?瞧这些日子,良娣又瘦了多少?“
许思颜不觉冷了脸,”张氏,你这是指责我冷落了良娣?只为让她安心养病,太子妃一边侍奉父皇,一边担下了府中内务。她又年轻未经世事,我难道不该每日多照应些?你既知良娣不好好用膳,怎不劝说照顾,由她一味胡闹?若再病得重了,是不是打算说全是太子过错?“
沈南霜在后忙劝道:”太子消消气,想来张嬷嬷也是一时气急,说话冲了些。“
往日慕容依依受宠,张氏亦受敬重,从未受过这等训斥,此时不由惊得跪倒,却哭道:”奴婢何尝不劝,也要良娣肯听!从来心病难医,良娣一心牵挂谁,我便不信太子不知!“
慕容依依已哭得气哽声塞,身体一晃已倒在地上。
张氏和从人忙扶时,慕容依依强撑着跪到许思颜跟前,喑哑泣道:”我知江北之事,太子与皇上,都疑着慕容府有异心,太子从此也便不待见我。可请太子细想,依依既然将终身托付太子,慕容府与太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断无谋害太子之理!“
她一提及朝政之事,除了成谕、沈南霜等心腹近侍,众人都悄悄退了开去,再不敢细听。
慕容依依见没了旁人,愈发再无顾忌,抱了许思颜哭道:”何况姑姑贵为皇后,独太子一个孩儿,慕容家尽以皇后马首是瞻,必定万事以太子为重,保护还来不及,又怎会谋害太子?我掌持太子府九年,时时处处以太子为念,生怕太子饿了,冷了,累了,病了,从来不怕辛苦……依依和父亲家人的一世荣宠俱在太子身上,又怎敢有半丝谋逆之心?“
”一世荣宠在我身上……“
许思颜默念一声,然后低眸问道:”若我不是太子,你和你家人还会这般情深意切吗?“
慕容依依愣住,然后凝泪望他,”依依在此立誓,若有人敢动摇太子之位,除非从依依尸体上踏过!“
柔弱女子发出的铿锵誓言,向来最易打动人心。
许思颜盯着她,忽然便想起极小的时候,她似乎也这样铿锵陈词过。
那时他只有五六岁,许从悦也只七八岁,刚被接入宫中抚育不久,却顽劣异常,再无半分后来的谨慎细致。许思颜从小被严格管教,反显老成忠厚,便时常被许从悦欺负。
比如抢了笔墨,污了衣物,偶尔还悄悄绊他一跤。
因父亲曾将他抱在膝上说过,从悦自幼失怙,家世可怜,乍进宫来人生地不熟,需多多容让;何况他向来尊贵,并无足以与他平起平坐的兄弟姐妹,难得多出个堂兄来日日做伴,心下十分欢喜,虽给欺负了,也从不告状。
笔墨被抢了再叫人另取一套不难,衣物被污了另换一件也方便,被绊摔跤了也没事,他也可以想法绊他一跤。 便是眼下力气小打不过,父亲不是常说他很快会长大么?
但偏生有一次,慕容依依前来寻表弟玩耍,许从悦不知怎的又看他不顺眼,看着他走过去时,冷不防又伸出脚来使坏,教他结结实实又摔了一跤。
好在小时候矮矮胖胖,衣服也厚实,也不觉十分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