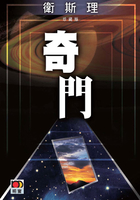仕途上钟副书记可谓轻车熟路、春风得意,可惜人生很少十全十美。妻子年轻轻就没有年轻相,只生一个儿子就横向发展,全无人家林华虽然年老色衰却依然一副魔鬼身材,叫人一进家门静下心来就开始对外面想入非非。更叫人心烦的是儿子逃学,老师把书送到家里来,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管得了华夏县数十万人就是管不了一个儿子,长使英雄仰天叹哟!人家林华却是美满幸福,女儿去英国,儿子去美国,女婿在法国,声言退休后就出去当“国际妈妈”。自她当人大主任以来,就千方百计提高人大决策力,美其名为“发挥职能”。他已通过关系要提拔林华到市里去,只要她一走,他的路就愈走愈平坦宽广了,就可策马挥鞭驰骋华夏了,那时就只剩下一件事无法做到——把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摘下来给儿子戴上。他要利用换届这个良好契机组织县委、县政府两套年轻有为的班子。当然要出于公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初出道时没经验,险些断送自家前程。但不知怎么搞的,当过孙中山先生总统府咨政的一位老叔公错误的经验不时地在脑海里波浪般掠过。老叔公在他的书里说:“欲成大业者,须先依附他人,后自立山头。”前一轮人事调整,虽有杜青山书记主持,但他还是有备无患地准备了一张名单。宦海瞬息万变,半年后的今天,杜青山书记升官去了,一大批踩着年龄线的部局长又多了一岁,还有的甚至英年早逝如梅文夫。哀哉文夫!钟副书记十分看重此君。
当钟副书记还是钟老师的时候,就十分佩服这位有研究员和二级作家双重职称的副局长。他的书架上有亲自到书店买来的三本梅文夫的著作。他是成了分管文教的钟副镇长以后才结识梅文夫的。那回梅文夫执行局务会决定到东湖镇来办事,承包县歌剧团的市广告公司经理就是东湖镇人,欠剧团十几万元不还,东湖镇配合催讨无效,梅文夫主张诉诸法律,阮旺局长叫梅文夫辛苦一趟。镇长叫钟副镇长接待梅文夫副局长。一个上午,钟副镇长就被感动了两回。因为镇政府至今还在一家旅美华侨十几年前才建造的华夏县特有的皇宫体式的房屋里办公,钟副镇长要借此向他崇拜的梅作家表现博古通今的学问,就大讲这一种有高翘屋脊雕龙画柱宫殿般建筑的由来故事。他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华夏县,在围观的人海中看见一位包着头巾的美女,国色天香,后宫佳丽无人能比。美女姓黄,被风流天子带回京城。临幸之夜,乾隆叫美人解下头巾,美人羞涩不脱,乾隆时已神魂颠倒、急不可耐。一夜游龙戏凤极尽欢悦。第二日上朝就封皇后。不久,乾隆发现黄皇后原来头上生疮寸发不生像一盏电灯泡,因此长年累月包裹花头巾。但是乾隆还是万般宠爱,黄皇后万般如意,只是逢大雨就悲切不已。乾隆问其故,答说老家破屋,日出十八天窗,落雨十八漏孔,不知寡母怎生度过。乾隆龙心大动,说“爱卿休虑,朕赐你母皇宫起”。黄皇后借“母”与“府”谐音,传旨时说成“朕赐你府皇宫起”。一字之差,皇恩浩荡,华夏县所在府县都仿效皇城宫殿样式结构建造民宅。巍峨壮观,还有石狮子镇守大门两边,两个门扇上还画有唐将尉迟恭和秦叔宝荷剑执戟站岗护卫。钟副镇长一讲完,梅文夫就大摇其头,质疑说“不可能不可能,故事情节不成立。第一,乾隆会宠爱一个臭头民女?第二,立皇后乃朝中大事,岂能第二天就下旨封后”。钟副镇长听了不高兴,说“这是民间故事,你梅局长就会认死理”。他对梅文夫颇有了解,他认为梅文夫和阮旺合不来原因就在于认死理。据说阮旺在局务会上指责他反对把歌剧团承包给广告公司,是反对改革,而他针锋相对地说:“我承认歌剧团眼下像曹操吃的那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就真的没有活路可走了么?就不能像郭嘉说的,先退兵后图良策么?承包给广告公司,无异于承包给一个泡影!”但他认死理有啥用,人家阮旺最后一言以蔽之:“我是局长,这个局我负责,你仅是一个助手,借古讽今啥?请免开尊口!”当官又不是写文章,能认死理么?有死理可认么?虽然不幸而被梅文夫言中,但当副官只有擦屁股的份,要是认死理就没有当正官的份,不仅不能转正,连副官都会没得当!瞧这厮还毫无自知之明,高傲得很哩,兴许眼里压根儿就没有我老钟的影子哩。想到这里,他一改恭敬态度,以半是教导半是揶揄的口吻说道:“梅局长,官场上不能认死理呀!”梅文夫听懂钟副镇长的话,沉思良久,问道:“老兄有何见教?”钟副镇长说:“灵光点,灵光点,尤其是我辈书生!”梅文夫笑了笑问道:“老兄是说当两面派?”钟副镇长抬头看了梅文夫一阵,心里想,真是距离产生美,今天零距离一看,身上的光环全不见了。他也笑了笑说道:“我去过泰国,看了人妖表演,一种扭曲的人性和扭曲的艺术,也很够精彩。有一个节目叫《两面人》,那人妖从舞台左边走向右边,观众看到的是西装革履,油光可鉴的背头,留两撇八字胡,真他妈整一个日本太君大大的坏。灯光一暗,从右边走向左边,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个妖娆美女,长发披肩,穿绣花鞋,着透明低胸短衫,袒露两只翘翘的大肥乳,一抖一抖很诱人。两面人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很受欢迎,掌声如雷。”梅文夫若有所思,不知是不想说话还是不知说什么。说话间已经来到县广告公司经理的家里。钟副书记是主人先说话,说到钱便无缘,经理含千古不白之冤似的跳起来说道:“你别说,叫你们镇长来跟我说!”钟副镇长无奈,指着梅文夫对他说:“我官太小,奈何不了你这位县级干部,这位是社会事业局梅副局长,他有权力说吧?”经理哼了哼,对着梅文夫说:“你不知道,我不跟你说,你叫阮旺来跟我说!”梅文夫生气了,说道:“欠债还钱,自古皆然,我们是认为区区十几万元,不必上法院吧?”经理愈说愈嚣张,倒好像欠债的是梅文夫,指着梅文夫的鼻子吼道:“上法院我奉陪到底,但我要告诉你们,我要是输了,顶多就还十几万元,你们社会局,还有你们东湖镇的工作,最少要停顿半年!”两人一无所获地离开经理家。
这一天,梅文夫身上的光环虽然在钟副镇长眼里消失了,但消失不了崇拜作家、学者的心中一结,过后想起来,还颇受感动。政治家是悲剧的制造者,惯于抓任致命之处打击对手,梅文夫此君虽然与阮旺水火不容,却是只停留在“寻思”而没有“寻根”去打击对手。梅文夫虽然认死理,但却也顾全大局,愿意替人擦屁股。聪明的当权者就该用这种人,使用安全又能排忧解难。可惜,可惜呀,居然步李太白江中捞月醉乡,终魂断凉台。哀哉!钟副书记今日清早想起梅文夫,还不禁扼腕叹息。
早餐时,钟副书记接了县政府办主任的电话后,想起一件事,就给阮旺局长打了一个电话约见他。本想打完电话上床合一会儿眼睛,补回昨晚的失眠,不料阮旺说马上就要来见他,只好抖擞精神,抓起文件包就出门去县委。
一路跟打招呼的人频频点头,如今当政了那些招呼都别有滋味,仿佛阵阵掌声似的。在县委门口,钟副书记遇到阮旺。
“钟书记!”
“哟,这么快呀阮局长!”
受到表扬的阮旺嘿嘿地笑了笑。
电梯刚好下到底层,门开处有几个人走出来,都向钟副书记亲切招呼,仿佛没个阮旺似的,一股冷落感寒气般袭来。
“请,阮局长!”钟副书记一反从前的矜持与自尊,很热情地请阮旺走在头里。
“让列宁同志先走!”阮旺一反常态幽默地引用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话。
众人响应钟副书记的快乐都呵呵地笑起来。
新近安装的三菱电梯干净、亮堂,空调器吹出淡淡的茉莉花香。到12楼时电梯里只剩下钟副书记和阮旺,像接受馈赠一样,阮旺的双手掌接住钟副书记伸过来的右手,五十多岁的老人在四十出头的小伙子面前,虚弱的心脏蹦跳得有点发喘。妈的!什么荒唐逻辑?阮旺很不服气但很快就心理适应了,权力这玩意儿跟埃及金字塔里法老的符咒一样威力无比而又无法洞悉。阮旺待了一会儿,就伸出食指,在钟副书记灰色西装的肩膀上细致地刮着什么,而后加上中指轻轻地拂去污屑。钟书记心里顿时和阮旺近乎了许多。其实钟副书记的肩膀上并没什么脏东西,阮旺凭空的动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梅文夫和刘明敏上班第一天,阮旺也这样做过而且帮他们扣上一个纽扣。这样,尊重、关心和暖乎乎的父爱都有了。可恶的是梅文夫居然不领受,真是天下唯文人难养也!
电梯停留在第12层上,门无声向两边滑开。钟副书记走在头里。常委办公室一律三房一厅:会客、工作、午休;而且都装修得很雅致,电视、冰箱、电脑配备齐全。难怪人家争着当常委,下一辈子吧!钟副书记心头的温热一直坚持到办公室里尚未完全消退,因此很客气地泡茶请阮旺,谈话气氛很好一下子就能切入主题,但是无论钟书记此刻怎么礼贤下士他的语气还是自然而然地带着脱不了的恩赐味道:
“阮局长呀,我一位表哥,看中你的那个排练厅啦!”
近乎亢奋的情绪犹如中弹的小鸟从空中倏然跌落。原来为这个!操他娘!阮旺脑子里一阵轰轰响,受到欺骗和侮辱似的,心里恶狠狠骂着,血管在骂声中膨胀,心和欲望开始萎缩。什么留任,什么升迁,全都梦幻般不真实。阮旺心中顿生一种对抗情绪。妈的,这种鸟事不在电话里说,用得着如此这般故弄玄虚,叫人心惊胆战、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心中那个仇恨就长上羽毛一样扎得难受烦躁。但阮旺毕竟混迹政坛多年,愿意让下属看到自己的喜怒恩威,却绝对不会在上司面前流露不快和怨恨。他明白人的全部灾难有时仅仅是一个瞠目的细小的动作。他对下属自如自在、随心所欲,当着上级的面,绝对温柔谦和、恭敬从命,尽管他不是谨小慎微之人常常坚持不久,但他都尽力了。虽然要把一腔心事装得若无其事,有时也很痛苦,但人的进步是要用痛苦去交易的。此刻,阮旺为了掩饰心中喧啸的海洋,伸手抓起茶几上一只企鹅打火机把玩起来,其认真程度不低于古董鉴赏家。之后,他抬起头来一边欣赏书架上的唐三彩和窗台上的“罗汉双松”,一边听钟副书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