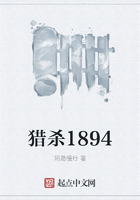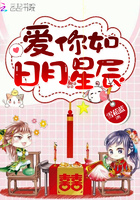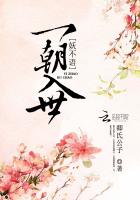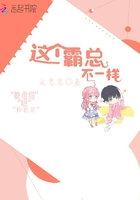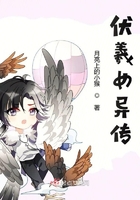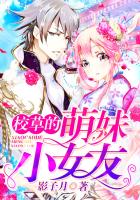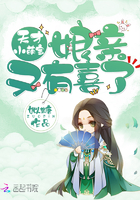李孝恭虽然心知隋朝的大厦将倾,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于是拿起笔墨,在《粮草筹措方略》上修改道:“现有三策进呈”、“策之三:一应军需粮草、马匹除用于前线战事及紧急情况外,不得挪作他用,凡发现有倒卖军粮、马匹以谋私利者,罪当枭首,家资充公。”
李孝恭心想:这第三策虽然是为了避免军用物资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但也只能对中下级军官起到震慑作用,对于那些军中真正的“大老虎”,却也是形同虚设。自古中国就有“法理不外乎人情”的传统,对于那些“大老虎”处理好了固然可以收买人心、巩固统治,然而如果处理不好就既得罪了权贵之人,又失去了民心,这把双刃剑的确不好拿啊!
思忖再三,李孝恭觉得暂时先补充这一条吧,具体的等父亲回来,再详细讨论一下为好。
于是他放下笔,开始在书房里四处打量。由于他本身就是爱书之人,自然将目光放到了榻后的一大排书架上。这里果然藏书丰富。珍贵的秦代竹简、汉代绢帛、皮纸卷轴应有尽有,还有古本《道德经》、《孙膑兵法》。都是后世难得一见的珍品。
李孝恭拿起竹简版的《道德经》,打开仔细观看。由于《道德经》他自儿时就已熟读,对于其间字句更是倒背如流。然而这一看,他却发现,这卷竹简版的《道德经》很多地方与后世流传的《道德经》不同。如:后世是“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而这竹简上却是“阗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情,天地将自正”;还有,后世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而竹简上却是“至虚,极也;守情,表也;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情。情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亡亡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沕身不怠。”
李孝恭心想:后世《道德经》上的“静”字,怎么竹简上都是“情”字呢?莫非老子的意思大道的修炼是守于“情”中,而不是守于“静”中的?这“静”字是后人篡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