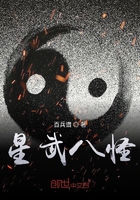一路上陈虎一直注意着路旁抑或是附近会不会有可疑的地方,但都一无所获。到了山下的百合花店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拦住了陈虎的去路。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接过纸条陈虎试图盘诘这个脏兮兮的小男孩。但纸条刚交到手上小男孩就飞也似地跑走了。他没有往哪个犄角旮旯跑去。而是到一个貌似同样是乞丐的大人身边。
“我们原本井水不犯河水,都因为你太爱管闲事。这是我们的家事,希望你不要插手,要不然你的妹妹的安全我可不敢保证。”
汽车掉过头,直接往竹岚的家里驶去。一路上陈虎一直在打电话,总希冀能突然听到竹岚的声音。让另一个兄弟给疗养院打了电话并告知竹岚已经有了下落,让晓珏放心。从电话里陈虎听到了妹妹的抽泣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竹岚在自己的心里已经夺去了无法取代的位置,半夜才到竹岚的家里。狺狺的狗吠声把整个朱维村吵醒了,汽车在逼仄的山路上像一个二级残废的人,坑坑撞撞。
下了车陈虎直接冲到早已熟睡的朱达成家。他还没来得急睁开眼睛,陈虎就一把把被子掀开。
“你们干嘛?大半夜的。”紧接着竹岚母亲发出了一声惨叫,忙不迭的用被子往身上捂。
陈虎没有说任何话,翻前翻后的查看了一遍。最后才质问道:“如果有竹岚的消息要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他把名片扔到了床上。
“你们把岚岚怎么了?她到底怎么了?”竹岚母亲一下扑到陈虎面前,被子被踢到了地上。朱达成像一个刺猬缩成一团躲在墙角,他惊恐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生怕陈虎这个恶魔伤害自己。他尽量保持沉默,盯着床上一动不动。
“如果你们敢隐瞒什么,你们应该知道我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不隐瞒,不隐瞒,绝对不隐瞒。”朱达成怯怯的说。
这注定是一个担惊受怕的夜。有晓珏,有陈虎,有竹岚。他们交织的黑色的夜吐露着蚕食躯体的血液。这是一个奔波的夜,陈虎一直都在路上。他的下一个方向是红河镇镇长刘福贵的家。
当一幢风格别样的别墅出现在眼前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门口有一只硕大的藏獒在忠诚的守卫着自己的家园。
吵闹声很大,但很久楼层里都没有动静。大门被锁着,透过大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村民以为来了小偷,三两个年轻人拿着锄头和铁锹踉踉跄跄的跑过来了。为首的是一位俊俏的小伙子,一绺鹅黄色的头发在车灯的映衬下像璎珞在风中摆动。他放慢了脚步同时示意后面的人减缓速度。他定了定神,看清楚这里的情况,怯怯的问:“你们是什么人?半夜怎么跑到我们村里了?”
“跟他们费什么话,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对,肯定是小偷。”
“你们说什么呢?小心你们的舌头。”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攥紧了拳头提着步子就走过来了。
“大熊!”陈虎厉声喝住了他。然后文质彬彬的向年轻人走去。
“兄弟,我打听个事。”
“谁跟你是兄弟?九三别跟他们废话。要不我回去喊人。”九三没有理他,疑惑的脸上展开了笑容。</p>
“什么事?”</p>
“你们知道刘福贵家现在在哪?”</p>
“你是说刘镇长吧。他不经常住这。一个月也就两三次过来,和一个很年轻的女人。你是不是陈虎哥。”</p>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p>
“嗨,红河镇还有谁不知道您的大名。刚才多有得罪。”</p>
“多有得罪。”其他人也异口同声的表示了歉意。</p>
“哦,没关系。你知道他们还有其他的住址吗?还有昨天有没有看到有个叫竹岚的女孩被抓过来。”</p>
九三一伙人皱起了眉头。他们很想帮助陈虎可心有余力不足。他们对陈虎那次与刘胜的交锋颇为赞赏,大快人心。刚要走的时候九三的老婆也跑了过来,她以为九三遇到了坏人。见到陈虎,九三的老婆一眼就认出了。那天陈虎抢亲的时候她正好在娘家。对刘福贵和竹岚两家也了解。她很快告诉了陈虎,刘胜经常去的地方叫鹤云坊,一个礼拜三四次不等。而且把镇长办公的地方也一一说了出来,拜谢过他们陈虎匆匆上了车。
现在的境况只能等,别无他法。陈虎焦急的把一包中华一路上吸完了,他居然怒斥是谁把烟给吸了。大熊憋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是他自己吸完了。
蒙蒙的天空眯着眼,宣告又一个黎明将要到来。陈虎一夜都没有睡。他把其他人叫醒,驱车直逼镇长大楼。距离红河镇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幢醒目的大楼,矗立在红河镇的正中央。
辚辚地汽车声在熟睡中的红河大街上吼了第一声清亮的嗓子。声音的空旷让萧条的景象更加的突兀起来。大楼的风格特异的有些诡异,在清晨的阴沉下鬼楞楞的像一座神秘的魑宅。大熊看着这么大的物体陈显在面前,竖着耳朵勾起了漫长的思索。陈虎同样对冷冰冰的景象有些抵触,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
时值黎明的碎步刚刚轻落门槛,大门理所当然的紧闭着。焦急的思绪渐渐地涌了上来。
“大哥要不把锁砸了。”
声音走进了陈虎懵痴梦懂的耳朵里,他似乎听得很清楚,但依然一动不动。被晨露****的五星红旗有气无力的彰显出风摆地洒姿。长长的红河街道里这时候有一阵开门的声音,紧接着店门次第像万家地灯火告知你清晨的结束。
陈虎再一次向其中一家店员询问,结果是今天礼拜天镇长大人不会来上班。
“操!”
陈虎终于安奈不住,吐出了这个让他神清气爽的字。然后他从容的从后备箱拿出了一根电棒。这一幕让几个兄弟愣了半天。接着大熊才恍然大悟。但陈虎没有让他们大动干戈,免得让别人看到那么多人,还以为红河镇来了一群土匪呢。陈虎慢条斯理的松了松领带,之后还是觉得不舒服干脆,一把把领带扯了下来,扔到了大熊的脸上。
在闪电地一瞬间,红河镇政府的大门被第一声电棒击响了。声音和破铜烂铁的没什么两样,依然是铁固有的属性。接下来的两下把大门各自捅了一个凹坑,显得对称好看。有人停下了脚步细细聆听这刚刚洗去的清晨后是谁将和谐撕裂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诠释着一览无余的愤怒和无懈可击的本分。
事毕,陈虎使劲的甩了甩手,骂道:“操,震麻了。”
奔波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所有的人都打不起精神。亮子从昨天到现在打了十几个电话。陈虎知道是什么事,无心去听。
剩下了惟一一个地方。
其他的一无所获把积怨和恼怒一起堆叠到了鹤云坊。或许现在的陈虎就像是三天没有进食的猛兽,眼睛红通通的,布满了血丝。鹤云坊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如果刘胜把竹岚藏起来了,想必也不会大摇大摆的出现在鹤云坊。即使有这样的想法,陈虎还是决定去一趟。
下车后陈虎一群人不分青红皂白把赌博现场打砸的一片狼藉,等老板回过神来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他傻了眼,老板娘从楼上匆匆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看到大熊拿着一根手臂粗细的木棍立马住了嘴,返回到楼上。
临走的时候陈虎扔下了一扎钞票,客客气气的说道:“兄弟,对不住啊,哥们今天火大,借个地方发泄一下。”
当车开到一片开阔的路上时,陈虎让大熊停了车。他下车后,仰着头,使劲全身的力量喊出来。毒素没有排解掉反而又加剧。一群兄弟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说话,他们跟随者着陈虎的一言一行,打砸劫舍无所不敢。
一天一夜没有看到竹岚,陈虎无法想象她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处境。他不敢往下想,他怕这样的想象会击垮自己内心的平衡,他知道一个人倘若心智失去平衡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脑海里都是竹岚的样子,一分一秒都在他的脑袋里播放着无法消去的影像。这样的痛苦是匕首一刀一刀刻上去的。
找到刘胜是第二天的下午,但是刘胜一口咬定自己从上次到现在一直没有见到竹岚。他的坦然自若看起来毫无破绽。陈虎完全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刘胜的瘦小的肩膀。拎起来像一只可怜兮兮的母鸡,但它是乐观的母鸡,死得其所。
眼前的刘胜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陈虎把他使劲甩到地上,并没有摔倒。刘胜一个趔趄退到了一棵香樟树边。他依然堆着笑脸,满不在乎。大熊圆睁的大眼快要飞出来了,但也没有吓到这个似乎天地间可以纵横捭阖的羸弱的人。
陈虎的手在抖,他的嘴唇张弛的有些失去理智。这也许是一个信号的传递。
气急败坏的大熊一把把刘胜拎起来高高的举过头顶,刘胜仿佛吓破了胆,嗷嗷的叫了起来。
“到底说不说?不说的话老子摔死你。”
“你先放我下来。我就说。”
大熊犹豫了一下,胳膊一松,一堆骨头顿时从高空坠落,稳稳地铺在了地上。刘胜捂着肚子翻来覆去的叫着疼。陈虎以为真的摔到了,让大熊看看。没想到刘胜从背后抽出一把匕首向大熊刺去,正中心脏。刘胜爬起来就跑,陈虎让两个兄弟赶紧去追,自己和另外一个兄弟把大熊扶到车上,温热的鲜血把车厢染红了。腥红的气味弥漫着陈虎的整个世界。
在半路上大熊就不行了。悲伤之余陈虎姑且让亮子给大熊料理后事,并且给了他的家人一些钱。
刘胜被跟丢了。
儿子欠的债老子可以还,但刘胜的老子刘福贵。断然称自己与犬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对于他的生死他暂不过问。
“刘叔,这样吧,我们到内室谈一谈。”
没等刘福贵答应,陈虎早就窜到了办公室。只听门咣当的一声,紧接着刘福贵被推搡到了办公桌上。
“你想干嘛?现在可是和平年代,由不得你胡来。小心你的后半辈子。”
“可以把你的狗儿子喊回家吗?刘叔”
“哼,小**。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耍横。”
陈虎闭上了眼,做一次深呼吸。他让刘福贵从办公桌上下来站好。搞得刘福贵莫名其妙,他站起来掸了掸褶皱的衣角,刚一抬头,就被陈虎飞来的一脚踢到了脸上,顿时这个同样和刘胜精瘦的老头往右侧倒在了地上,恰巧的是他的头载到了沙发上,把他弹了起来滑落到了地上。他油光可鉴的发型顿时凌乱了,他呻吟的同时还不忘梳理资源并不富裕的头发。嘴角被磕破了,他从嘴里掏出两颗泛着青菜味和血腥味的牙。嘴里流出了鲜血,他说话开始含糊不清,没想到这是他仅存的两颗牙。
陈虎一把把他提了起来,质问道:“把你****的儿子叫回来?老东西。”
“年轻人你愤怒了,愤怒可以让你失去理智。没有理智的人就是一条疯狗。所以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的办公室有摄像头,刚才的事情全程录了下来。明天你就等着坐监狱吧。我可以让你一辈子都呆在里面。你不要妄想毁了它,我还有隐秘的摄像头。”
深秋的寒气并没有把罪恶凝住,它伸长着纤细的爪子只是轻轻的抚触每个人心中的伤痛然后裹卷着冷言笑语向着远方一个不知名的方向飘去了。飘去的有一缕青烟,在眷眷细语中吐露着陈虎内心疯狂生长的愤怒和孩童时残存的平和。陈虎把自己如同寒秋一样冷冻了起来。他一天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他静静地坐着?该何去何从?
亮子赶过来的时候是礼拜二。他向陈虎事无巨细的交代了公司和大熊后事的有关事宜。晚上一辆警车高调的在大街上悠悠的呼啸而过,向着陈虎的住处奔来。他来的理所当然,如果它有生命,他一定会这么想。
监狱对于陈虎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不可触及的地方。他又一次的与它擦肩而过。他彻底愤怒了。
他的愤怒的同时迎来了一个人。
陈虎看到她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能现出欣喜和幸福的征兆。他依然用平静来看待眼前的这个人,仿佛她真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与自己萍水相逢的普通朋友。
“最近怎么样?听说你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了?”
“......”
“别一见面就这幅表情。”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想见到你。”
“别把话讲的这么绝。毕竟我们还是曾经的恋人呢!你可以不想见到我。但不能剥夺我想见你的权力。”
“你可以走了。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还有那些东西不要再碰了。”
“早就不碰了。金盆洗手了。你看看我的手洗的多干净。”
申雪把白皙的有些恐怖的手伸到了陈虎的眼前。他的恍惚的眼神仿佛没有捕捉到任何物体,痴愣愣的一排爪子动了一下,然后縮了回來。
两个人的交谈时断时续,沉默已经诠释了时间吞噬的东西再也弥补不回来。陈虎没有吭声,穿上深赭色的风衣甩门而去。汽车要走的那一刻申雪的手抓住了方向盘继而像一个在威严的父亲面前调皮的姑娘,不顾父亲颜面艴色骄矜一屁股歪到车里。在不耐烦的趋势下汽车还是迈开了步子。
中途亮子也赶了过来。看到申雪也在,亮子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客客气气的叫到:“雪嫂。”
“亮子注意称呼。”陈虎严厉的说道。
“怎么了?喊我嫂子怎么了?这也看不惯啊。前两天我到你的公司去看了看,还是老样子。我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了。这一去居然没有惊喜。当初我让你......”
“闭嘴。”
“火气还不小。我现在多多少少也赚了一些。上次的事情已经有人替我坐牢了。只要我没被警察抓到把柄以前,一切都可以说是积极的。我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次是真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你倒好,不说请我喝杯茶,还赶我走。幸亏我了解你的脾气,说的都是违心的话。要是不了解你的人还以为真的让我走呢。”
“你说完了吗?可以走了?自己把门打开。”
“你******真不识抬举。老娘从来没这么卑躬屈膝的向一个男人乞求过,你别蹬鼻子上脸。天下男人多的是,我干嘛要在一棵歪瓜裂枣的书上把自己吊死,我有病啊,切。”
“你那么同情达理,干嘛出现在我面前。滚蛋。看到你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压抑的我喘不过气来。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求求你了?”
“操,铁了心了是吧。行,你有种。狗叔让我来劝你先把个人感情放一放,回去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既然你这么不待见我,我也就不厚着脸皮硬往某些人身上靠了。”
“什么事?”
“狗叔想把会长的位置退下来?”
“噢,弟兄几个谁当上会长我都没有意见。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足够了。在这个世界里我觉得太累了。不想参与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我追求自己想要的。就这么简单。”
“如果事情都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干嘛还要亲自来请你入宫。打一个电话不就行了。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会长的一片苦心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面面相觑,无言相对。夹杂着彼此的过去,即使嘴上说可以放开,可我们都知道有些话终究是违心的,讳莫如深的心里清楚的比明镜还要透亮。加之会长的事情和竹岚的事情陈虎的脑袋一时间空白的就像一张白纸。思绪飞乱,就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无法掌控自己的方向,任凭自己垂直的跌倒。
他想清空记忆,可记忆里总会有一个人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思念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看不到摸不着。她只在自己的想象里,她有时是摇摆不定的风筝,颇许稍大的微风就能把他吹向梦的碎片里。这时候梦开始苏醒。苏醒的梦还是痛苦的,现实是冰冷的墙,除了冰冷他没有血液的温衬到处寒气逼人。苏醒的梦里滋生了消极和无奈。可无奈的背后总有逼迫将自己挺立起来,重新看一看前面的人。或许那个背影就是你想找的人。
车里多一个人陈虎总觉得不自在。他只想和亮子干脆利索的行进。可申雪是典型的不会省油的灯,一哭二闹三上吊,死缠烂打等等手段样样精通。她说自己最失败的人生不是干了违法的事,而是没有让自己喜欢的人爱上自己。
最终陈虎还是把申雪扔在了一家超市门口,趁她购物的时候闪电逃脱。思维清晰的时候方向感没有了。陈虎看了看满脸狐疑的亮子,他们同样的表情揭示了他们同样的疑问。该往哪去呢?
按着原来的路线再一次到竹岚的家里。家里的境况没有陈虎想象的那么令人焦急,而是不慌不慢,悠悠然然。朱达成靠在石墩边和一个人在说话,嘴里不停的吞云吐雾。他故意不看陈虎的车子。不过他的额头慢慢的沁出了细密的冷汗。他有些神色慌张,陈虎在他眼里犹如一条饿狼,随时都会把一切的生物当成自己的猎物。他还是无法拜托阴影不散的心,草草的把烟扔了。朱达成匆匆的钻进屋里,留下那个说话的人莫名其妙。
咣当的踢门声还是冲破了朱达成惊惧不安的心。他和老伴躲在屋里故作镇静的看着电视。老伴则病吟连连,嘘声叹气。陈虎还是老生常谈的问起了竹岚。
“没有。”老伴一口回绝。
“她有没有和家里联系?”
“我说了没有。”
一旁的朱达成生怕老伴粗粝的语气惹怒陈虎。他伸着畏畏缩缩的干枯的老茧手扯了扯老伴的衣角。不让她再多说话。老伴这时候越说越有勇气,仿佛她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态度似的。没有头绪,陈虎不再多问,还是那句话,如果竹岚回家请给我回个话。
临走的时候陈虎听到了女人骂骂咧咧的话:“你算个什么东西给你回话。”
“就是。”
亮子返回的脚步被拦住了。
去鹤云坊的路上陈虎遇到了九三。没等他问,九三就把看到刘胜的事情说了出来。但是到家的时候家里阒无人影,看来有人偷偷的透漏了消息。陈虎猜到了朱达成会这么做,他总希望竹岚能嫁给可以让自己衣食无忧的官二代。完全忽略了竹岚自己的感受。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陈虎分遣几个兄弟各自蹲点竹岚家,刘胜家和镇长的办公室。好消息传来的很快,但对于陈虎来说是一个噩耗。竹岚由于想要逃脱刘胜的魔抓,从二楼窗户上跳了下去,目前的情况还不清楚。在医院里,除了竹岚的母亲以外,陈虎没有看到任何人。简陋的病房设施很不齐全。
“你们来干嘛?你们这些**把我女儿害成这样,还嫌不够吗?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大娘,你有没有用眼睛看哪?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是在......”
“亮子!”
陈虎没有让他说下去。病床上的竹岚全部用纱布包着。头部的血已经把纱布洇红了,右腿小腿骨折。医生说还没有度过危险期。陈虎马上联系了省内最好的医院,想要赶紧把竹岚转院。可是不仅受到竹岚的母亲的掣肘,医院的阻挠有些让人心生非议。两个护士死活不让陈虎把人转走,而且另一个胖胖的护士驮着震颤颤的肉请来了救兵。几个男医生跟着一个貌似领导模样的人。此人五十岁左右,稀疏的发型已经成为了他不得不是领导的标志。
果然一开口就态度强硬,陈虎扰乱秩序,他说违反了医院的规定。
“操,违反******什么规定。老子把人转走违反了哪条规定。”
“你他妈是不是活的不耐烦了。我们把嫂子转走是看得起你。要是有什么意外你们能但得了这个责任吗?”
疑似院长神秘的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踉踉跄跄的款步而来,轻蔑的说:“今天你们休想把我的病人转走。”
“腰杆又硬了。秃子。别学人家态度强硬,没有好果子吃。”
疑似院长理了理飞舞的几根乱发。给旁边的几名医生使了眼色。顿时医生们像打了鸡血似的向陈虎冲了过来。陈虎说时迟那时快飞起一脚,正中下颏,一阵沉闷的落地声把整个平衡都打破了,大地颤抖了。厮打声把其他的人都招了过来。陈虎和亮子看到人越来越多,有些招架不住。两个打上瘾的医生趁陈虎不注意一把拽住胳膊,反扭到背后陈虎岂能被这小小的挫折吓到。他定睛一看,两双46码的大脚把自己围了起来。他使劲全身力气把脚提起来,脑海中汇集着无数辆起重机的样子,然后把这些幻想中的起重机踩到对方的脚上。他速度很快只听见两个男医生哇哇的叫唤起来,扳着脚像得了羊角风似的在医院的走廊里单腿跑路。他们单腿跑的很快仿佛这样真的能迅速的减轻痛苦似的。
“两个废物!”疑似院长骂道,自己却远远地躲在后面。
“怎么回事?”一阵红亮的声音从密集的人群中传了出来。
人群分成了一条小路。一个同样是资源稀少的家伙装腔作势的插着手挪了过来。
“操,又一个秃驴。”亮子哂笑道。
“你说谁呢?”
“你觉着这里有几个秃驴?”
人群里有人窃窃的笑了起来,准领导哼了一声,窃笑声立马消失。
“你是他什么人?”准领导严肃的问道。
“朋友。”
“朋友?哼。那又是怎样的朋友的呢?朋友有权力不顾她的生命安危吗?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你何德何能有理由可以把我的病人转走?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或者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说用行动也可以表示。”
“你要是表示的让我们满意,我立马让你把人带走。她现在就是一个死人我要了跟废人一样。你要是做的让我开心了,这个女人就可以拉走。”
“畜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的女儿。”竹岚的母亲向人群后的这个声音骂道。
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是刘胜。他锃光瓦亮的头发在节能灯的光照下居然熠熠夺目。他嘴里嚼着一根棒棒糖,像一个未断奶的孩子允吸着****似的。他瘦弱的身子从人群的狭缝中顺畅的溜了过来。他打量着陈虎,从头看到脚,面部表情随着看的部位千变万化,难以猜测。
“怎么了?没胆了。我就知道一到关键时刻都他妈是娘跑。哼。你连这样的要求都达不到,凭什么竹岚会喜欢你。你就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畜生,一点人性都没有。”
“你说够了没有?”亮子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
“少废话,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这么多人在这看着。我岂能戏言。”
<p>刘胜抱着胳膊撇着薄如刀片的嘴唇,他的舌头在嘴里不停的在翻动棒棒糖,整个脸部的肌肉都在围着棒棒糖工作。他或许知道陈虎不敢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他想看看陈虎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出丑。如果陈虎做不到,他完全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不会再有陈虎的骚扰,这是hēi社会的信用。
“亮子把刀拿来?”
“虎哥。”
“拿来。”亮子不情愿的把一把砍刀递到了陈虎的手上。
刘胜冷笑了一下,他完全不相信陈虎有胆为这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奉献自己的一切。在他的眼里不值得。
陈虎二话没说,伸出左手拇指在刘胜的面前晃了晃,举起刀快速砍下。在拇指落地的一刹那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一幕是意外,也是意料中的事。紧接着陈虎把刀扔到了地上,忍着剧痛走到了竹岚的病床边。就连竹岚的母亲也傻了眼。他被陈虎另类的举动震慑到了,她不知道这是喜还是悲,除了惊惶她的思绪是紊乱的。
临走的时候亮子捡起拇指拖着沉重的刀在陈虎的面前开路。陈虎血淋淋的手托着昏迷的竹岚。看着竹岚安详的脸他笑了。笑的很幸福。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稳稳地抓住了竹岚。她不会在从眼前消失了。
到了省里医院各个部门都做好了准备。陈虎再三恳求院长一定要让竹岚醒过来。亮子磨破了嘴皮子最后陈虎把竹岚的事情安排妥当了才把拇指接上。
连续一周陈虎每天都陪在竹岚的病床前,他没有一丝笑容。憔悴的颜容爬上了他的脸,竹岚醒过来是在第二天下午。夕阳伸着懒腰快要西去,在走的时候顺便把竹岚叫醒了。醒来的时候竹岚发现自己的手被紧紧的攥着。熟睡中的陈虎呓语连连,虽然声音漫漶的不太清楚,但竹岚分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桌上摆放着一束百合花,一袋通红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戊酸戊酯。一封装帧精致的信躺在花瓶的旁边。竹岚没有把手抽开,就这样静静的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她突然感到头有些痛,不经意的抽dong把陈虎吵醒了,他很疲惫的张开眼睛。他没有说话,眼睑无力的在挣扎,陈虎有些昏厥,仿佛这是一个逼真的梦。他努力睁开眼睛,不想让梦如同流星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悲运,眼睛睁开了,竹岚难受的表情呈现在他面前。他的眼角****了,他尽情的让眼角的泪自由奔放,他不知道这是虚幻和真实两者的交叉点。当眼睛再一次的闭上后陈虎像一条蛇一样瘫软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