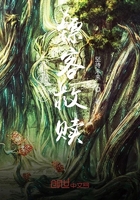是的,生命力论者把有机物质神秘化,使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维勒的科学发现不仅遭到许多“生命力论”者的反对,也遭到了老师的痛击。这场论战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然而,维勒坚定地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他认为:既然一种有机化合物可以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来,那么别的一些有机化合物也必然可以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来!这里面根本不需要什么“生命力”!对“生命力论”进行坚决挑战。最后,醋酸、脂肪、糖……这些有机化合物都一个一个地在实验室中被人用无机化合物合成了,“生命力论”
终于像肥皂泡似的破灭,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被打碎,一个崭新的有机化学时代开始了。遗憾的是,贝采里乌斯没能看到“生命力论”的下场,就离开了人世。
度假村的云雾
1894年秋天,英国物理学家威尔逊到苏格兰的山区度假。清晨,威尔逊站在山顶望着喷薄而出的红日和山间变幻莫测的云雾,不禁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他看着、想着,突然心里一动:“这么美丽的云雾是怎样形成的?人类可不可以造出云雾来?”
威尔逊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实验中心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这里具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仪器设备。度假归来后,威尔逊进入实验室,开始探索云雾的秘密。
经过长期的研究,威尔逊发现云雾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其一,得使潮湿的空气处于饱和状态。其二,空气要很“脏”,而且越“脏”越好。因为“脏”空气里含有大量灰尘,灰尘上面聚集着一些电荷,电荷则把饱和空气中的水汽凝成小水珠———雾滴。
发现了云雾形成的原理,威尔逊进一步想,能不能利用这个发现做些对科学有用的事呢?理论上讲,在一只干净的瓶子里形成了过饱和的空气,如果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带电微粒闯进去,那么在带电微粒周围会立即凝结成一串串雾点,而且这些雾点随着微粒运动形成一条径迹,显示带电粒子经过的路线。若真能实现这个过程,那无疑对基本粒子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威尔逊继续探索着,经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上述理想,发明了“云雾室”。利用云雾室,人们看到了过去只能猜测而无法见到的原子核反应过程,了解到原子核的一些衰变现象,发现许多基本粒子。为了纪念威尔逊的功绩,科学家们给这种仪器起了个名字———威尔逊云雾室。威尔逊也因为发明云雾室荣获了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能否像在原子核里点燃普照全球的熊熊烈焰呢?哈恩没料到,斯特拉斯曼没料到,迈特纳也未料到。然而,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了!迈特纳接受了这一新发现,并由此确立核裂变的理论。从而使科学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核裂变反应”进入化学王国。
十几年后,一位身临其境的物理学家,在费米的葬礼中遗憾地说,“上帝按照自己不可思议的动机,使我们当时在核分裂现象上成为盲人”。
氨气的发现历程
18世纪20年代后期,英国的牧师、化学家哈尔斯,用氯化铵与石灰的混合物在以水封闭的曲颈瓶中加热,只见水被吸入瓶中而不见气体放出。18世纪70年代中期,化学家普利斯德里重做这个实验,采用汞代替水来密闭曲颈瓶,制得了碱空气(氨)。
19世纪末,法国化学家勒夏特利是最先研究氢气和氮气在高压下直接合成氨的反应。很可惜,由于他所用的氢气和氮气的混合物中混进了空气,在实验过程中发生了爆炸。
虽然在合成氨的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不少,但是,德国的物理学家、化工专家哈伯和他的学生勒·罗塞格诺尔仍然坚持系统的研究。起初他们想在常温下使氨和氢反应,但没有氨气产生。他们又在氮、氢混合气中通以电火花,只生成了极少量的氨气,而且耗电量很大,后来才把注意力集中在高压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高温高压是最有可能实现合成反应的。
但什么样的高温和高压条件为最佳?什么样的催化剂为最好?这还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探索。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经过不断的实验和计算,哈伯终于在20世纪初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这就是在600℃的高温、200个大气压和以锇为催化剂的条件下,能得到产率约为8%的合成氨。8%的转化率不算高,当然会影响生产的经济效益。哈伯知道合成氨反应不可能达到像硫酸生产那么高的转化率,在硫酸生产中二氧化硫氧化反应的转化率几乎接近于100%。怎么办?哈伯认为若能使反应气体在高压下循环加工,并从这个循环中不断地把反应生成的氨分离出来,则这个工艺过程是可行的,于是他成功地设计了原料气的循环工艺。这就是合成氨的哈伯法。
哈伯把他们取得的成果介绍给他的同行和巴更苯胺纯碱公司,并在他的实验室做了示范表演。尽管反应设备事先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可是实验开始不久,有一个密封处经受不住内部的压力,于是混合气体立即冲了出来,发出惊人的呼啸声。
他们立即把损坏的地方修好,又进行几小时的反应后,公司的经理和化工专家们亲眼看见清澈透明的液氨从分离器的旋塞里一滴滴地流了出来。但是,实验开始时发生的现象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说明再设计这套装置,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避免不幸事故发生。哈伯的那套装置,在示范表演后的第二天发生了爆炸。整个设备顷刻之间变成一堆七歪八扭的烂铁。随后,刚刚安装好的盛着催化剂锇的圆柱装置也爆炸了。这时金属锇粉遇到空气又燃烧起来,结果,把积存备用的价值极贵的金属锇几乎全部变成了没有多大用处的氧化锇。
尽管连续出了一些爆炸事故,但巴登公司的经理布隆克和专家们还是一致认为这种合成氨方法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于是该公司不惜耗巨资,还投入强大的技术力量,并委任德国化学工程专家波施将哈伯研究的成果设计付诸生产。波施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从大量的金属和它们的化合物中筛选出合成氨反应的最适合的催化剂。在这项研究中波施和他的同事做了两万多次实验,才肯定由铁和碱金属的化合组的体系是合成氨生产最有效、最实用的催化剂,用以代替哈伯所用的锇和铀。第二,建造了能够耐高温和高压的合成氨装置。最初,他采用外部加热的合成塔,但是反应连续几小时后,钢中的碳与氨发生反应而变脆,合成塔很快地报废了。后来,他就将合成塔衬以低碳钢,使合成塔能够耐氢气的腐蚀。解决了原料气氮和氢的提纯以及从未转化完全的气体中分离出氨等技术问题。经波施等化工专家的努力,终于设计成了能长期使用的操作合成氨装置。
哈伯合成氨的第二年,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试验工厂,三年后建立了大工业规模的合成氨工厂。合成氨生产方法的创立不仅开辟了获取固定氮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一生产工艺的实现对整个化学工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合成氨的研究来自正确的理论指导,反过来合成氨生产工艺的研究又推动了科学理论的发展。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民族沙文主义所煽起的盲目的爱国热情将哈伯深深地卷入战争的漩涡。他所领导的实验室成了为战争服务的重要军事机构,哈伯承担了战争所需的材料的供应和研制工作,特别在研制战争毒气方面。他曾错误地认为,毒气进攻乃是一种结束战争、缩短战争时间的好办法,从而担任了大战中德国施行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
根据哈伯的建议,德军把装盛氧气的钢瓶放在阵地前沿施放,借助风力把氯气吹向敌阵。第一次野外试验获得成功。接着,在德军发动的伊普雷战役中,在6公里宽的前沿阵地上,德军5分钟内施放了180吨氯气,约一人高的黄绿色毒气借着风势沿地面冲向英法阵地(氯气比重较空气大,故沉在下层,沿着地面移动),进入战壕并滞留下来。这股毒浪使英法军队感到鼻腔、咽喉疼痛,随后有些人窒息而死。英法士兵被吓得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据估计,英法军队约有15000人中毒。这是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毒剂的现代化学战的开始。毒气所造成的伤亡,连德国当局都没有估计到。
然而使用毒气进行化学战,在欧洲各国遭到人民的一致谴责。哈伯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动,战争结束不久,他害怕被当作战犯而逃到乡下约半年。
战后,哈伯庄严地声明:“40多年来,我一直是以知识和品德为标准去选择我的合作者,而不是考虑他们的国籍和民族,在我的余生,要我改变认为是如此完好的方法,则是我无法做到的。”科技的发明对人类而言,永远都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会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用不好,则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发明化学毒气不是化学家的错,而是被战争集团利用的结果。因此,化学武器在战场上的运用与化学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不是哈伯的错。
一波三折的“空气”发现
18世纪70年代初,卢瑟福在密闭容器中燃烧磷,除去寻常空气中可助燃和可供动物呼吸的气体,对剩下的气体进行了研究,发现这种气体不被碱液吸收,不能维持生命和具有可以灭火的性质,因此他把这种气体叫做“浊气”或“毒气”。同年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里也了解到木炭在密闭于水上的空气中燃烧时,能使1/5的空气变为碳酸气,用石灰水吸收后,剩下的气体,不助燃也不助呼吸。
18世纪70年代中期,普利斯特里利用一个直径为一英尺的聚光镜来加热各种物质,看看它们是否会分解放出气体,他还用汞槽来收集产生的气体,以便研究它们的性质。那年,他如法加热汞煅灰(即氧化汞),发现蜡烛在分解出的“空气”中燃烧,放出更为光亮的火焰,他又将老鼠放在这种气体中,发现老鼠比在同体积的寻常空气中活的时间约长了4倍。可以说,普利斯特里发现了氧。遗憾的是他和卢瑟福等都坚信当时的“燃素说”,从而错误地认为:这种气体不含燃素,所以有特别强的吸收燃素的能力,因而能够助燃,当时他把氧气称之为“脱燃素空气”,把氮气称之为“被燃素饱和了的空气”。
事实上,瑞典化学家舍勒在卢瑟福和普利斯特里研究氮气的同时,也在从事这一研究,他可算是第一个认为氮是空气成分之一的人。他用硝酸盐(硝酸钾和硝酸镁)、氧化物(氧化汞)加热,制得“火气”,并用实验证明空气中也存在“火气”。
综上所述,可见舍勒和普利斯特里虽然都独立地发现并制得氧气,但普利斯特里却与成功失之交臂。
法国化学家拉瓦锡较早地运用天平作为研究化学的工具,在实验过程中重视化学反应中物质质量的变化。当他知道了普利斯特里从氧化汞中制取氧气(当时称之为脱燃素空气)的方法后,就做了一个研究空气成分的实验。在试验中,他摆脱了传统的错误理论燃素说的束缚,尊重事实,做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揭示了燃烧是物质跟空气里的氧气发生了反应,指出物质里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燃素的特殊东西。
18世纪70年代后期,拉瓦锡在接受其他化学家见解的基础上,认识到空气是两种气体的混合物,一种是能助燃,有助于呼吸的气体,并把它命名为“氧”,意思是“成酸的元素”;另一种是不助燃、无助于生命的气体,命名为氮,意思是“不能维持生命”。
18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化学家卡文迪许用电火花使空气中氮气跟氧气化合,并继续加入氧气,使氮气变成氮的氧化物,然后用碱液吸收而除去,剩余的氧气用红热的铜除去,但至终仍残余有1%的气体不跟氧气化合,当时就认为可能是一种新的气体,但这种见解却没有受到化学家们应有的重视。
百余年后,英国物理学家瑞利于19世纪末发现从含氮的化合物中制得的氮气每升重12505克,而从空气中分离出来的氮气在相同情况下每升重12572克,虽然两者之差只有几毫克,但已超出了实验误差范围,所以他怀疑空气中的氮气中一定含有尚未被发现的较重的气体。瑞利沿用卡文迪许的放电方法从空气中除去氧和氮;英国化学家拉姆塞把已经除掉二氧化碳、水和氧气的空气通过灼热的镁以吸收其中的氮气,他们二人的实验都得到一些残余的气体,经过多方面试验断定它是一种极不活泼的新元素,定名为氩,原文是不活动的意思。
19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在印度发生了日全食。法国天文学家严森从分光镜中发现太阳光谱中有一条跟钠D线不在同一位置上的黄线,这条光谱线是当时尚未知道的新元素所产生的。当时预定了这种元素的存在,并定名为氦(氦是拉丁文的译音,原意是“太阳”)。地球上的氦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从铀酸盐的矿物和其他铀矿处中被发现的。后来,人们在大气里、水里,以至陨石和宇宙射线里也发现了氦。
接着,拉姆塞又在液态空气蒸发后的残余物里,先后发现了氪(拉丁文原意是“隐藏的”)、氖(拉丁文原意是“新的”)和氙(拉丁文原意是“生疏的”)。
19世纪的最后一年,德国物理学教授道恩在含镭的矿物中发现了一种具有放射性的气体,称为氡(拉丁文原意是“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