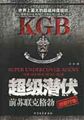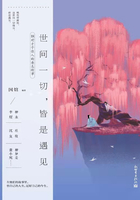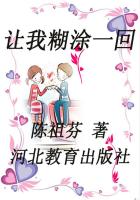一九九零年,我们同时从高考中失利,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不出门,你妈捎信让我去,伸手敲门的时候你就把门打开,喊我一声"姐"。我比你早生34天,我的父亲在小作坊挥汗如雨的时候,你的父亲品着香茗听下属恭恭敬敬地请示汇报;我在大别山区捏着泥巴吃着野果野菜的时候,你在省城武汉抱着娃娃吃着糖果饼干。这样遥远的距离仍然阻挡不了前世来生的缘份,我们只好在此生此世情同姐妹。
一九九一年,我在家养痨病,你背上背着、手里拎着营养品和我喜欢的零食,坐了两趟公交,转了两趟三轮,还步行了一公里,路上向十二个人打听,转辗从你城里的豪宅到我乡下的土房子,说是想看看我圆圆的下巴有没有瘦得尖尖的,说是一个人在家里吃那些零食没什么滋味。
一九九二年,我在学校补习,你说自己玩儿够了应该开始挣钱。你每周三风雨无阻地在我宿舍的床头悄悄放一堆增加营养的食品,每周六喊我去你家尝你煨汤的手艺有没有长进。你说你姐我的病是穷人的命富人的病,比较适合让你来患。
一九九三年,寒假回家时先去看你,你搂着我向同事介绍:"我姐,替我上大学了哦!"一脸的得意。你从柜子里拿出崭新的衣服和鞋子,说是买大了不能退,只好请我回收了;我穿起来有点紧,你拉上我说:"走!我们换个大一码的去!"
一九九六年,单位集资买房,我一筹莫展,你把自己的小金库掏空了给我送来,你说真后悔自己这几年尽想着出去旅游、想着购物,不然的话,就能多支持你姐一点了。
一九九七年,新婚后从安徽回娘家,你孤身一人在火车站等到24:00,第二天用生鲜野味和五粮液招待我们,你说:"新女婿回门,娘家万万不能怠慢,不然他将来会怠慢我姐!"
二000年,我回家给母亲庆贺六十大寿,你说自己家里有别人送的长寿面和滋补品,让我什么也别买,你知道我的小家要养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已经捉襟见肘,见面时一定要塞给孩子一个大红包,说是小姨必须给的。
二00二年,你遍读群书、遍游群山后,自考完武大的本科,终于愿意把自己嫁出去,象你姐一样居家过日子。你姐真想给你置一样嫁妆呀,可是你说什么都不缺了,只要我回去送送你,你说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一定要你姐来见证。
一晃到了二00六年,就在昨天,电话中传来你清脆的声音,说你们在广州订好房了,再去那边你姐就不用住酒店。这些年中,你爸爸瘁然离世,家里的房产成了你抱病多年的妈妈的依靠,你放弃安定的工作到广州陪伴夫君,我知道你们也没多少积蓄,买房肯定是举了债的。
你姐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渴望过--渴望自己是个富人,能够一掷千金,为你置一片屋宇,抵挡南国的湿热空气。
盼过年女儿从学校回来,兴奋莫名,细细问过,原来是快放寒假了,做父母的总免不了多虑:"是不喜欢上学吗?
--所以才那么盼望放假!"女儿摇摇头"不是啦!妈妈,我想时间快快走,我们到外婆家过年去!"我鼻子酸酸的,强作平静地对女儿说:"今年不去外婆家,行吗?"女儿懂事地点点头:"是因为你妈妈不在了,回家看不到她,你会伤心?"紧紧地抱着女儿,不能再说一句话,只怕一开口,拼命忍住的眼泪会化成一阵呜咽。
曾经也是这么快乐的小姑娘,进入冬季就开始数日子,盼望过新年。对于所有乡下孩子来说,没有比过年更幸福的时光了,穿着新衣服,吃着平日少见的糖果点心;点燃"二踢脚",混在踩莲船和舞狮的队伍中上窜下跳;借拜年之名走遍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所到之处,莫不是一团祥和喜气""那样的祥和喜气氤氲围绕着我们成长,直到某一天,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开始追寻成人的理想和幸福,义无反顾地摒弃所有孩提时的乐趣。
而我们最纯真、最珍贵的记忆,就那样深埋在日渐冷漠结痂的心里,从此不敢轻易撕下岁月的封条;就象母亲在世时酿造的过年酒,藏得越深越久就越美味。过年酒是需要用虔诚来精心酿造的,菊花开得正艳时,挑选最饱满的糯米洗净蒸熟,先盛一碗祭灶神;余下的用最纯正的酒曲,在最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发酵,然后过滤封存。过年时开启一溜儿的坛子,母亲闻着酒香就一脸的沉醉,一一指给我们看:这是"摆头""酒精浓度高的酒,喝多了会醉得摇头晃脑",这是"胡子""第一次滤出的酒,味道香甜,糖度高,有胡子的喝过此酒后,一抹胡子,胡子全都粘在一起"。其实我们早就闻香而动了,每个坛子都被我们用酒葫芦舀着解谗过。
过年衣服是请裁缝来家里做的,翻来覆去做不出什么特别的样式;但母亲会在布料上下功夫,挑选最时兴最好的料子,年年保证她的孩子走出去最打眼。鞋子则是母亲用许多个夜晚,一针一线做出的千层底布鞋。母亲的手工活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偶尔来个外地人或者干部下乡,穿了款新鞋,她看几眼,回家用纸反复剪着样儿,剪着剪着就给家人剪出新款式了。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我的鞋子集中了母亲最高的手艺,有时是各种颜色拼接的图案,有时是手工刺绣的花朵,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女儿的脚上开着花儿或者长出小动物。
吃完"腊八粥"就开始准备过年的吃食。杀一头年猪,一部分做腊肉,一部分做熏肉,还得留一部分做滑肉、肉丸、藕夹之类的,只要是家人提出的要求,在过年时母亲都会满足。豆腐也是必不可少的,乡下的规矩是过年不吃白豆腐,所以炸成长的、方的、三角的金黄小块;母亲会在炸完豆腐后,用面粉炸许多甜的、咸的小点心,预备给我们和来家里拜年的孩子当零嘴。还得打糍粑,用蒸熟的糯米压成许多小个的粑粑,可以煮在汤里吃,可以煎了蘸糖吃,我们最喜欢放在火上烤,烤得鼓鼓的、焦焦的、香香的。还得准备鸡蛋,正月初一煮熟染红,家里人人要吃,来的小孩每人一个,那时不是鸡蛋了,代表"元宝"""
乡下有许多风俗,平日里也许用不着太在意,但到了过年时,却不容半点马虎。衣食住行,样样都有讲究,我们老早就被母亲耳提面命--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尽管家家都贴了写着"童言无忌"的大红纸,但我们还是小心翼翼,总怕说错话、做错事会给自家或者人家招来不幸。长大后,每逢过年就暗暗骂老祖宗,认为他们太过愚昧,用繁文褥节来束缚后代子孙。现在明白了,正是因为有那些规矩,才能衬出过年的隆重,才能让这个传统节日,世世代代根植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
一度以为过年只是老人和孩子盼望的节日,老人盼的是阖家团聚,孩子盼的是热闹喜气;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代人,过年只是多了一个劳累的假期:来来回回赶路,腿脚不得休息;吃完东家吃西家,胃肠不得安宁。可是母亲几十年如一日,每年都不厌其烦地打点着过年的行头,并且随着日子的安定,一年比一年准备得丰盛。我们一致要求她从简从略,但她往往从繁从复,并且乐此不疲。
母亲走后,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过简单安静的年了。从超市中拎回一堆成品或者半成品招待客人;大年三十,去酒店吃一顿团圆饭。原以为这样会轻松舒服,但没有了母亲那些冗长的准备,过年的欢乐也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瞬。终于理解母亲那样辛劳的价值,对于生活而言,有些过程不能省略、有些仪式必不可少、有些等待必须经历。
于是学了母亲在世的样子,潜心准备过年的衣食。为了给家人挑选合适的衣服,走得双腿发软也在所不惜。亲手采集所有的原材料,学会自己腌腊肉、腊鱼,做香肠,做各种卤菜。女儿亦步亦趋地跟在身边,脸上写满赞美;老公时不时插上一手,眼里溢着依恋。家里挂满自己的劳动成果,时时飘散着浓郁的香味,看着看着就从心底生出一份期待--期待用自己的虔诚,为家人制造一份幸福、一份安宁。
长歌当哭
01据说我是父亲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的女儿,在两个哥哥之后,父亲说:再不生个女,死了连个哭的人都没得。这话在村子里流传了很多年,长大后我听见两个乡亲吵架,一个对另一个说:你横什么横?等你死了,连个哭的人都没得。另一个老乡家只有四个儿子,闻之气短,扭头走了,从此两家结下梁子,老死不相往来。
乡村里,并不一味重男轻女,通达的人家都希望儿女双全,是谓福份。一个人福寿终了时,常常是女儿来总结他"她"的一生,当然这个总结是哭着完成的,用书面语说是"哭丧"。操办白喜时,哭得热闹那是吉利,如果一户人家有三个女儿,一齐哭起来,简直跟搭了台唱戏一样,从死者受的难到哭者受的苦,一一陈诉,一曰表哀思,一曰驱噩运,从此死者和生者得以远离苦海,幸福地行走在天堂和人间。
是以哭是女儿家的一项功课,村里办丧事,姑娘家围着哭得三溪流海的七姑八姨,学习"哭"的套路。那会哭的一开口,凄凉婉转,感人涕下,可谓一哭百应,带得哭声一片,在场的人无不掬一把辛酸泪。
02在我呱呱坠地之前,父亲肯定是指望我能一个顶仨的,至少在"哭"的噪门和技能上,能够熟练又深情地总结他辛劳的一生。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教我大口吃饭,大声说话,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讲述他的那些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日子,每每我听得眼泪叭嗒叭嗒地落在饭碗里,他才刹往话头,说:吃饭吃饭!那时刻他的神情是满足的,胃口是好的,我赶紧擦干眼泪扒起饭来。
关于哭的本领,直到奶奶去世,父亲都对我寄予厚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多少日夜的教诲,在我八岁那年正式登场时没看到一点成效。奶奶大概是冬天的子时走的,当时我被隔壁的姑从热被窝里拎出来,穿着一条花棉布睡裤,瑟瑟地躲在门背后看大人们哭进哭出,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盖在奶奶脸上的白布,摸着奶奶的脸;姑妈一手托着腮,一手甩着毛巾,象唱歌一样数着她自己的苦;还有其他的家人和族里的亲人,都在奶奶睡的门板周围哭作一团。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亡人,当时是羡慕奶奶的,她已经死了,还有那么多人围着她;而我一个活生生的伢,已经冻得栗栗颤了,却没有一个人给我添件衣服,为此,我哇哇大哭起来,哭着喊:冷!冷!!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