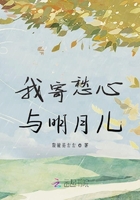凌归茹听耳边细细碎碎叽叽喳喳的谈论,头发好像被人扯住,头皮疼痒,脑袋里嗡嗡如蝉鸣。
尝试打开眼皮,发现干涩难耐的难以睁开,水分像是被催干,能感觉到眼皮在颤抖,却同样不受控制的颤抖,不受控制地打不开。
“她不会是死了吧?呀!那这样就不好了,她死了掌柜会不会怪罪?”说话的声音来自头顶,看不到,其他的感知会更加敏感,音色很纯正,很单纯,口气里有害怕,有担忧,唯一没有的就是恭敬和发自内心的担心。
“她莫名其妙地死了关你何事?她栽倒是在场所有人都看到的,咱们只是来这里看管而已。”是一道别的声音,凌归茹感受到浓浓的不善。
“对呀,雅儿,归茹姐姐可是红牌呢,她死了你担心着什么?再说她不一定会死啊。”伴随嘲讽占了一般的语调,凌归茹细嫩的头皮又是一阵刺痛,是,原来一直是她们在抓自己的头发。
没有预兆,凌归茹直接睁开眼睛,眸中不是秋水如映月,而是淡然如初雪,一是因为眼睛干涩好像没有丝毫的水分,二是人不似前。
凌归茹不适地摇晃沉重的脑子,脑仁嗡鸣,很难受。眼前不止一次地飘下黑亮的发丝,无瑕顾及,青葱玉指按揉太阳穴,面上只有黑白两色,黑的是发,白的是肤,连唇瓣也是苍白。
“这是……哪?”凌归茹神色莫名呆滞,红绸飘飘,霓裳舞舞,琉璃彩灯,红烛碧澄,身上松哒哒的,宽大的衣袖,低领的衣裳,古代的韵律,古代的风韵,她在古典的肥皂剧里的场景映入她的眼睛,虚妄,虚实,虚假,不知是否为真。
“呀,姐姐这是怎么了,否是摔坏了脑袋?”雅儿关切的语气很尖锐,大惊小怪多像是装出来的。纤白的十指牢牢地抓住凌归茹的胳膊,衣服就这样绞到一团,可以猜的到里面的衣服是有多少的褶皱。
“我?摔倒脑袋?”她是否摔倒脑袋她不记得,但她很明白地知道自己是被撞晕的。
之前是个这样的雨夜,寂寥悲凉,绵绵密密没有停歇,不停地下,不停地洒,空空荡荡心里慌张,不安。
爷爷叫姐姐和她回国,姐姐凌馨怡来送提着大小包裹的她,阴雨密密沾湿裙袂,暗色的布料仿佛天边最阴沉的云。
车灯透过细雨直射她的双眼,两个车灯,两只眼睛,直直迎上,她来不及躲避,耳畔车笛声音已经回荡到耳廓,剩下就是无尽的疼,惋惜的心,痛惜的心,她舍不得自己的姐姐,想她每次费尽心力地逗她笑,想她每次不管对错地惩罚欺负自己的人,想她每次分享各类好东西……
“我的姐姐,您不会真的不记得了吧?”雅儿又说。
“我该记得什么?”她冷眼对她,眼神空洞无光直视前方,是一盏明亮的篱灯,外面整齐包裹枯败的竹片,里面就是一盏在普通不过的红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