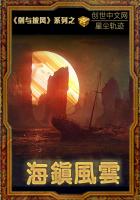在场外百姓的不断注目下,宁奕搀着那妇人缓缓地迈进了扬州府府台衙门的大门,只是刚一踏进去,一名身穿紫色官袍,帽子上还插着一对乌翅的中年男人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一见宁奕,便立即哈哈大笑起来:“敢问这位公子可是宁奕宁御史?”
“在下正是。”宁奕微微地一拱手,冷冷地道:“敢问阁下是否就是扬州府府台陈大人?”
陈学艺点了点头,一张老脸笑的无比灿烂,走上前去亲热地一把拉住宁奕的手臂,口中不住地笑道:“宁御史,本官等了你很久了啊,正好,来来来,去后堂稍作歇息一番,本官一会便去传杜冲杜将军前来府衙一起絮叨絮叨。”
“不必了。”宁奕冷冷地抽回手,顾不上陈学艺那满面的错愕,宁奕淡淡地道:“敢问陈大人,究竟可知宁奕突然到此的目的。”
“这个…”陈学艺愣了愣,附在宁奕耳边,低声道:“宁御史的意思…莫不是为了罚银的事?”
“正是。”宁奕冷冷地一笑,“宁奕斗胆在问陈大人,衙门口大门敞开,却为何许出不许进,连百姓申冤诉状也不肯受理,请问陈大人,这又是何故!”
宁奕说完以后,陈学艺忽然深深地叹了口气,愁了半晌,陈学艺那张老脸上忽然皱了起来,轻轻地道:“还请宁御史移步后堂,待本官与你详细说说缘由,如何?”
宁奕想了想,指着身边的那一对母子笑道:“可是陈大人,你看,苦主都上门来了,你说这怎么办才好?”
“待本官将事情的一切经过缘由详细说明以后,如果宁御史要说开堂,那本官便立即开堂,毫不犹豫!”陈学艺忽然直起腰来,两眼泛出一阵精光,重重地应道。
“好!”见陈学艺如此干脆,宁奕也就不打算在冷嘲热讽,重重地一点头,宁奕微微应声道:“陈大人,请。”
随着陈学艺进入内堂以后,宁奕往下首处一把椅子上坐下以后,一杯热腾腾的清茶立即端了上来,宁奕只是看了一眼那杯茶,然后便淡淡地道:“陈大人,现在可以详细说说缘由了吧。”
“唉…”陈学艺忽然重重地叹了口气,满脸的愁云涌动,无奈地道:“宁大人,你是有所不知啊…”
听见陈学艺如此之说,宁奕顿时心中一惊,脸上却没有任何表露,淡淡地道:“陈大人,怎么了,有事不妨说出来吧。”
陈学艺的脸上顿时闪过一丝苦笑:“宁大人,莫非你当本官想向他们收罚银?不管怎么说,我陈学艺在扬州为官两任,也是这扬州地界的父母官,如果我陈学艺真是那种********的士绅土匪,嘿嘿,那么这个官,不当也罢了。”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宁奕紧盯着陈学艺的眼睛冷冷地道。
“请问宁大人,知道江南应办局么?”陈学艺忽然紧盯着宁奕的眼镜淡淡的道。
“应办局?”宁奕想了想,道:“莫不就是负责采办一应用品的职能衙门么。”
陈学艺脸上顿时嘿嘿一阵冷笑:“是!也不是!”陈学艺紧咬着牙关,忽然长笑一声说道:“宁大人有所不知,这些所罚的银子,最终可没落入我的腰包里,而是如数全都送进了江南应办局里!而且是每月必送,一刻也不许耽搁,否则我陈学艺就得丢了这乌纱帽!”
“每月必送!!”宁奕顿时大吃一惊,冷不防忽地站了起来,惊疑不定地道:“陈大人贵为当朝二品大员,应办局里的采办也不过才九品芝麻官,怎么还会要陈大人丢了乌纱帽?”
“嘿嘿,人家可是太子的人,并且还手中握有花岗石采办的一应事务,惹不起,惹不起啊。”陈学艺忽然笑了起来,“这江南大半官员都是太子一党,我陈学艺夹缝中求存,又怎么能不虚以委蛇,难道还要自己乖乖的伸出脖子,让人迎着脑袋硬砍上一刀吗?”
陈学艺刚一说完,宁奕就彻底的陷入了沉默。陈学艺说的合情合理,从根本上来说,陈学艺得罪惹不起江南应奉局,只要陈学艺还想在江南做官,就不能不这么做。
人皆有私心,凭良心而论,又怎能以己之心要求别人如何去做。何况,整个江南官场都是这么做的,他陈学艺又凭什么不能跟风呢?
想到这里,宁奕的双眉紧紧地拧了起来,冲着陈学艺一抱拳沉声道:“只是陈大人,收受罚银这种事情,对于百姓只会被逼的家破人亡,还请陈大人尽早收回。”
“我陈学艺也知道啊。”陈学艺重重地叹了口气,良久以后,陈学艺脸上浮现出一股深深的忧愁,重重地道:“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若是不这样做,每个月供给应奉局的银子可就不够了,宁大人足智多谋,应当能想到,这些银子,最终又究竟去了哪里。”
陈学艺苦苦地一笑,落在宁奕心里却如同针扎了一般的刺痛,忍不住喃喃地道:“这些银子…最终流向了…京城!”
“那么,宁大人,这种情况下,你可叫本官如何是好?”陈学艺捋了捋胡须,喟然叹道。
“我想请问陈大人,江南各地的官府,为何要每月按时向应奉局缴纳银子?可有依据?”宁奕沉思了许久,缓缓地道。
“这个…”陈学艺顿时愣在当场,然后皱起眉头苦笑起来:“这种事还能有什么依据?天知地知的事情,都知道这部分银子最终落入了谁的口袋里,可是,谁敢管?这可是牵扯进皇家的大事啊!”
“我敢!”宁奕冷冷地站了起来,缓缓地道:“既然无凭无据,这种活动就必须要立即禁止,陈大人,下官请求陈大人立即废除罚银的行为!还扬州府百姓一个天日!”
“宁大人!!你…你不要命了么!!”陈学艺急忙站了起来,只见陈学艺满脸忧愁地道:“这可是牵动皇家的大事,宁大人,你还究竟要不要命了。”
“我当然要命,并且,我宁奕还没有活够。”宁奕缓缓地道,“只是眼见江南百姓已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宁奕可不能不管!还请陈大人下令在整个州府立即废止罚银等一切正常纳粮以外的一切行为,否则,我宁奕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宁奕铁骨铮铮地说出这句话来,惊得陈学艺顿时呆住了半晌,好半天,陈学艺才终于缓缓地吐出一口气,说道:“若是追究下来,谁人承担。”
“我承担。”宁奕冷冷地道,一弓身向陈学艺拜服道:“还请陈大人立即废止,现在已是片刻容缓不得了。”
“好…好…”陈学艺仿佛一口大气没有接上来似得,不住地重重喘了粗气,脸色涨的通红,顿了半晌,从门外唤进来一门押差,淡淡地道:“传我令,从即日起严禁扬州府下各地额外收取正常纳粮以外的一切罚银行为,若是有违此令,立即撤职查办!严惩不贷!”
“是!”那押差应了一声,急忙转身跑了出去。
“这下你满意了吧,宁御史!”陈学艺重重地坐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重重地问道。
见陈学艺终于让了一步,宁奕微微一笑,一拱手又继续道:“另外,还劳烦陈大人移驾大堂,老百姓们,似乎有很多冤情没有得到申诉啊。”
“好…好!都依你,都依你宁大人的!”陈学艺复又重重地站了起来,眼中的怒气都快要喷出火来似得,一边走一边向着门外巨喝了一声:“来人,来人!击鼓,开堂,本官要开堂受状!”
“唉…大人要开堂审案了?”一名衙役望着一身紫色官袍的陈学艺,疑惑地挠了挠脑袋,然后捣了捣身边一位同样疑惑着的衙差,皱起眉头不禁问道:“你刚才听见了么,大人要开堂审案?是真的么?”
“我也听见了…莫不是装装样子的吧?咱们府台衙门已经有一年多没接过状子了,嗨,大人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咱们大人日理万机,哪有这闲工夫啊。”那押差嘿嘿一笑,淡定地说道。
那两名衙役对视了一眼,然后纷纷嘿嘿直笑起来。
陈学艺冲着门外满脸怒气地吼了半天后,发现竟然无一个人理睬,陈学艺那张通红的老脸顿时变成了一片酱紫色,忍不住那滔天般的怒气冲了出去,一抬手一人给了一个巴掌,怒道:“没听见本老爷说要开堂吗!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击鼓开堂!!”
那两个衙役被陈学艺一人一个巴掌打的眼冒金星,懵了半晌,这才缓过神来,看着自家大人满脸的怒气,那两名押差这才反应过来,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
陈学艺的胸膛不停地上下起伏着,显然胸中的那一股怒气还没有被消除,宁奕坐在木椅上微微地喝着茶,眼角微微地抬起观察着处于巨怒之中的陈学艺。只见陈学艺大口大口地喘了半晌,然后转过脸来缓缓地道:“宁大人,本官现在要开堂审案,你随不随本官一起来?”
“既然如此,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宁奕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茶盏,大步随着陈学艺走出了内堂。
扬州府台衙门口处,一声惊天的鼓声忽然响起,紧接着双门大开,两排整齐地衙役整齐地排列在了大堂两侧,一名健壮的衙役正操着手中的鼓棒猛烈地敲击着那面早已沉寂了一年,许久也未曾听见过了的…登闻鼓!
登闻鼓一响,如同青天现世,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有冤的申冤,有仇的诉仇,天地间最浩然的一股正气!登闻鼓一响,就如同给扬州城所有的老百姓敲响了一个信号:府台衙门,开堂受状了!
相传早在尧舜之时,就有“敢谏之鼓”了。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此后此例一直受袭,直到唐朝时,即开始有明文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则加罪一等!
在中国的历史上,登闻鼓的使用经久不息为历代所使用,但凡登闻鼓一响,水情水浊,立时毕现!
起初,扬州府台陈学艺往大堂上一座,头顶的一副牌匾上刻着“公正廉明”四个大字,宁奕坐下首,扬州城的老百姓们一个个隔着衙门口远远地看着里面的动静,只见陈府台坐在椅子上满脸的怒气,站堂的两排衙役个个神情紧肃,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看到扬州府衙门里这种紧张的气氛,一时之间竟然无人敢击鼓喊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