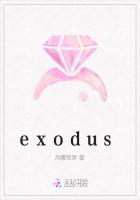开朗温雅的伊丽莎白走了,寒冷阴郁的10月逼近了,我们初尝伦敦大雾的滋味,天天喝便宜汤汁以果腹,这或许早已引起贫血,就连大英博物馆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好些日子,我们甚至没有勇气跨出大门,只是裹着毛毯坐在室内,在厚纸板做成的临时棋盘上下国际象棋。
回想往日轻快欢愉的心情,与这段时间我们极度萎靡不振的样子,都同样让我感到诧异。事实上,有好多个早上我们完全没有勇气起床,整天躺在床上。
终于,伊丽莎白捎来了一封内含汇款的信。她已经抵达纽约,住在五号街的白金汉旅馆,创办了她的学校,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放心多了。工作室租约已经到期,于是我们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小屋子,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广场花园。
在一个暖暖的秋日之晚,雷蒙同我在花园里跳着舞,这时一个戴着黑帽子、美丽动人的女子走过来,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是来自人间,”我回答她说,“而是来自天上。”
“嗯,”她说,“无论是来自人间还是天上,你们都非常甜美可爱,要不要到我家去玩呢?”
我们跟她到她位于肯辛顿广场的可爱的家,里头挂着一些伯恩·琼斯、罗塞蒂[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及诗人,协助创立“前拉斐尔派兄弟会”,为罗塞蒂家族中最负盛名者。]、莫里斯[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美术设计家、手工艺人和社会主义先驱者,被视为19世纪伟人之一。]为她画的、颇能烘托出她个性的不凡画作。
她就是坎贝尔夫人[坎贝尔夫人(1865—1940),英国女演员。她因与萧伯纳有信件往来而驰名。]。她坐到钢琴前为我们弹奏,唱了几首英国老歌,又朗诵了几首诗给我们听,然后看着我跳舞。她真的是美丽非凡,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一双深邃的黑眼睛,娇嫩的肤色和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我们迷上了她,这次见面无疑将我们从忧郁与失意中拯救出来,命运也从此开始转折。由于坎贝尔夫人十分喜爱我的舞蹈,所以她写了一封信,将我引荐给乔治·温德姆太太。她告诉我们,她少女时代第一次在社交界露面,就是在温德姆太太家里朗诵朱丽叶的台词。温德姆太太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让我生平第一次在暖烘烘的火炉前享受了下午茶。
暖烘烘的火炉、面包、奶油三明治、浓浓的茶,加上屋外的浓雾,让伦敦愈发迷人,对我具有一股无法形容的魅力,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爱上这一切了。屋子里有一种神奇的气息,让人感到舒适、安闲、宁静、悠然,我在这里感到非常自在,如鱼得水;那精致的藏书室也让我深深着迷。
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些优秀英国仆人的良好教养。他们来去之间总是充满着自信和保持高贵的风度,一点也不像美国的仆人那样自卑或是去争取社会地位,他们将自己能为“最高尚的家庭”服务引以为傲。虽然他们的父亲以前是仆役,他们的孩子未来也会成为仆役,但这种工作态度让他们生活得安定自得。
某天晚上,温德姆太太安排我在她的客厅里献舞,几乎所有伦敦的文人雅士都出席了。我在那里遇见了深深影响我一生的一个男人。当时他约50岁,是我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高高的前额下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希腊式的鼻梁和细致的嘴唇,身材修长,微微驼背,灰色的头发中分,发丝垂向两旁耳根,脸上的表情特别迷人。他就是查理·哈莱——一位著名钢琴家之子[著名的钢琴家指的是查理·哈莱(1819—1895),英国指挥家与钢琴家。]。奇怪得很,当时我所遇到的准备对我展开追求的年轻男子中,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好感,事实上我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可是我却一下子就被这个50岁的男子深深地吸引了。
他曾是玛丽·安德森[玛丽·安德森(1859—1940),美国女演员。]年轻时的挚友,在我受邀到他家喝茶时,他还展示了自己精心收藏的、玛丽在《科里兰纳斯》里扮演维吉利亚时所穿的束腰及膝长衣。这次探访大大加深了我们的友情,每天下午我都想方设法到他家探访。他告诉我许多事情,有关于他过去的好友伯恩·琼斯的,还有关于罗塞蒂、莫里斯以及所有“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科里兰纳斯》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出悲剧。剧中主人公科里兰纳斯是带有神话色彩的罗马英雄人物,维吉利亚是他的妻子。“前拉斐尔派”是英国一群青年画家于1848年组成的一个艺术团体,其宗旨在于反对他们认为缺乏想象力而又做作的皇家美术学院的历史题材绘画,竭力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一种新的道德严肃性和真诚性。],还有惠斯勒与丁尼生[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同这些人都很熟。我在他的公寓里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这位随和的艺术家是引领我探知老一辈们的艺术的领路人。
当时,哈莱是展出所有当代画家作品的新美术廊的馆长。那是一个有中庭与喷泉的迷人小型美术馆,哈莱想让我到那里表演。他介绍我给他的朋友们:画家里奇蒙、历史学家安德鲁·兰和作曲家帕里[帕里(1848—1918),英国作曲家。]。三人都同意就舞蹈发表演说——里奇蒙先生的主题是“舞蹈与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先生的主题是“舞蹈与希腊神话的关系”,帕里先生则讲“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我在那绕着长满花草植物及一行行棕榈树的中庭喷泉跳舞。这场盛会非常成功,报纸大肆报道,哈莱也为我的成功高兴不已,伦敦的名流争相邀我喝茶或用餐,命运之神终于短暂眷顾我们一下了。
一天下午,罗纳德太太家举行的宴会上挤满了人,有人引荐我给威尔士王子,之后又引荐我给爱德华国王。他称赞我美如庚斯博罗[庚斯博罗(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其所绘的贵族仕女肖像画优雅迷人。]的画中美女,这个称号提高了我在伦敦社交界的声誉。
我们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因此在沃维克广场租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我在国家美术馆看到的意大利艺术仍启发我、帮助我产生新灵感,尽管我当时仍深受伯恩·琼斯和罗塞蒂的影响。
这时,一位声音柔和、眼神梦幻、刚从牛津毕业的年轻诗人走入我的生命中。他是斯图尔特贵族的后裔,名叫道格拉斯·安斯利。每天黄昏时分,他会带着几本诗集来找我,读斯温伯恩、济慈[济慈(1795—1821),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勃朗宁[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作品由表达个人诗情转而注重探讨在日趋多元化社会中社会与宗教的价值。]、罗塞蒂和王尔德[王尔德(1854—1900),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的诗给我听。他喜欢大声朗读诗篇,我也很爱聆听。我可怜的母亲虽然懂得并爱这些诗篇,但是这种牛津风格的诗歌朗诵却让她大惑不解,因而即便她认为自己必须在这些场合中同我做伴,却总会在一两个小时后,尤其是念到威廉·莫里斯的诗时就坠入梦乡,这时这个年轻诗人就会俯下身来轻吻我的脸颊。
这份友谊让我非常快乐,我只想结交安斯利和哈莱这两位朋友。平庸的小伙子让我极端厌恶,虽然当时许多人目睹过我在客厅中的舞蹈后,很乐于访问我,带我出游,但是我高傲的态度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
查理·哈莱和他迷人的小妹一起住在卡多根大街上的一间不太大的老房子里。哈莱小姐对我很亲切,她常邀我和她哥哥三个人一起用餐,后来也经过他们两人认识了欧文[欧文(1838—1905),19世纪末伦敦舞台上极著名的演员和剧院经理。戏剧上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爵士封号的演员。他与女演员特里的演出珠联璧合,成为英国戏剧史上的美谈。]和特里[特里(1847—1928),英国女演员,欧文的搭档,擅演莎士比亚剧目。]。我是在《钟》这出剧里第一次欣赏到欧文的演出。他的艺术表演让我既兴奋又着迷,使我陶醉得好几个星期不能安睡。至于特里,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是我此生景仰的对象。只有亲眼看过欧文的人,才能领会到他表演时所产生的动人美感与震撼壮阔,他所散发的聪慧与戏剧魔力难以用言语表达;他的才华出众,就连缺陷都令人着迷;但丁式的才华与神韵贯穿在他的演出中。
那年夏季的某一天,哈莱带我去见伟大的画家瓦茨,我在他的花园里为他献舞,在他的屋子里挂着多幅以特里为主角的画作。我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时,他诉说着许多关于他的艺术与人生的动人故事。
特里当时正值中年,已不是瓦茨倾心并想象的那种修长、苗条的青涩少女,而已成长为身材玲珑有致、举止落落大方的丰腴女性,与今天流行的理想身材相去甚远!如果当今的观众能见到成熟妩媚的特里的话,肯定各种教她如何节食减重的意见会令她不胜其烦,倘若她真的效法现在的女演员们花时间让自己更显年轻苗条,我敢说一定会让她的演出成就遭到损害。虽然她并不轻盈和苗条,但确实是一个充满女人味的美丽典范。
就这样,我接触到当时最有才气的文艺界人士。冬日沉闷无比,沙龙比暖季时举办得少多了,于是有段时间我加入了本森剧团,只是除了演出《仲夏夜之梦》的精灵外,就再无突破。剧场经理似乎无法参透我的艺术,也看不出我的看法将给他们带来好处。此时,莱恩哈特[莱恩哈特(1873—1943),奥地利出生的著名导演。1894年应布拉姆之邀加入柏林德意志剧团。1902年首次执导王尔德的《莎乐美》,1903年与布拉姆分道扬镳,接管新剧院,执导过42出戏,其中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最能体现其早期天才。1910年演出《俄狄浦斯王》等许多古希腊戏剧,使许多伟大作品获得新生。1910年执导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的首演,为歌剧引进了现代观点。]、吉米尔,还有“剧场前卫派”之流,争相模仿我的风格但效果拙劣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因此这些经理的态度更令人百思不解。
有一天我被引荐给特尔夫人,在排练时我到化妆室找她,感到她非常热情。通过她的引荐,我穿上舞衣,到台上为比尔爵士[比尔(1853—1917),英国一位具有喜剧天才的浪漫主义演员和性格演员。1904年创办“皇家戏剧艺术学院”。]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只是他并没有注意看,反而一直望着远方。我后来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趁他向我敬酒,赞誉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时,告诉了他这件往事。
“什么?”他惊呼着,“我曾看过你的舞蹈、你的美貌、你的青春,却没懂得欣赏?哎呀!我多傻啊!”“现在太迟了,”他接着说,“太迟了!”
“不会太迟的。”我回答说。从那时起他就对我推崇备至,这些我下面还要细说。
事实上,当时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唤醒了安德鲁·兰、瓦茨、阿诺德爵士[阿诺德爵士(1832—1904),英国诗人和新闻记者。]、杜布森[杜布森(1840—1921),英国诗人、评论家及传记作家。]、哈莱,唤醒了我在伦敦见过的所有诗人与画家心中的狂热与赞赏时,这些剧场经理却始终无动于衷,仿佛我的艺术理念过于崇高纯净,因此无法融合于他们所理解的那种世俗粗劣的剧场艺术。
我整天都在工作室里忙着,晚间不是诗人安斯利来读诗给我听,就是画家哈莱带我出去,或是看我跳舞。他们从不会一起来,因为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诗人说他搞不懂我怎么会整天同一个老家伙在一起;画家则说他无法理解这么聪慧的女孩怎么会看上一个自大狂。事实上,他们两位的友谊都带给我莫大的快乐,我真的无法分辨自己比较喜爱哪一个。但星期天倒是都为哈莱保留,我们会在他家享用斯特拉斯堡的鹅肝酱、雪利酒,还有他自己煮的咖啡。
有一天,他总算允许我穿上那件玛丽·安德森的纪念舞衣,摆好姿势,为我画了多张素描。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