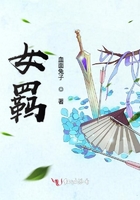羊叔一手拿着块儿馍,一手抱着娃娃,娃娃像半个袋子一样挂在怀里昏昏欲睡,一扭一扭走了进来,说:“爷——!我偓还恶得给整了个大(duò)活!”尖声细气的!韩晓扑哧一声乐了!他倒不是笑羊叔的动作和神情,这多少年从小到大都习惯了,他是笑羊叔的说辞。
韩晓妈没有过多说话,显得很平淡,说:“你可当呢!”又问:“你(们)吃了么?”
“早上烙了一点儿馍!……她娘的偓肶,我偓弄得这馍都跟死人脚(juě)后跟一样!大人咬(niǎo)都咬不下(hā),还甭说娃娃!”羊叔一边嚼着那块儿发青烧焦的馍,一边骂他媳妇层层!随即靠着墙根儿要蹲,韩晓赶紧给拿了块儿板凳!
韩晓也就纳闷,这层层姨都多少年了,咋还不能把馍做到向上?这即就是每次总结也早该总结出来了呀!多少面放多少水,再放多少碱,用多大的火,这一次两次不好说,这四次五次总该可以吧!但层层姨每次做的馍不是酸得硬得咬不动,就是“金黄蛋”苦得吃不成,火色还不均匀!结婚三十年了一直如此,做的饭也不咋样!馍和饭就常喂了狗吃,狗都不好好吃!村里人就为此常笑,羊叔也常骂,一家人也都常骂——弄得层层姨就像旧社会的“苦媳妇”!
“那娃呢?”韩晓妈又问。
“给冲了一点儿奶粉。”羊叔说毕,继续把娃蜷缩在怀里,颠拍了两下,像金豆儿一般。
“那么大的娃咧,都快两岁咧,吃奶粉能着住?!偓贵得跟啥一样,能吃起(qiě)?!”韩晓妈说。
“他爸把这蛋儿货看得重么!”羊叔嘿嘿笑着,接着刚才的话题凝声说:“我刚才在门儿听说,拿咧一万多都不够,要输血呀、要动手术呀……现在抗争跟他爸满堡子跑着寻钱呢!我英健才刚拿咧两万块钱走咧!……这可能还得寻人说话呢!”一边说一边咂舌,一边挤眼睛!
“你不管咋样,你肯定先得给哖人看病么!”韩晓妈说,“……我看哖还是有钱呢!”
羊叔嘎嘎笑着,大张着嘴,说:“还看不出,我偓是个咥冷活的!……这回可得花些钱!”
英健和媳妇按道理是管羊叔叫五大的,他爷和羊叔他爸是亲弟兄们,只是两家也为地畔起过纠纷,从此不再说话!起因还是因为牛伯爱占人家地,又仗着人多势众,把么理的事也要说搅成有理的,就还要给自己家造势!酸酸给他的两男一女教见了羊叔叫“二阴子”“五婆娘”,又管层层姨叫“瓜层层”;她自己见了羊叔则说“不下籽儿的”;牛伯骂他三姨即羊叔他妈骂得更绝,说他三姨要不是头上安个泡泡(发髻)人准会把她当成男的!……羊叔一家被骂得张不开嘴!把羊叔他妈三婆骂得坐不住咧,如坐针毡,就冲着前来叫嚣的酸酸说:你妈引咧两个野的!……这一下可搔了猴子肶,酸酸她妈拄着拐杖前来,慢悠悠说:三姨,三姨,把你(家)的亲的领出来让我看一下,看一下你是咋日下的亲的?!……两家为此还打了仗,酸酸将她五姨的头发拔了下来,脸抠得稀烂!她五姨层层哪能经住那个,险些被胖大的酸酸要了命!
喎人恶人占了上风,羊叔一家还被骂得不像样子,为此羊叔和那家一直不说话,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韩晓这次忍不住了,问:“羊叔,你这一支(zǐ)儿咋为啥起名字全是牛啊骡啊羊啊的?”母亲看了一眼,不等说完,说:“老早人么文化个啥!”羊叔说:“把他家的,我也就常说,你看我(们)这起的这名字:老大是马,老二是牛,老三是骡子……驴、羊、猪、狗,尽起咧些‘牲口’名字!”羊叔扳着指头嘎嘎大笑,娃娃险些从怀里溜了下去,韩晓扑哧一乐!母亲也笑着说:“过去人么文化,尽都图好记,一点儿也么考虑看娃将来长大咋弄呢!我记得东来村还有个老汉都八十多咧,……人还把那叫‘勾蛋’……”说到这里,话未说完,韩晓妈已不能自已,再次笑了,三人都笑了!“勾蛋”即“牛蛋”,男娃生殖器的意思!
羊叔的孙女娃娃从迷糊中醒来,哼哼唧唧地叫着闹着,手胡乱抓扒!
韩晓妈提议看得是么吃饱,要么在自家锅里给舀一点儿米汤!“要不在你婆屋里给我娃舀一点儿米汤哦?”羊叔问着,娃并没有吱呜,只是睁着眼珠胡乱看着,显得惊惶失措——看着院子三人,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再往她爷脸上瞅!
羊叔站起身说那让他回去取个碗去,听韩晓妈说“你就在我案上随便拿个碗,碎娃能吃多少!”就停了下来,就在案板上取了个小碗,在锅里舀了一勺端了出来。然后给娃喂,娃却不吃,反过身在他爷胸口胡扑乱抓,把饭碗能撞翻!
见状,韩晓妈吼了起来:“你干啥呢?!”有意吓唬!
那娃回头看了一眼,转身又继续起来,不闻不顾,将手索性还从脖颈伸在他爷的胸膛里面,摸索起他爷的****。他爷将手拨不下去,只得嘿嘿笑着!
“这跟她妈一样,一点儿都不听话!你回去给嘴上抹点儿辣子!”韩晓妈气得大声说,看那娃的反应,不罢不休,又急忙转身回从厨房里抄来一筷头辣子示意要往嘴上抹!那娃一拨头,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脚手带踢打,更加不好好安稳起来!
羊叔只得站了起来,感慨道:“这可不安宁咧,得人把她又拤(qiā,抱)上转!饭可又给你糟蹋咧!”
“她在在你层层跟前还是那样子,你叫你层层给涅涅(乳房)上抹一点儿辣子!——不了这都这么大咧,快两岁咧,还一直要吃涅涅!——咋弄呢?!赶紧要给吃饭呢!猫不吃糨子——惯下(hě)的病!你看我晓晓一岁多咧哪儿还吃奶!”韩晓妈面色凝重地说。那娃确实平时把她婆的衣襟撕开,将手伸进去胡扒胡抓,她婆也说不下。
韩晓不愿母亲提说起吃奶的事儿,便说:“你管人家娃那干啥呀!”
羊叔则说:“你看你婆骂呢,快不敢了!……”那娃还在踢打,她爷就抱着,俩人往出走,娃手还在她爷脸上不停抓着!……
看着背影,韩晓叹了口气。
接下来村里的事儿可就热闹了,人们都在叽叽喳喳议论那件事,说得都跟眼见一样。
有人就说酸酸将争娃媳妇打了之后,争娃媳妇大声叫唤着打电话说:你媳妇叫人打咧!赶紧回来!争娃就连忙赶了回来!本打算找酸酸理论,没想到酸酸已经做了准备,可能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在柜盖上将杀西瓜刀放着,准备“自卫”!两人言语当场不和,争娃用手在酸酸胸膛上打了一下,酸酸顺手拿起西瓜刀就给了争娃一下!说争娃那会儿都瓜咧,也不知道该干啥,只看着血流着,就站在街道上!……
还有人说争娃现在在医院不好好配合治疗,说他不看了,最好残废了,有人养他一辈子!……英健都吓得勾子么脉(měi)咧,到处凑钱、寻人说话,还好他姨表哥是书记,又给帮忙又给说话又给出主意!找的说话的人就劝,说你不看了,你看你一辈子干啥不方便,也看起来不好呀!争娃就说那有人服侍我呢么,有人给我干地里活呢么,有人给我养媳妇养娃呢么,有人养我爸呢么……我害怕个啥?!争娃的日子早都过不下去咧,终于寻了个“抬埋”他的!吓得英健满村跑,见咧街道上的人都躲着,不敢抬头看,关键是他闯下的丢人事,到处找人托人说话;酸酸现在是不理不问,依然大模大样在加油站干着,争娃媳妇倒是在那儿干不下了,不在那儿干了——从加油站那边来说,还是酸酸胜了!
酸酸理直气壮是因为觉得那个家亏欠了她许多,早都对那段婚姻不满意,要不是她娘家妈……她娘家妈把她从外地带来自己嫁给牛伯又把她嫁给了人家儿子英健,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种耻辱,尤其是这家还光瓜爱种地,影响得娃娃都是这样子,这还不说,英健还是个不安分、好色的货!……
现在听说争娃媳妇在医院照看争娃着,人家到时候还要收取误工费、服侍费,营养费这些就自不必说了。英健已经给说话的人交了底,哪怕看好后再给些钱,要让把这事彻底解决了,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不能再来找他;说话的人又联合争娃他村主任侄子还有英健他姨表哥书记齐齐一块儿给争娃做思想工作,让赶紧动手术!……听说血管和筋脉已经错位了!
英健一家人倒是暂时尾巴翘不起来了!大门整天关着,酸酸呆在加油站很少回来,井房那边儿也有歇息的地方;儿子女子也很少在这边呆,女子出去在她姑家躲着,小子在他婆那边吃饭;英健忙着找人平事息事也很少在家;倒是牛伯时常回来着,还要回来喂狗,人家家里龛了三只狗,就常从加油站带回来饭菜和骨头。
英健在村里得罪、亏的人不少,不少人就都看笑话着,等着看笑话,争娃能是个“吃菜”的?!
争娃他妈死得早,不知是什么妇科病还是子宫癌,反正就是死了。
那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冬天冷得出奇,尤其是那个冬天。厨房冻得人呆不住,水刚一落到案板上,就紧拿慢拿切菜刀在案板上刮,就已经结成冰溜子;冻得人手拿不住切菜刀;水瓮上缠裹了厚厚一层草帘子,可还是冻成实实子;拿切菜刀、擀杖好不容易砸开几块儿冰放在锅里,可半天烧不化烧不开;锅底下的火焰就像得了“气死病”一样,“奄奄一息”,看得人木乱……
那天夜里,不知是面包车,还是救护车回来了,反正就是车回来了,车里的被子里裹着争娃他妈……第二天早上听母亲叫穿衣起来韩晓才听说争娃他妈死了!外面下着很厚的雪,树上,房檐上,地上,墙上,远处的房上……全都是很厚的雪,一片白!光树枝上的雪似乎都能有一匝厚!……也不知是夜里埋的还是天明埋的,这些韩晓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丧事应该过得很简单,尤其是三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人吃饭就走了。
争娃他妈去世那阵儿他应该是十三四五岁,和韩晓哥韩军是一般大年纪,很叛逆。他妈一死,他就成了“天不收地不管”,他爸他哥是说不下的,动不动还要骂他爸几句。那时他倒是和韩军是发小,玩得来,常常就一起去干些莫名其妙的“勾当”:偷西瓜、偷玉米、钓鱼……偷来西瓜在没人的地方偷着砸着吃;将偷来的嫩玉米在城后边儿拾了干柴干草树股树叶笼了火放在火堆里烧着吃,韩晓就常被指使放哨拾柴草,让吃那几个烧焦的玉米粒儿,还被一边训斥着不要声张吵吵回去给谁说;在外村塘库边用烧红的缝衣针弯成的钩去钓鱼,鱼没钓上来,就去逮,险些将韩晓掉进去淹死了;还会去偷看考察谁家地里都种着绦黍(高粱),挨个儿去品尝看秆是不是甜的,如是,就裁成节儿偷了回来慢慢吃……当然,也会做一些“正当”事情,推着自做的小车和韩军去捡柴禾,或者等雨后挎着篮儿在湿草地上去捡拾地软软,就常带着韩晓……韩晓就像个跟屁虫跟在后面!
韩晓家出了事儿,韩军接了班,同龄的伙伴儿都相继有了事做,年龄也老大不小了,争娃就开始在社会上荡漂:早些年在城里干活,不知干什么;后来贩起了假钞,蹲了一段时间监狱;前几年又在公众舞厅值班儿看车;现在又不知干什么!好在他还给他谈了个媳妇,有了个娃娃,这倒是不错,总比村里的周敢强!
周敢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单亲娃,但最后把他弄了个“光杆杆”,成了个二流子!周敢他爸夜里浇地去了,回来时过公路被车撞了,死机也是开车跑了,最后他妈、他妹还有他三个人过活;结果周敢好吃懒做,还给他妈耍脾气,大冬天把一盆尿从他妈头顶浇了下去;他妈一气之下带着他妹改嫁了,就留下他一个人胡游荡着,没人说,没人管,这才“好”了!先把家里的旧房及庄基卖给村里人,再后来把地也“卖”给了村里人种着,他自己就在外面胡混着,回家来等于连个落脚的“窝”都没有,都三十左右的人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还不知道活着么?!这就是村里“二毬”的典型,连名字上都被人冠以“瓜”字,人称“瓜周敢”,碎娃都这么叫着!
因此上相较一些人争娃还是不错的!争娃媳妇嫁给了争娃是一意相从,于娘家父母意见不顾,从这一点上来说争娃还是很有“本事”的,只可惜让她后悔的日子还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