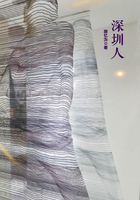我有些倦了。我险些又要睡过去了。我努力驱赶着睡意。我要等待着辉,等待着他买的豆浆。如果我睡去了,他是一定不会吵醒我的。那么那豆浆,他飞奔下去买回来的,就凉了。
然而,我还是睡去了。我竟然没有等到他回来。
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一名年轻的护士,神情怪异地站在我床前。
她说:“那位民警同志,是你哥哥吧?他生病了,不能来看望你了。”
我想继续问下去,她却转身飞快地走了。
之后的一个礼拜,所有的护士都对我讲同样的事情。她们的目光闪烁着,她们不等我发问便慌忙地溜掉。
我有些急不可待了。我必须知道,辉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开始绝食。洪水般的恐惧,日益强烈地向我涌来。
终于,一位年轻的护士,手里捧着饭盒,站在我面前流下泪来。
她说:“你哥他……被车撞了,就在楼下,给你买豆浆的时候。当时就没救了。”
我哥哥。
辉。
我的大脑似乎突然间麻木了。
我看到那豆浆,泼洒到马路上,乳白色的液体,向四面八方流淌着。这张画面,占据了我大脑的全部神经。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它知觉了。
我其实丝毫也不难过。我麻木得不知道什么是难过了。
上苍终究还是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其实,这故事的结局,不是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吗?现在,只不过换了一个形式而已。
我翻开那本日记。我狠命把刚写的那一页,连同最后空白的几页,统统撕掉了。
撕得粉碎。
我没有要求去见一见辉的遗体。
因为我并非他的亲生弟弟。
更何况,梅一定会在那里,她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第二天清晨,天色微亮,我顺利地悄悄离开医院,我头上缠绕的纱布还没有完全拆掉。我离开的时候,整座城市还沉浸在睡梦里。没人注意到我。
除了那本日记,我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我的故事真的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不需要治疗,也不需要康复。我不需要任何其它的东西了。
沿着漫长的长安街我缓步前行。高大的华灯依然明亮。
我走了很久很久。我想我仍然是很虚弱的,以至于走不了两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地呼吸。天色大亮了,这座城市又沸腾起来。有些近似疯狂般的。
已经疯狂了好几年了。我就在这座疯狂的城市里成长,亲眼目睹它夺走我的家,我的父母,如今,又夺走了辉。
不,它并没有从我手中夺走辉。辉原本不是我的。他从来不曾是我的。
然而突然间,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上天终于把他赏赐给我了呢?只不过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方式。
当然要使用一个特殊的方式了。这世界早已没有属于我的位置,又何以存放任何属于我的东西呢?假如上天果然要给我谁,当然要先把他从这世界上带走了。
我确信我是拥有他了。我加快了脚步。
一拨一拨的游行队伍,举着标语,从我身边经过。幸而没有什么人留意我。这的的确确是我所希望的。我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颤抖着双腿,我艰难地爬上辉家的楼梯。我是熟悉这里的。每一级台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楼梯的扶手正蒙着一层灰。正因为它脏,人们才更加故意地躲避它,所以一定很久都没人扶过了。
然而我却紧紧握着它。没有它,我爬不上这突然变得陡峭的楼梯。
辉家住在二层。家门紧锁着。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扇门!而门里又曾经是多么亲切的一个世界!
我在门前徘徊。我原本希望站在那阳台上,再看一眼古观象台。然而,我本以为那离开的人是我,所以早把辉给我的钥匙还给他,再也无法走进那熟悉的房间了。
我于是继续往上爬。我要到顶楼去,那里也可以看到熟悉的景色。
我经过三楼。和辉家完全相同的方位,这家人的大门敞开着。一对年轻夫妇,正兴高采烈地打扫新居。
年轻的妻子腹部鼓胀着,看上去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了。她呼喊着:快!他又踢我了!
那年轻的丈夫忙停下手里的活计,把耳朵贴在妻子肚子上,幸福地微笑。
他们的故事,正欢乐地进行着。那腹中的婴儿,想必也为他即将开始的生活而兴奋不已,迫不及待。
我突然想起很小时外婆曾讲过的故事:她说从前有一对夫妇,妻子突然死去了,剩下丈夫悲痛欲绝。那妻子的灵魂终究放心不下丈夫,所以迟迟不肯离去。正巧此地有个孕妇临盆,那灵魂便恳求阎罗,让她转世成为那即将诞生的婴儿,好一生一世照顾前世的夫君。阎罗被他的真情感动,果然就应允了他。那婴儿长大以后,果然一生未娶,只一心一意照顾那孤独的老人,陪伴他走完一生。
外婆曾用这个故事阻止怀有身孕的女人去参加别人的丧事。
外婆的故事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我再看一眼那孕妇,心里突然微微一动。她所怀着的莫非是辉?难道辉始终是对我放心不下么?
但果然是他又怎样呢?我不是早就打算要偷偷跑掉吗?我和他不是永远也不会有结果吗?难道我甘心像那传说中一样,耽误他一辈子吗?
不!我不能!
只要他记得我,而他知道我也想念着他,那就足够了。
我低头看一眼手中的日记。我和他的每一分钟都记录在这里面了。如果那孩子果然是辉的话,就让我把这本日记留给他做个纪念吧!
那户人家的大门毫不吝啬地敞开着。很多杂物堆积在门前。
我随手把那本日记仍到堆杂物里去了。那微微褶皱的封皮,竟然也能反射出些许阳光来;封皮上那手举《毛主席语录》的少年,脸上正绽放着夸张的笑容。
我继续往楼上爬去,直到顶楼,再也没有见到过其他人。
我终于站在楼顶上了。
这里风很大,毕竟已是秋天。
这里的视野异常开阔,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山。
我却只想看一眼那古观象台。也许,我还可以看到一列火车,正徐徐从那下面驶过。
第一次来到这宽阔的顶楼上,我有些迷失方向了。
我花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又看到那古观象台。
我向着它靠近,再靠近。我站在顶楼的边缘了。
我未曾料到我会如此地靠近边缘。我一向是非常怕高的。
然而此刻,我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站在这里,我仿佛终于拥有了彻底的自由,走或者飞,生或者死,任我选择。
我试着伸开双臂,仰起头努力呼吸。我突然发现,北京的天空原来如此的湛蓝。
我终于要自由了。
我轻轻迈开腿。
我开始飞翔了。风在我耳边呼啸。
我飞过五楼的阳台,屋里,一位老妇人,正坐在阳光下,专心地缝补着什么。一双眼睛,被老花镜拉城很长很长两条缝。
我飞过四楼的阳台,一位父亲,正在教训他的儿子,那孩子满脸的委屈,泪水马上就要落下了。
我飞过三楼的阳台,又是那对夫妻,他们争论着,丈夫说,他姓夏,叫作夏天吧!而妻子却说,但要等到冬天,他才会出生,不如叫夏冬吧……
冬天,夏天。我也有些拿捏不准了。我想告诉他们,不如叫他辉吧。然而,谁又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辉呢?
这瞬间思考,使我错过了辉家的阳台。但我丝毫也不觉得遗憾。或许,我马上就能见到辉了。除非……除非那婴儿果然是辉?我想我实在是太迷信了。
我想再看一眼远处那古观象台,它转瞬即逝。然而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我却见到了,有一列长长的绿色的列车,正从那下面徐徐开过。
我的飞翔虽然短暂,但我终于飞翔了。在那一刻,我享受了彻底的自由。
天的确是大亮了,阳光很耀眼很耀眼,把一切都变作无边的白色。
我的世界里一片纯白。
“我终于写完了。”
我从阿文手中接过茶杯,吮一口,眼睛却仍旧盯着电脑的屏幕。那茶叶的芬芳迅速充满了我的鼻腔。
他从背后环抱着我,把下巴架在我的肩膀上:
“就这样吗?这个结尾,到底算是喜剧还是悲剧?”
“不知道。算悲剧吧。”我回答。
“那咱们的故事呢?不讲完了吗?”他有些不甘心地问。
“讲什么?”
“接着讲下去呀?讲在机场,马上就要登机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回头一看,立刻就发现你了。”他从我手中夺过茶杯,也吮了一口,继续说:
“我狠心往机舱里面走,可走了两步就掉头跑回来了。”
“你为什么跑回来呢?”我故意追问着。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很多很多遍了。
他顽皮地眨眼。
“我……问你要钱嘛,两百块都还给你,我后悔了。”
“小气鬼!那后来呢?怎么不要了?”
他把茶杯放回桌子上,我轻轻握住他的手。
“你连人带车从山坡上翻下来,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我怎么向你要呢?”
他把手指插在我指逢间。
“所以你就留下来,等我醒了再管我要对不对?”我收紧手指。
“对啊!你真聪明。我就坐在你身边等着。怕你跑了。你知道你昏迷的时候一直叫什么?”
他也收紧手指。两只手就紧紧纠缠在一起了。
“我都昏迷了,怎么会知道?”我故意。
“你记性太差了。跟你讲很多遍了,你一直阿文阿文地叫着,护士问我阿文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告诉她,是中文“亲爱的”的意思!”
我转过身,把他拉到怀里。他额上的发又垂了下来,不很长,却很黑很直。
“得了吧,你才没那个闲情逸致呢!我醒过来以后,护士告诉我了,她说你这位朋友真emotional(重感情),一直趴在你床头握着你的手流泪,不吃也不喝。”
我替他整理一下头发。
“我没哭!那是我感冒了,在门外等了你一夜,差点儿冻死了!你倒好,和老情人还有女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吃饺子。”
“哈哈,多久了,还吃醋呢?”
我想去刮一下他笔直高耸的鼻梁。他闭起眼,皱起眉头。
“鬼才吃你的醋!对了,自从你转学来洛杉矶,两年没见了,你不想他么?”
他诡异地看着我。
“哈哈,想!朝思暮想呢。”
我列着嘴,表情夸张。
“想吧!想死你!”
他另一手直奔我的肋骨。
“朝思暮想都想不起来呢!人老了嘛!瞧我这记性!”
我扮一个鬼脸,顺便抓住那只偷袭的手。
他笑起来,仍旧是十六七岁少年般的笑容。
“哎,对了,昨天听一个从密大来的人说,他们过得不错,女儿都学会说话了!”
“是吗?”我应着,“我说你别老张家长李家短的。明天不是还论文答辩吗?准备好了没有?”
“嗨!那壶不开提哪壶!要通不过,我就找你算帐!每天读你的小说,我都快成专业编辑了。”每日朝夕相处,他那几句北京话似乎比我还要地道了。
“好好好,都是我的错。不让你看你非看,看了还那么多意见。怪我结尾写的不真实?要是把咱俩的故事都写上了,这本小说不就真成了我的回忆录了?”
“那有什么不好?真实嘛!现在这个结尾,有点悬。”
“是吗?悬就悬吧,不过难说是不是真的……”
我喃喃到。
是幻觉也好,是猛也好,反正我的梦的确是这样的。我自己知道。
而且还不止这些。
后来,我又回到那纯白色的世界里,又回到那五彩的光环前面,在那里,我没有听到那神秘的声音,却见到了我的父亲。
我告诉他,这许多年,我一直有个疑问。
父亲说:有什么疑问呢?
我说:在咱家的杂物堆里,我曾经找到一本日记。那本日记却没有结尾。我一直寻找结尾。
父亲说:找到了么?
我说:也许找到了,但不是我所希望的。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父亲说:那就好。
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我说:我曾向您许诺过,要毕业,成家。可……
父亲打断了我。他说:小冬,你误解爸爸了。爸爸就是希望你能够自食其力,而且,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然后我便苏醒过来。我躺在密西根大学医院的病房里,浑身缠满绷带。
病房里除了我,只有阿文,他趴在我床头睡熟了。他的衬衫敞开着,饱满的胸肌在略紧的T恤衫下平稳地起伏着。
他的T恤衫永远都小着一号呢。
我没有惊动他。我默默地注视着,他的发,他的额头,他的眉,他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下巴,他的脖颈,他的喉骨,他的肩……
我很努力很努力地注视着他,记忆着他。谁让我有着那么不可靠的记忆呢?
我把他彻彻底底记在心里了。
记得很熟很熟,再也不会忘记了。
明媚的阳光正穿透棕榈树那巨大的叶子洒进屋里来。暖洋洋的。
加州的阳光。
我闭上双眼,依偎着阿文的肩。
我们的手指仍紧紧纠缠着。似乎要纠缠一生一世了。
我仿佛又看到那古观象台了,绿色的长长的列车,正从下面悄无声息地缓缓驶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