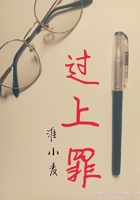沅弟左右:
数日未寄信于弟,想弟悬系无已。余于二十二宿芜湖,二十六宿池州,二十八坐一小舟回省寓中,内外平安。二十五日接到初七日所发一折之批、一明谕、一寄谕,舟中匆匆,尚未咨弟。兹接弟二十六日信,已赶办咨文矣。
弟撤勇之事,余必一一速办,除催李世忠及办里下河之捐外,再札上海官绅办沪捐六十万,并加函托苏、常绅士,必有收获,弟可放心。昨得筠仙信,已办六万径解弟营。弟之退志兄应成全,兄之门面亦赖弟成全。第一要紧守金陵、芜湖、金柱三处,第二要分一支出剿广德,以塞众望。即令朱南桂与刘松山、易开俊三人进剿广德,而弟处派三支,分防宁郡、泾、旌,或亦一道,望弟早为酌定。倘兄之门面撑立不住,弟亦无颜久居山中矣。熊登武、张诗日、刘南云三人,弟万万不可放走。陈舫仙稍迟一步,明年再退可也。此外孰留孰散,听弟裁酌。总不使我遽倒门面为要。千万千万。
弟肝气不能平伏,深为可虑。究之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千万自玉自重。顺问近好。
评点:老九遭各方攻击郁郁不乐
曾氏在金陵住了二十多天,于七月二十日返棹归皖,二十八日抵安庆城,二十九日即给老九写了这封信。他知道老九还在为封爵一事而郁郁,便开导他,又特别指出自己的侯爵都是他所赠送,并要将此遍告家人宗族,用以宽慰大功告成后却偏多忧愁的老九。
老九的忧郁不仅是封爵一事,还有别的。曾氏当然清楚,只是信里没有讲罢了,让笔者来略叙几桩。
一、放走了幼天王。这是令朝廷最为不满意的事。幼天王虽是十六岁少年,并无实际才干,但他名义上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有他在,也就意味着太平天国并未灭亡。何况江南江北尚有二十万太平军将士存在,这些人马很有可能在他的旗号下再度聚集,整军复国。另外,令朝廷不快的是,曾氏六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清清楚楚地写明“破城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事实并非如此。若上纲上线的话,曾氏兄弟有欺君之罪。
二、擅自杀李秀成。朝廷先后两次严令将李秀成槛送京师,讯明后依法处置。但曾氏兄弟抢在谕旨下达之前,便匆忙将李秀成杀了。这便让朝廷内外许多人产生疑问:是真的捕获了李秀成吗?为什么不押李到北京来?这中间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朝廷还为此密令江宁将军富明阿暗中调查。
三、财产去向不明。多年来外间纷传金陵城的圣库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但曾氏七月七日的奏折中说“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还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这几句话,能让朝廷相信吗?朝廷还指望着这笔财富来办事哩,不料竹篮打水一场空。朝廷怎能不生气?
朝廷的强烈不满很快表现了出来。首先是六月二十六日上谕的严厉斥责:“该逆死党尚有万余,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即应一鼓作气,将伪城尽力攻拔,生擒首逆。乃因大势粗定,遽回老营,恐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懈弛万一。该逆委弃辎重,饵我军士而潜出别道,乘我不备,冀图一逞,或伺间奔窜,冲出重围,切不可不虑。着曾国藩饬令曾国荃督率将士,迅将伪城克日攻拔,歼擒首逆,以竟一篑之功,同膺懋赏。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
接下来是七月十一日廷寄的训斥:“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存恩眷。”
再往下,便是曾氏一连七次保举都被吏部打了下来。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曾氏以往的每次保举,朝廷都照准不误。狡兔刚亡,走狗便不受宠了。
紧接着,便是四面八方都说吉字营将金陵城内的财富打劫一空,为消灭罪证,有意放火烧了天王府和其他王府,并骂曾老九是“老饕”(饕即饕餮,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后世以此比喻贪婪凶恶)。
老九虽获伯爵之封,受双眼花翎之赏,处于这种形势下,他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事实上,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有根据的。常言道,擒贼先擒王,打下金陵,却让幼天王逃跑了,缺憾不可谓不大。赵烈文说,幸而后来捕捉了李秀成,否则真是不能交卷出场。像李秀成这样的大人物,当然不能擅自处置。是怕李秀成供出金陵城里的金银财宝吗?无论如何,杀他有灭口之嫌。至于吉字营将士把金陵城财货打劫一空,则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敲竹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便是针对此事的。说是吉字营将士将金银藏在竹杠里,用船载回湖南。后来被官府知道了,便设卡专门稽查。见有装竹杠的船便拦下,用棍子敲打竹杠。竹杠里若装了金银,响声与空竹杠明显不同,一敲便知道。一旦查出,便作私货没收。由此可见他们打劫银子之多。至今在湖南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打开南京了!”这话的意思是说发大财了。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赵烈文当时的日记:“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使槛中之兽大股逃脱。”
照理说,事实是这样,曾国荃也没有必要太忧郁,但他有委屈之感。他的委屈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产生的。
同治二年,李鸿章在打下苏州后,在奏折中写明李秀成从小路搭桥而去。同治三年春,左宗棠打下杭州后,在奏折中也写明听王陈炳文等十万多人逃走。同是打下名城而让主犯逃逸,李、左都没有遭到指责。至于城破后抢劫,几乎是所有胜利之师的通病,为何独对吉字营要求这样严格?
老九的这些委屈,曾氏是深抱同感的。他知道自己的文字,即便是家信,日后也得公之于众,故不愿在信中挑明,只作如此泛泛劝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