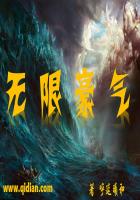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贷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熟,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附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右不忮)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忲。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右不求)
评点:安排后事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奉到一道“前赴天津查办事件”的上谕。天津出的这个事件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天津教案。为方便读者阅读以下所录的几封家书,有必要将天津教案简单地介绍一下。
同治九年入夏以来,天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传说有人用药迷拐幼孩,又义冢内有暴露的小孩尸体,暴露之尸系洋人教堂所丢弃,并有教堂挖眼剖心之说。五月二十日,有人捉拿用药迷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至官府,审讯时牵涉到已加入法国教会的教民王三,于是民情汹汹。二十三日,法国领事丰大业、传教士谢福音面见武兰珍,但武不能指出王三其人,且所供与教堂实际不符。教堂外面,围观的老百姓与教堂中人发生口角、殴打。这时,丰大业持枪进入清廷设在天津的办理洋务的机构——三口通商衙门,并在衙门内放枪。丰大业走出衙门后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向刘开枪未中,伤及刘的仆人。围观的百姓愤怒至极,遂将丰大业打死。百姓的情绪因此更加激愤,涌至法国领事馆,扯毁国旗,捣毁房屋,又放火焚烧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二名、英美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大教案。此次教案中,外国人所遭受的打击,为历次教案所仅见。法国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威胁清廷说要调集兵船,英、俄、意、比等也纷纷提出抗议,事态极为严重。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急报朝廷,并请派大员来津处理此事。朝廷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直隶总督曾国藩。五月二十五日曾氏所奉的谕旨是这样写的:“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五月二十七日,朝廷在接到崇厚的再次报急后,又给曾氏下了一道上谕,令他赶赴天津查明案情,缉拿凶手,弹压滋事人员。五月三十日,朝廷谕内阁严惩作奸犯科的匪徒,紧接着又将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先行交部分别议处,随后又派崇厚为出使法国大臣,向法国政府说明真相,赔礼道歉。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事关重大、朝廷严命,还是职分攸关,重病中的曾氏都不可能不接受这个使命。离保定前夕,他想到眼下天津城一片乱哄哄,中外情绪都在激昂中,事情不仅棘手难以处置,即便处置了,也绝对是两边不讨好。事多心烦,再加之病情严重,此去天津很可能不是活着回来,于是给两个儿子写下了这份带有遗嘱性质的信。
信中所说的运灵柩回湖南之事,自是一般人的不愿客葬他乡做野鬼的心态,可不必说;关于不忮不求勤俭孝友等等,乃曾氏一贯的主张,先前的家信中反反复复地说得很多,也可不必再赘述。与通常人的遗嘱不同的事,曾氏着重叮嘱二子今后要“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这是因为曾氏的兄弟经历与常人不同。曾府的真正鼎盛靠的是那场战争。五兄弟四人带兵在外打仗,一人在家守摊子。曾府因此赢得“一门忠义”的御旨赞誉,又因两人死于战场,使得这四个字的分量更重。在曾氏看来,曾府今日的局面,是众兄弟共同撑起来的。此为其一。其二,老九战功最大,为家族捞得的金银最多,曾氏又常说他的侯爵是老九送的。信中说各家的“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可知曾氏一直深记老九对家族的实在贡献,并对他心存感激。其三,曾氏从三十岁起便离家宦游,不能多管家事,身为次子的老四实际上挑起了长子照顾家庭的重担。
凡此种种,使得曾氏对健在的两弟的情感大为超过常人手足之情。明白了这几层原因,便不难理解“事两叔如父”的话了。
这封信另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关于他对自己所留文字的处置态度:奏折、古文不可发刻送人,只留于子孙观览;不刻文集。其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文字不足以传世。
他的这个遗嘱,家人并没有执行。他死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二年便开始刊刻他的全集,四五年间他的全集陆续刷印问世。不但奏折、古文刻了,他的诗、杂著、批牍、信函都刻了,连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如日记、家书等也刻印了。
由李瀚章、郑敦谨等人主编的这套《曾文正公全集》,后来成了晚清人物文集中最为著名的一种,百余年来对中国官场士林影响最为深巨。到了20世纪80年代,湖南岳麓书社则组织学者专家对存世的湘乡曾氏文献予以清查整理,积数十人之功,历十余年之久,出版了一套三十册一千五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将曾氏遗留人世的所有文字搜罗一尽。
曾氏家人不执行这个遗命是对的。因为曾氏一旦谢世,他的文字便进入历史档案一类,将它公之于世,对于历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倘若拘泥于遗命,反倒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事实上,曾氏本人及其关系密切之人,早就知道这些文字必定会刊刻出来的。曾氏将所有文字均录副送到老家保存,便是试图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他的档案,以利于今后出全集。他的日记绝少涉及机密事,也很少臧否人物,也是出于今后面世的考虑。有一次,老九看了曾氏的日记后,发现其间有对自己不利的文字,曾氏说可以将那些文字涂掉。
既作刊刻的考虑,又不同意发刻送人,看似有点矛盾虚伪,其实不然。曾氏是一个明智的人,自我看待是一件事,别人看待又是一件事,两者不能混淆。“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尽管自己不愿刻印文集,但他知道,刻印的“厄运”是不可逃避的。一向谨慎的他,于是处处预做日后刊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