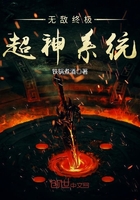自从路之函转性以来,每每与先生的谈话便不再让我替,而是自己亲去受教。他与先生大谈商贾之道时我和糖豆呆得无趣,便悄悄溜去集市。此时路之函也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们在谈话结束前溜回来,他也不会多说什么。
我和糖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他溜出来纯粹是打发时间连带着看美女,而我,则是来探消息的。冲着这一点,我觉得自己的动机还是相当高尚的。
眼看已经过去快四个月了,我在都城所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但我却一点都打探不到阿非的消息。有时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脑子发热,一股脑的认定阿非一定在都城,可直觉有时就是这样,认定的就是认定的,加之我平日里也有些死脑筋,往往认定的事都是一较到底。
已经数不清多少次,我兴冲冲的跑到街上,却沮丧的返回。
无聊的踢着脚边的小石子,我撅着嘴捏着帕子往回折返,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幕幕阿非带我逛遍大街小巷的场景。
偶尔身边的情侣嬉笑的话语声也会吸引我,登对的青年与女子围着胭脂水粉首饰摊一件件挑选中意之物。那种感觉,让人觉得暖心,却也格外落寞。
我收回心思继续游荡在集市上。
也许,还是去求助先生,说不定能有结果。
我低头悠悠的走着,心绪飘荡悠远绵长。
“姑娘,买朵花吧!”
“小妹妹,挑个发簪不?”
“新鲜的蔬菜!”
“热乎的馒头喽!”
我走在热闹的市集里,越发的觉得形单影只。
远处,十余丈开外的地方忽的掠过一抹白影。那一刻,我仿佛忘记了呼吸,于天地间再看不到其他人,只有那抹白影。
然那白影只一晃便消失于繁杂的小摊之后。我甚至来不及细想,提脚就追了上去。
我绕过了无数的摊铺,七拐八拐的在市集上奋力的奔跑着,可是那白影仿佛消逝了一般,又仿佛从未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局促不安的在原地打转,四处张望,可就是找不到那抹身影。绝望就像汇聚成海的水流,无情的充斥着我的心,直至占满。
无论如何我都不愿相信,是因为思虑过甚产生了幻觉,我坚信,阿非他一定就在都城,在等我。就好像在苍茫的雪山,他微笑着在前伸出手,一把将我拉到身旁,那种触手可及的距离。
蓦地,一角白色飘过眼帘,我惊喜的抬起头去追寻那抹痕迹,远处浮现出白衣男子的修长身影。
我咬着唇,忍住涌上眼圈的泪水,踉踉跄跄的提起步子追上去。
直到我站在他身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嘴唇和舌头在发抖,我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颤巍巍的伸出手想去碰触他,却又怕那只是我的幻象,碰一下就会彻底消失。我就这样半举着手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在摊位上精挑细选,看着他从怀里摸出钱来给小贩。这样的距离已经让我由衷的觉得幸福,我以为山洞里那一眼就是诀别,我以为我再也不能亲眼看到他,我甚至在跌下山头时脑海里都是我们的过往,就连病榻上昏迷的那些天,梦里也全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