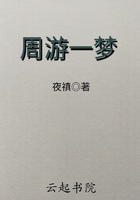这一次梦里那双含恨的眼神消失了,可以舒心的踏实的睡上一觉。
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又看见了那个人爱怜的看着我,只是此时的我,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自此,我休养了好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多久,我看着外面的花盛开凋谢转换成了漫天的大雪,白茫茫的一片,树枝早已枯萎。
此时,玻璃房的人消失了,唯一的彩色也跟着失了踪。
这个会怜惜我的人,会温柔的抱我的人,是一个医生。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外婆。因为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和她生活在一起。
离开了医院,我终于可以看着阳光,摸摸花草。只是我的身子太差,一点点细菌都不会放过我,一点点小事都能让自己疼得打滚。这个时候,外婆总会抱着我说,一遍遍的说,“对不起,对不起”。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那声声“对不起”的时候,心会疼,很疼。
这些离开医院的日子里,偶尔还是会被梦惊醒,慢慢的有了眼泪,慢慢的会流着泪醒来。
还是不可以上学,但是有了一个会教我东西的老师。外婆说是家教,每日我开始充实自己,连老师都夸我,学什么都快,半年后,我自己能开始独自看书,写字,画画。
如今的外婆开始忙了起来,也不再日日在家,总会让旁边的一个奶奶给我送饭,或者照看我。
邻居老奶奶家也有一个小孩,比我小,那是我的第一个小伙伴,小果子教会我了很多,虽然都是小事,但却是我开始触及,慢慢的我脸上多了笑容。
奶奶家有一个小小的书店,带着四岁的孙子果子守在那里。
如今这个书店多了一个我,也许因为一直在医院,对外界总是很渴望,但终不敢为矩,所以我会拼命的看书。
开学了,我目送了果子去上学了,而后,每日便只有我和老奶奶,守在那书店里。
除了上午和下午一个小时跟着家教外,我最多的时间是看书。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只知道慢慢的看书的速度越来越快。
偶尔果子回来会给我讲,他们学校的事,偶尔会和我说起外面多好玩的事,还信誓旦旦的说,带我出去玩,可每次都被老奶奶拦下了。
我知道,不能任性,因为我不再想看见那双含恨的双眸。或许是违心的,只是那双眼已经刻划在了心底里,沉积了下来,不敢在去盘踞。
外婆越来越忙,偶尔深夜醒来,空荡荡的房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的呼吸,或许还有鱼缸内那几尾鱼。
书中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我明白了很多,慢慢的知道什么是寄人篱下。
我便整日整日的在外婆家看书,偶尔到阳台上晒晒太阳,我喜欢被阳光温柔的包裹着。
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慢慢的喜欢上了这种日子。中途我多了一位家教,因为我会问外婆,“外语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学”,之类的话。后面来的这个家教,很是负责,会给我讲故事,看了我画的会赞美,又问了我许多,慢慢的我接触到了更多,我们相处得很是愉快。
同年,在外婆的点头下,我进入了学校,大家都只是以为我是转学生,其实我不是,我没有上过学,除了那么几个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每次只有傻傻的跟在后面或者选择沉默,但是在短短的校园生活里,我却很快乐,感觉自己很幸福。
过了九岁生日的那年,熟睡的我一醒来,看见外婆泪盈盈的看着我,“宝贝,你最后再一次给哥哥输血好吗,害怕吗”。
我坐起来,乖巧的点了点头,一切都改变不了的现实,“外婆,我去给哥哥输血”。
哥哥,我只是从书中见过,对于我而言,那么的陌生。
此时,我才明白,那个人是我哥哥,我一直抽血是为了他。
在我年幼的记忆力,我没有叫过爸爸,也没有叫过妈妈。我以为那只有书上有,因为我也没见过小果子的父母,我不知道我也有家,不知道小果子知道不。
以为能开开心心的背着书包上学,可以唱着歌跳着舞的和伙伴们玩。以为就算不能上学,依旧能在这屋子里面,自由的玩,自由的安排。
九岁那年,这对夫妻来了,我对他们记忆犹深,午夜那双含恨的眸子,已经渗入了我的一切。
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望着这对人,不知道心里一份渴望是什么,一份害怕是什么。
九岁那年,他们找了来,我才知道我有亲人,除了外婆以外的亲人。
九岁那年,我才明白,原来我是一个活着的供血体。突然很黯淡,又像回到了血液被抽走的时候,难受,很难受。
外婆拥着我,九岁的身体比正常人瘦小,冰冷的眼泪落在了我的手臂上,“宝贝,这是宝贝最后一次”。
我看着外婆苍老的脸,摸着那蓄满泪的眼睛,望着那复杂的眼神,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外婆慈爱的看着我,然后眼泪离开了眼眶,滑落了下来。
退出了外婆的怀中,我站在那里,此刻不知为什么,我却笑了,莫名的笑了。
再一次回到了这个白白的世界,可我的脑袋里回不到那一片白的时候。
为了这一场准备,检查的项目日渐频繁,每日只能吃固定的东西,每日必须做固定的运动。
在这日复一日中,努力的配合医生提出的所有条条框框,慢慢的适应了这白白的世界。
第一次面对面的看到了自己的哥哥。他坐在轮椅上,脸色很不好,和抽完血的我一样,惨白惨白,他泪眼朦胧的望着我,“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