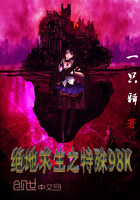崔柔到了前营,只见众卫士已摩拳擦掌,准备厮杀。营外大道上百丈外,青压压一片长枪阵,正是敌军步兵攻营来了。让崔柔不解的是,这敌卒手中握着的长枪甚长,每支起码接近两丈,这么长的兵器在步兵接仗时如何施展的开?
正在崔柔疑惑不解之时,只听敌营里一通鼓响,那些散漫的敌卒迅速插枪列阵,组成一道方阵。处在第一排的敌卒手中却无长枪,而是每人举着一块齐人高的盾牌,身后却是每人一杆长枪。鼓声稍歇,只见敌军阵势已成,长枪森森,给人以无坚不摧之感。崔柔见了敌人这长枪阵,马上明白敌人见己方人少,又无城池依托,意欲强攻。果不其然,只听一阵急促的鼓声响起,长枪阵开始移动。敌军显是操练已久,只听“擦擦擦”皮靴触地的声音,虽然是走在坑坑洼洼的满是尘土草地的道路上,但这脚步声却是整齐明亮丝毫不乱。
崔柔明白若让敌人这方阵移动到营前,单凭这些“拒马”木栅栏是根本无法阻挡的,只有趁敌阵还未靠近前,先打乱其阵脚,随即对身旁一名卫士吩咐道:“你马上去把后营守卫的人全部调过来。”又对其余卫士说道:“以我为准,我立在那里,你们四人一排立在我身后,每人间隔两步。”扬了扬手中弓箭又说道:“记住!我的箭射到那里,你们就跟着射到那里,先射敌军后阵,就算敌军前阵冲到跟前,只要我没有动,你们就不准动,否则军法处置!”说完,拿了两枚长弓提过四筒箭袋来到营前拒马前,十八卫见状纷纷取了硬弓箭支赶到崔柔身后列队。
敌军“擦擦”的阵脚移动的声音,像一只无坚不摧的怪兽靠近过来,崔柔知道此时绝对不能自乱阵脚,早在几个月前,她就听兄长崔刚说过,一伙贼众从山海关外入寇,人数只有区区五千余众,但接连攻陷幽州兖州势不可挡,就连两州都户使都战死杀场。据斥候回报,那伙贼众人人短发青衣,作战时以大部步兵结成枪阵,两翼辅以强骑,阵后有弩兵和刀兵。看眼前这方阵,虽然只有区区百人,也无强骑和弩手,但仔细看确是人人着青衣,削短发,看来真是入寇幽兖的那伙贼军攻到安邑城来了。此刻用弓箭对付这长枪阵是否有用,崔柔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好在这山梁地势狭窄,敌人的长枪阵摆出的只是一个残阵,不光人少,更没有了两翼的强骑和弩手的保护,而且移动时为保持方阵威力,持枪士兵只能踏步前行,移动的速度过于缓慢,也不能左右移动,更不能后退。崔柔知道若要击败这样无坚不摧的方阵,只有摧毁阵中持枪士兵的心理防线,才能让这方阵不攻自溃。此阵厉害就厉害在身处阵中的士兵,除去四面最外层,里面的士兵前后左右四面都是己方人员,自己无后顾之忧,再就是如若心怯想临阵脱逃,也无路可逃,只能一条心思向前冲击,击败前方敌人才能活命。
敌人方阵那催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却见崔柔把箭筒里的箭支取出插在脚下,动作不慌不忙。身后的一众卫士见状,因临阵而急促的呼吸声稍稍平复,都学了她的样子将箭支竖插在身前的泥土中。
眼见敌军方阵前队已进入弓箭射程,崔柔左手持弓,右手指间夹了三只箭,其中一支已搭在了弦上,众卫士见状纷纷搭箭,更有心急之人已拽满了弓弦,但崔柔
却迟迟不肯发箭,众卫士只得静静等待。
在擦擦的脚步声中,敌军方阵大部已进入弓箭射程,只见崔柔手臂轻舒,弓已满弦,箭尖斜指向天,只听“嗖”的声响,那箭射向天空,划过一道弧线,一声惨叫,方阵中一名持枪敌卒应身倒地。紧接着嗖嗖嗖一阵放弦声响,天空中下起一阵箭雨,虽只有区区一十八支箭,但十八支箭一齐划过空气的声音,仿佛一阵疾风吹过,敌阵里一片惨叫,又有十来名敌卒中箭。
这时敌阵后方鼓声响起,一声响过一声,那方阵后队未中箭的士卒越过中箭倒地的己方士卒,迅速与前队汇合,一个完整的方队又组成了,随着身后那腾腾的鼓声越来越快的接近崔柔的营地。
这边,随着崔柔射出第一支箭,这箭雨就不曾稍有停歇。十八卫果然依崔柔所言,崔柔的箭支射到那里,他们的箭支就跟到那里,而崔柔每一箭都射向敌阵人员密集的地方,两箭绝不射在同一个地方,敌阵里哀嚎阵阵,敌卒一片一片的倒下,但敌阵后的鼓声却像催命的音符,催逼着后面的士卒填补倒下的士兵。如果崔柔此时有暇去查看敌阵后方,她会发现敌阵后方有一队弓弩手正弯弓搭箭,但他们的箭尖所指的不是崔柔和她的一十八亲卫,而是组成方阵的人,那是准备射杀方阵中想转身逃跑的人。
在短短百十丈的距离,锵锵的脚步声,咻咻的箭羽声,组成一道道死亡的声音,方阵终于在损失了大半的兵力后,已靠近了营地。崔柔忽然停了下来,松开早已麻木的手指,转身对身后的十八卫喊道:“散开!把你们所有的箭支全部射到拒马前!”说完转身抓起箭支,不顾一名敌人的长枪已刺到了跟前,“咻”的一声响一支羽箭从崔柔耳旁穿过,射进持枪刺来的敌卒左眼之中,校尉秦度从后面赶了上来,与崔柔并肩而立,此箭正是由他所发!
就在这营前拒马旁,敌军方阵冲到跟前,却被距离更近穿透力更强的箭支死死钉住,一片一片的敌卒倒下盖住了拒马木栅栏,有少数冲过栅栏的敌卒,但丈把长的长枪,在近距离又如何是十八卫钢刀的对手,一一被砍死在阵前。
敌人方阵终于溃散了!弃枪的敌卒踩着同伴们的尸体疯狂的向回跑,在乱枪林立的营前大道上如同树林中受惊的兔子。崔柔站在那里,身上的白衣白甲已被鲜血染红,手上黏糊糊的都是血,手中的钢刀已滑落在地上。
无论是崔柔还是她身后的一十八卫,人人疲累欲死,大家都明白虽然杀死了上百名敌卒,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此刻如若敌人再来,大家也只有死路一条,好在经过这一场生死大战,众人早已是把生死置之度外,虽然手脚酸软,拉弦的手指几乎麻木,但人人精神亢奋,恨不能踩着遍地的敌尸杀出营地。
崔柔明白敌军已被吓破了胆,但己方如想就此冲出包围,那也是不可能的,随即吩咐十八卫就地休整,自己也脱下了身上沾满鲜血的盔甲。十八卫见从来甲不离身的崔都尉都卸了甲,也纷纷放浪起来,有人袒胸露怀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有人跳将起来,指着出峰口的敌营大声笑骂,更有校尉秦度领了两人从后营牵来一匹敌人留下的军马,在营前杀了,燃起篝火架了铁锅,在阵前煮起马肉来。崔柔心想,敌人军心已挫,此刻十八卫越是放浪,敌人就会越是惊疑不定,不敢贸然再次进攻,自己与十八卫也能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遂也不加阻止,反而让一名卫士去摸管治此粮草营的军官的帐篷,还告诉卫士那里可能藏着好酒,众卫士大声叫好,一下子就有五人从地上爬了起来,涌进后营,显是都好此道。不只是崔柔明白,众卫士也都清楚,管治粮草军需在任何军中都是美差,军官往往在自己帐篷里藏有私货,虽军中往往严令禁止饮酒,但却很少军卒能在此事上令行禁止,不管是那里盖莫如是。
果然,铁锅里马肉流香,后营里摸酒的卫士已是一人一坛抱着美酒回来了。还没等崔柔吩咐,众卫士已经是摩拳擦掌,纷纷抽出腰刀,也不管马肉熟是没熟,割下一块便大快朵颐起来,边啃马肉边就着坛口喝酒。
崔柔抽空查看敌营,只见远远的有一骑立在敌营前,马上那人拿着根两尺长的木棍对在眼睛上向这边望过来。崔柔不知这人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他在做什么,但看此人身形装束,仿佛便是在安邑城外劫掠的那伙人中的头目。“原来他们和这些贼军是一伙的。”崔柔心想,同时心中怒火更炙,恨不得立时冲上前去,一枪结果了那人性命。
这边,校尉秦度正吩咐一十八卫,肉可满饱,酒只可饮七分,还有那三分是留着握得住刀,提得了枪,奋勇杀敌用的,众卫士听罢,纷纷唱喏,更有卫士提了酒坛走上前去,用抓马肉的手指着敌军,大声骂道:“贼斯鸟!有胆子的再来与你爷爷大战一回,你爷爷我喝了酒,这手可痒的很,想杀人呐!”众卫士听罢,大笑附和。
崔柔吃了几块马肉,不善饮酒,只与卫士们就着酒坛喝了两口,见大家喝的已差不多了,又暗中吩咐道:“一会还有大战,酒就不要饮了,吃饱了马肉,大家轮流歇息。”众卫士答应了,依旧装作狂饮不休的样子。
不久敌营里走出一名手举白旗的士卒,孤身一人来到崔柔营前,十八卫里一人****腰刀,翻过木栅栏,就要将那敌卒砍翻在地,那敌卒却说道,是他家将军向各位壮士提议,等他们先收拾了己方战死的士卒尸体,两边再来交战。崔柔听罢一挥手,算是答应了。那敌卒正要转身离去,崔柔却突然问道:“几天前,安邑城下劫掠的是不是有你?”那敌卒一听崔柔如此问到,吓的一下跪倒在地,连连摇头,口中只呼没有。这时崔柔身后一名卫士说道:“有他!我记得混战中这贼斯跑的还挺快,刚跟我打了个照面,就窜到屋后了,我还听到有人叫他‘蛤蟆’。”那打白旗的士卒正是那晚烧了哑女木屋,迫的扶苏掉下悬崖的众人中的一员,人称“蛤蟆”的就是。
“临阵交锋,不斩来使,先留下一只耳朵吧!”崔柔说道。那提刀的卫士等的就是这句话,只见刀光一闪,伴随着一声惨叫,蛤蟆左手捂住脸旁,不顾已被斩落的左耳,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去,匆忙中竟连白旗都顾不上带走,惹的十八卫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