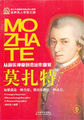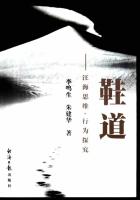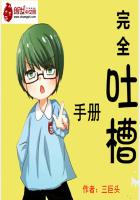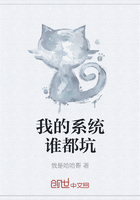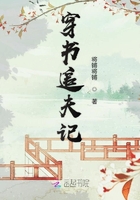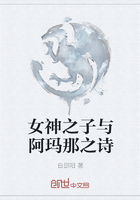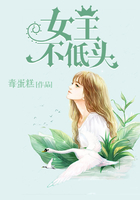弘一法师沉默了片刻,忽然大声说道:“就是一句-南-无一一阿-弥一一陀一一佛!”
这几个月里,他这寺中的僧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之间的感情相当融洽。但是,此时他却不得不走了,他不愿意大家为他操劳,也要继续到他处去弘法。临行之前,弘一法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郑重地交给谈虚法师。谈虚法师展开来一看,上面写着五个条件:
第一,不许预备盘川钱:
第二,不许备斋饯行;
第三,不许派人去送;
第四,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
第五,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
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处,谈虚法师对弘一法师的为人已有许多的了解,对于弘一法师提出的要求,前四条他都并未感到惊讶,只是他并不理解第五究竟为何。但是他相信弘一法师的要求自然是有其道理,也就全部依从。
对于弘一法师,来去,结是缘。他跟着缘分来了,缘尽了,也便要走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如同花落花开。过多的执念和情感,只是徒劳的挂碍。
4.梦·晚晴老人
【忆儿时】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李叔同
烽烟滚滚,迷了人们恐惧的眼,世间苦难,在战争中一一上演。从此,岁月里,所有美丽风光,都被硝烟遮盖,所有美好的声音,都淹没在嘶喊和悲声里……
此时的上海已处于了大战之中,战火硝烟弥漫在上海的天空中,这个原本风情万种的城市在战火中叹息。在上海,唯有租界尚能暂时避难。弘一法师此前已给在上海的夏丐尊写了信,表示要在上海停留:“拟暂寓泰安栈。(新北门外马路旁,面南,其地属法租界之边也。某银楼对门,与新北门旧址斜对门,在其西也。)即以电话通知仁者,当获晤谈也。”
半生的好友,情分已经深深根植在心里。夏丐尊接到信后,十分担心,上海正值战火危难之际,而青岛相对平静,于是写信劝说弘一法师暂留青岛,然而,弘一法师依旧是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还是毅然地离开了青岛。
畏惧,是因为恐惧死亡,弘一法师心中澄净,生死皆是缘分,便以面对战争,他便无所怖畏。
上海相见时两位旧友并未多言,岁月催人老,几年的光景,彼此都成了老人。弘一法师见丐尊的脸上有愁苦的神情,就笑着对他说:“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渴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世间诸事,弘一法师已经看淡了,一切如梦幻,也就不必过多执念。
依照计划,弘一法师将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再回到厦门,在第三条弘一法师即将离开始,夏丏尊又到弘一法师所住的旅馆看完。
此时,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外滩附近狂轰滥炸。而弘一法师的住处就在此。在这里住的人,一直都是神经紧绷,时刻都是受到弹火的惊扰,每眼神中都烙刻着深深的恐慌。然而,当夏丏尊见到弘一法师之时,便惊住了。弘一法师端坐着,捻着佛珠,嘴唇微动,念诵着佛经,宛如一尊佛,在这战火硝烟之中,散着纯净慈悲的佛光。夏丏尊看得出神,深受震撼。
这天中午,夏丐尊与几位朋友请弘一法师到觉林蔬食馆午餐,然后又要弘一法师到附近的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年春天,夏丐尊把这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则言:“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师最近通讯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效空爆最哑,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回到厦门住在万石岩。然而,厦门的形势也不乐观,战事一触即发,许多友人都十分担心弘一法师的安危,劝法师保自身安危,众人关心和好意,弘一法师感怀于心,但却坚定并不会为战事而逃离。
弘一法师开始了弘法之路,这一次,弘一法师到泉州弘法,与以往有所不同,广结法缘,就算是孩子,他也要开导。在开元寺里,弘一法师住在寺的后院,这里有晚二堂课诵,他经常会早晚听到慈儿院的学生念佛念经得法,那整齐的诵经声,让他感到一种纯净和浓浓的暖意。这次他再次来到开元寺,专门为慈儿院讲了《释迦牟尼佛为法舍身》的故事,学生们很喜欢听。
1938年5月中旬厦门沦陷,整座城,都陷入一种颓败和冗长的悲伤。那时,弘一法师正在漳州弘法。
7月,草长莺飞,万物兴荣,而弘一法师却越发衰微,逐渐走向了生命的迟暮。丰子恺写了一封信给弘一法师,希望他能够来内地与自己一同生活,并供养大师的余生,信中言辞诚恳,弘一法师收到此信后,心中十分感动,但是他仍旧决定留在闽南,便给丰子恺回了信:
朽人年来,已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弘法,近在漳州亦尔。犹如夕阳,殷红绚彩,瞬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纪念耳……缘是不克他往,仅谢厚谊。
弘一法师给其他友人的回信也一样,类似“近在泉州讲经,法缘甚盛”、“于厦门变乱前四天,已至漳州弘法”、“朽人近来漳州,弘扬佛法,十分顺利”等言语出现得十分频繁,多少表明了他对弘法的信心和决心。
弘一法师的宗教观非常明确,他虽是出世的僧人,却感念着俗世红尘,他用出世的慈悲和觉悟,在坐着俗世的事业。
佛不是孤远的幻影和清寂的梵音,佛是宏大而广博的仁爱。
佛说,我们眼中看到的世界,就是心里的世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世风日下,人们的心中被动荡的社会颠簸着,于是,浮躁的激进分子佛教被扭曲成了死人的宗教。为拯救中国颓微的佛教,弘一法师竭力提倡整治戒律,拂去佛教所蒙的尘埃,让佛光重新普照。他更是以自己“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苦行经历,开导众生。
这一年,弘一法师60岁了,六十而耳顺,他看将人生都看尽了,身体也在岁月中苍老了,再遇到艰苦的环境,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他的体质极速衰弱,许多人都为此感到吃惊。
1939年的农历二月五日,是他亡母谢世的34周年,弘一法师在一册《前尘影事》上作了这样的题记:“二月五日为亡母谢世三十四周年,敬书金刚经渴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回向菩提,时年六十岁。”
想起母亲,就不免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又想起了曾经那首婉转的诗《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在生命尾声之际,他深深滴陷入了生命之初的回忆。他经常梦见这种童年时的情景。那些欢乐,那些苦难,那些惆怅……都格外清晰。梦境过处,即是一生。弘一法师有一个别署,叫“善梦”,这段时间也经常用到。
虽然身体日渐衰弱,这病弱的皮囊并没有阻碍弘一法师云游。弘一法师60岁后,仍像孤云野鹤一般地奔走于各方。他在先后去过清源山、永春、普济山、南安、晋江、灵瑞山等地。这位誓舍身命,勇猛精进的高僧,依然为了救护国家,抱着“救国必须念佛”的信念。对于祖国,这位晚晴老人的心,始终是热忱的。
5.笑·人生如戏
《废墟》
看一片平芜,家家衰草迷残砾。玉砌雕栏溯往昔,影事难寻觅。千古繁华,歌休舞歇,剩有寒(JIANG)泣。
--李叔同
都说人生如戏,戏又如人生。舞榭歌台,转换着一场又一场的人生剧目,辗转飘零,各色人生都看尽了,再繁华的故事也要谢幕,当一切尘埃落定,面对生命的归去,你是心中又是怎样的感受……
曾有人说:这世间除了生死,没有大事。的确,生命是承载人生的根本,生命的始末,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生死,弘一法师有着自己的一番见解。
对于死亡,弘一法师非常郑重地讲了《人生之最后》这一课题。讲述共分了六章。他将死亡分成了病重时、临终时、命终后一日、荐亡等事。这一课,是将给众人听的,亦是弘一法师对自己生命的交代。
弘一法师曾说:“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心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他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放下了自己,放下了一切,唯有佛,端坐在心中。
弘一法师在第二次去往惠安弘法时,因为居住条件差患上了风湿性溃疡,可他并未服药,之后又连续高烧,甚至四肢已经发生了溃烂,一周后,高烧渐退。病痛让他体会到了皮肉的苦痛,却让他更加坚信佛法。繁华和颓唐他今生已经看尽了,他已经在沧桑世事里浮浮沉沉过一整个生命。人生,佛生他曾完满地活过两度生命,今世生死,便看淡了。死亡,只是一个静默的句点,无喜无悲。
当弘一法师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将逝,遂写了一封书信,致李芳远:“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即往生极乐。犹如西山落日,殷红灿烂,瞬即西沉。故凡未圆满诸事,皆深盼仁者继成,则吾虽调,复奚憾哉!”
弘一法师又将自己的后事交给了妙莲法师,他特地叮嘱妙莲法师两件事,一是圆寂前后,看到他眼里流泪,并不是表示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他一生的憾事,为一种悲欣交集的情境所感;二是当护膝停顿、热度散尽时,送去火葬,身上只穿这身破旧的短衣。遗体停龛时,要用小碗四只,填龛四角,以免损害了蚂蚁的生命。
生死,是世间的大事,然而,再面对死亡之时,弘一法师淡然视之,却悲悯蚂蚁的生命,是一种超然的大境界。
《梵冈经》亦云:“勿轻小罪,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刹那造罪,殃堕无间;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也是提醒世人要处事老实,行善造恶自有因缘果报,不可不慎!
《佛经》中也有记载,一名高僧知道他的小沙弥徒弟只剩七日的寿命,于是慈悲地让他回家探亲。途中,正好遇到一场大雨,小沙弥发现一群蚂蚁正努力地从积水的地方爬出,但却不断地被雨水冲回去。于是小沙弥心生怜悯,先将它们一一救出,确定安全无虞后,才继续他的旅程。七日后,小沙弥又回到寺院,师父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人定观察,发现原来是小沙弥的一念慈悲心,不但救了蚂蚁,也增加了自己的寿命。
佛是一种无量的智慧境界。每一个佛家的释子的顿悟各有不同,弘一法师对佛的觉悟,是积极的,热忱的。他没有逃避世事纷扰,反而是体恤众生苦难。救济众生成了弘一法师此生鸿愿。大悲众生之苦,愿一自己的肩膀担负众生的苦难。
八月三十日,这一整天,弘一法师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念着佛号,他的人生已经功德圆满,今生往事,终于在经历了六十余载的奔走后,尘埃落定。他的心中,只剩无限平静还有无限宏大的佛法。
九月一日上午,阳光明艳的倾泻,他为黄福海居士写了一副座右铭。又在下午的时候写下了“悲欣交集”四个字。这也成为了弘一法师的绝笔墨宝了。
“悲欣交集”因为弘一法师而光为人知,这也成为弘一法师从此生走向往生的概括。不念佛的人不会知道念佛也会起悲心,弘一法师的一悲一喜,是一种念佛见佛的境界。
九月三日,妙莲法师再次恳请弘一法师吃药,然而弘一法师还是轻轻地挥了挥手,拒绝了。他让妙莲法师为他书写遗嘱,把自己放心不下的事情都一一交代嘱咐给养老院董事会,他向董事会作四点请求:“一、请董事会修台(就是将过化亭部分破损的地方修复)。二、请董事会对老人开示净土法门。三、请董事会议定:住院老人至80岁,应举为名誉董事,不负责任。四、请董事会审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自己虽乐为助理治圃责任,应改为庶务,以减轻其负担。”这些都是一些原本无关于他的一养老院的一些细微事。慈悲的弘一法师,在自己生命路尽时还在为的老人们忧虑着。
之后,弘一法师将那几封早就准备好的给几位友人的信,让妙莲法师帮着填上日期,分别邮寄给夏丏尊、刘质平、丰子恺等几位友人。
诀别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信云:“朽人已于某月某日谢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宜。”
九月四日弘一法师的呼吸渐弱,妙莲法师在一旁助念诵经。不知何时,妙莲法师见弘一法师的眼角流出一滴晶莹的泪,一滴悲欣交集的泪。在泪滴落下之时,弘一法师也终于是了无牵挂地上路了。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抹静静的微笑,那佛的笑靥,是他生命最完满的句点。
弘一法师德高众望,九月六日,上千人念诵着“南无阿弥陀佛”跟随在弘一法师的灵龛后为弘一法师送行,一种悲壮的气氛笼罩在天空之上,整齐的经声有一种旷远的宏大。
第二年,妙莲法师在《晚晴老人生西之后种种》一文里向世人述说了大师火化时情景:老人于去年九月初四晚八时入灭,延至初六上午入皂。下午送盒去承天寺安座,至十一晚七时大众集会,诵普贤行愿品完,起赞佛渴念佛,至八时焚化,(遵老人过七日后焚化遗命)至十时即化毕。四众皆见有多色猛烈之火光。十二日晨拾灵骸,装满两坛。当时拾得舍利数颗,其余碎骨炭灰等,弟均将包起收藏。事后即将灵骸遵遗命送开元承天二寺自己房内,于百日内常念地藏菩萨,随于碎骨炭灰内拣选舍利,至百日拣去碎骨炭灰三分之一,得舍利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五六百颗……
他的一生,是说不尽的传奇故事,其生其死,都充满了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评出韵味的时候,便卸妆收场了。
“世间无不散的筵席,无不凋谢的花朵。”
在喃喃的经声中,弘一法师将于世永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