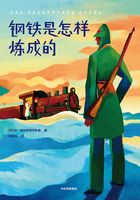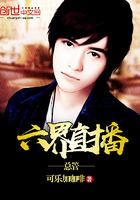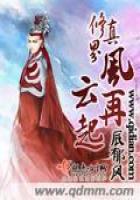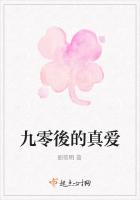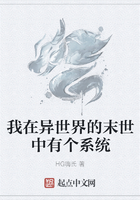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Dickens,1812.2.7—1870.6.9),十九世纪的英国大作家,作品擅长描摹现实,富含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主要代表作为《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本次入选两篇:《信号员》和《谋杀案之审判》皆发表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小说之典型,也是狄氏早期之杰作。主要以气氛烘托,人物刻画见长。故事虽短,寓意深刻。狄更斯写鬼物,不写其形貌,影影绰绰,点到为止,自留于读者诸君想象,此为其特点。
“喂!下边的人!”
那时,他正站在他的信号所门前,手里拿一面小旗,旗子卷在一根短棒上,却突然听见有声音这么喊他。你可能以为,看这里的地势,他断不会怀疑这声音的来源;他的上方是一面近乎刀削的峭壁——当时我就站在顶上——但是,他却没向上看,而是转了个身,往下面的铁路线上看。看上去他的脸色有些异样,虽然我至今也不明白他为何如此,但这已足以吸引我的注意了。只是他站在深谷里,我只能看到一个身形和影子。而且我站在峭壁顶上,正好被西边的火烧云照着,必须用手搭个凉棚才能看见。
“喂!下边!”
他收回目光,又转身四顾,然后才抬起双眼,看到我在他上面。
“这里有路可以下去吗?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呢?”
他便抬头看着我,却不作答,我也向下看他,只感到自讨没趣,不好催促他了。这时,地面和空气中突然产生一阵含混的颤动,俄而却变成猛烈的震动,那扑面而来的冲力似乎要把我推倒一般,我不由得后退了几步。我再往下看时,却只见蒸汽腾腾地升上来,那列火车已飞快地呼啸而去,缓缓地消失在远方,他已经完成火车过洞指挥的任务,正在卷旗子。
我又问了他一遍。却见他顿了一下,仿佛在凝神看我,接着便挥舞手里卷起的旗子,指着一个和我等高的方向,大约离我两三百码的样子。我便朝他喊了句“好的”,就往那边走。走到边上,我定睛一看,豁然发现眼前有一条崎岖不平的“之”形小径。
这小道实在陡峭至极,仿佛直直落下去一般;正好凿在一处阴冷的岩壁上,常年变得又湿又滑,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感觉那路变得更长了,我甚至回想起他当时给我指路的神情,真是窘迫又无奈啊。
当我走到足够低的地方,才再次看见他,他正站在火车刚经过的两条铁轨中间,似乎在等我出现。他用左手支着下颌,却把左手肘搭在胸前右手上;他的表情充满期待和观望,我不禁停下脚步,疑惑了片刻。
然后继续往下走,一直走到和铁轨齐平的地方,才信步朝他走去。
却只见一个面色蜡黄、浓眉黑须的黑汉子。这样的岗位实在孤独凄凉,我再没见过比这更糟的地方了。两道峭壁坑坑洼洼,潮乎乎一片,头顶上几乎只能看见一线天;远处只是这片弯曲的大地牢的延伸罢了;另一个方向上,近处只见一片模糊的暗红色灯光,照着一条更黑的隧道入口。在这庞大的建筑体中,充满了野蛮、压抑和禁忌的气氛。几乎一点阳光也透不进来,里面充满了死寂的灰土味;寒风凛凛,横冲直闯,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只感觉离开了人间。
他还未及反应,我已经到了他身边,几乎可以触到他了。他的眼睛却一动不动,此时四目相望,不由得朝后退了一步,抬出一只手来。
这个孤零零的岗位实在不是人待的啊(我这样认为),我站在远处往下看时,就已经被这迷住了。这地方应该人迹罕至吧,我想,而且恐怕没人愿意来吧?对我而言,我只看到一个人一辈子被囿于弹丸之地,而且最终获得了解脱,对这巨大建筑体产生了超然的兴趣。抱着这样的心思,我开始和他搭话,但却发现愈来愈词不达意。因为我并不乐于搭讪,而且这男人身上的某种气息令人生畏。
他只是盯着隧道口的暗红色灯光看,张望了良久,仿佛看到什么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然后才转头看我。
那片灯光也归他管吗?或许不是?
他低沉着嗓音答道:“难道你不知道它吗?”
一个诡异的念头浮过我脑际,我只是仔细看着他僵直的眼神,冷峻的脸,仿佛这不是人,而是一个魅影。那时我就揣摩,是否他脑子受过什么刺激。
该我说了,我也不由退了一步。后退时,我发觉他眼里似乎对我带着一丝畏惧。
这倒打消了我那个诡异的念头。
“你在看我,”我说着,勉强挤出一丝笑,“你好像有点怕我。”
“我只是怀疑,”他答道,“我以前是否见过你。”
“哪里?”
他却指着那盏他一直在看的红灯。
“那里?”我问道。
他便凝视着我,回答道(却没有声音):“是的。”
“老兄呵,我在那里干什么?好吧,就算如此吧,我真的从没去过那里。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想是的。”他重复道,“我非常确定,我发誓。”
他长舒一口气,我也平静下来。他的应答非常机警,话语也很伶俐。他在那边有很多事要做吗?嗯,就是说他职责压力很大。而且工作要求他必须精准和警觉,至于实际工作——体力劳动——基本没有。他必须时刻准备着完成这些工作:变换信号;调整灯光;还必须时不时地转动铁柄放车辆通行。谈到那些漫长而又孤寂的时光——我似乎言过其实了——他只是说,这种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已经自成一套形式,他只要逐渐去适应就行了。在这下面,他还自学了一种语言,都是通过观看来学习的,而且对它的读法,他还粗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可以说学有小成。对分数和小数也有所涉猎,也学过一些代数;但是,他自小就对数字不在行。难道他值班时只能待在这潮湿的隧道里吗?不能到峭壁之间去晒点太阳吗?这倒没那么绝对,得看具体时间和情况。有些情况下,道上的车会比其他时候少,日间和晚间的某些时候就是如此。天气晴朗时,他可以找机会站到太阳晒得低的地方;但是,总是不到一会儿就有电铃叫他,听电铃的焦虑倒是加倍了,所以那点安慰实际比我想的还要少。
他便把我带到信号所里,屋里有一个火炉,一张办公登记用的书桌,一架带转盘、纸条盘和印码针的电报机,还有他提过的那只小铃。
见我开始信赖他,他便不再含蓄,说自己受过良好教育——我希望这样说没有冒犯他——应该有更好的位置。他发现,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要找到一个不屈才的例子实在是稀罕事。他听说在济贫院,在警察机关,乃至那种求才若渴的地方——军队里,这种情况都存在;至于这种大型铁路机构,屈才之事有多少都是常事。他又说,他年轻时还是个喜欢自然科学的学生(坐在这样的小屋里,要我相信他的话,几乎不可能),还参加过讲演,但后来都荒废了,浪费光阴,终于成绩下滑,一塌糊涂。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那事情都是他做的,苦果也就自己吃。
想从头来过已经太晚了。
他说这些时非常平静,就坐在火炉那边,带着一种阴郁的神情向我点点头。他不时说一句“先生”,尤其说到自己年轻时,仿佛尽力要我明白,他其实别无所求,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了。中间几次被铃声打断,他只得读出信息,发报回复。一次,他必须站在门外,展开小旗,和司机打旗语,等火车通过。撇开他的职责不说,我发现他的动作非常精准警觉,可以突然打住谈话的某个音节,保持沉默,直到工作完成为止。
总之,我应该说,雇这样保险的人做这种工作实在最好不过了,只是他两次突然中断和我的谈话,面如死灰,转面看那个小铃铛——虽然并没有响——并且打开小屋门(屋门常关是为了挡避寒气),张望隧道口那盏红灯。他两次回到火炉边时,都带着我先前说过的那种莫名的气息,只是我们坐得太远,实在难以言表。
我一边起身要走,一边说道:“你真是我见过最知足常乐的人。”
(我恐怕要承认,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引他说话。)“我想过去是吧,”他回答道,却又像第一次那样低沉着嗓音,“现在却有苦恼了,先生,真是苦恼不堪。”
他很容易打住这些话的,所以他一说完我就赶紧接上了。
“为什么?有什么苦恼?”
“这实在难说啊,先生。非常难说出口。你要是改天来看我,我试着告诉你。”
“我倒是乐意之至,但不知什么时候方便?”
“我早上下晚班,要到明晚十点再上班,先生。”
“那我十一点来吧。”
他谢了我,便和我一道走出门来。“我会亮白灯,先生,”他用惯有的低沉嗓音说道,“直到你找到路过来。到时你不要再喊了!在崖壁顶上时,千万不要喊!”
他郑重其事,我却感觉这地方变得更冷了,便不再多说话,只说了句“很好”。
“那你明晚下来保证不要再喊!我再问一个问题,今晚上你为什么要喊‘喂!下面的人!’?”
“天知道,”我说,“我大概是这样喊的吧——”
“不是大概,先生。就是这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就算是这两句吧。我说过了,是的,因为我看见你在下面。”
“没别的理由吗?”
“我还会有别的什么理由吗?”
“你不觉得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暗示你吗?”
“不。”
他便和我道了晚安,举起他的灯照路。我沿着铁轨线下行一边走(感觉似乎有列车正从我背后开过来),直到上了小道。上山比下山容易多了,我安全地回到了小旅馆。
第二天晚上,我准时赴约,远处钟声刚敲了十一点,我已到了“之”形小道的豁口处。他正亮着白灯,在谷底等我。“我没喊,”我走到很近时才说,“现在可以说话了吗?”“洗耳恭听,先生。”“那就打个招呼,晚上好。”“你也晚上好,先生。”说着我们并肩走到了信号所,进了屋,关上门,都坐在炉边烤火。
“我已经想好了,先生,”我们刚坐好,他就向前倾着身,用比耳语大一点的声音说道,“你不必再问我一遍有什么苦恼缠身了。昨晚我把你当成其他人了。麻烦就是这个。”
“误会?”
“不。我以为是其他人。”
“是谁?”
“我不知道。”
“像我?”
“也不知道。我根本没见过脸。因为它左臂挡住了脸,右臂挥舞不停。就像这样。”
我看他做动作,却像是一种手势语,充满激情,十分猛烈,“拜托,天啊,快闪开啊!”
“那晚上月光皎洁,”他说,“我也是坐在这里,突然听见一声尖叫:‘喂!下面的人!’我惊了一跳,便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个人站在隧道口的红灯边,就像我刚才那样挥舞着手臂。那声音嘶哑了似的,大声喊,‘当心!当心!’,又喊,‘喂!下面的人!当心!’我便抓着我的灯,扭成红色,朝那个身影跑过去,一边叫,‘怎么了?有什么事?哪里?’只见它站在那黑乎乎的隧洞外面。我跑得很近了,但还是看不清,真纳闷儿它为何老用袖子挡着脸。我便几步跑过去,伸手拉开它的袖子,它就消失了。”
“进了隧道吗?”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