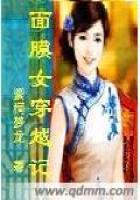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曹植《洛神赋》
隔天醒来,齐彦民就不见了。被子上隐约有残余的温热。赵爰清轻轻摸着。昨晚喝了药,又出一身汗,病真是好了大半。
太医开了方子,她吃了两日,但齐彦铭没再来过。说不出难过还是不舍,只是空空的罢了。
而楼惠妃的乞巧宴,照着时间,踏然而至。
酿造局里外忙着,宫人进进出出,楼素带了人来,赵爰清搁下验到半当口的酒,到门外迎她,“素姑姑,您亲自过来,可是惠妃娘娘有何吩咐?”
“大人给皇后的酒是否备好了?”楼素望向桌上十几只银色镂纹酒壶,皱起眉头,“这么多放在一道儿,大人可别弄混了。”
“姑姑请放心。”赵爰清拿起一只,指着壶面的花纹,“您看,这上头刻着凤凰,是专程给皇后的,就这一只,出不了岔子。而这镂牡丹的,是夫人和娘娘的。其余的贵人、才人,统一用普通酒壶。”
“恩。”楼素接过酒壶,递给身旁的宫人,她掀开盖子,细细闻了闻,又拿小银杯倒了些尝尝。楼素边看,边解释道,“赵大人,娘娘没有旁的意思,只是想确认一下。还请您别多想。”
“不会。”赵爰清由她试完,将酒壶重新放回桌上,“这位姑娘,本座酿的酒可有问题?”
“大人说笑了,您身为我朝四品酒正,奴婢怎么敢怀疑您的酒有问题呢?”说着和楼素交换眼神,“时候不早了,奴婢送大人去太医那儿吧。”
“也好。”赵爰清令以木拿来托盘,将酒壶挨个放上去,由五六个宫人端着,一道朝外走。楼惠妃终究对她不够放心,还找宫人全程瞧着。赵爰清笑着,但眼里满是嘲讽。
离太医处仍有一段距离时,楼素她们不便继续跟着,赵爰清径自走到前头等着。身旁有膳房的宫人分别端着奶白杏仁,柿霜软糖,玫瑰凉糕等点心。
“这是各位娘娘的玫瑰凉糕?”赵爰清狐疑地看向那叠格格不入的绿豆凉糕,“为何有盘不一样的?”
“回大人的话,沁夫人用不惯玫瑰凉糕,是以换了绿豆。”小宫女低着头回话。
“恩。”赵爰清不由得想到另一个人,刚巧队伍轮到她们,将她的思绪打断。那太医认真验了一番,又经食夫尝过后放她们进去。
夕阳已逝,华灯初上。舞姬在一片袅袅琴音,管弦声中挥着彩色水袖,身姿曼妙。宴会上有夜来浮香,每桌都用乳白色瓷瓶养一支莲荷,或是淡黄或为嫩粉。
无论从哪处看,都能觉察出主办者的用心。
“微臣给给位娘娘请安。”
“赵大人请起。”楼惠妃搁下玉筷,转头对皇后道,“娘娘,酒正手艺好。我专程托她酿了洛神花酒,养颜益容,温和滋补。还愿娘娘同‘洛神’一般,才德双馨,艳冠后宫。”
“你费心了。”这是重生后与沈月然第一次碰面,赵爰清心里虚着,她跟前世没太多变化,妆容简约,却不失大气;服饰素雅,却端庄得体,好像生来就该母仪天下的。
“姐姐忙着照顾临淄侯,分不开心神。妹妹能替姐姐做些小事,也是妹妹的福气。”楼惠妃转而问道,“不知侯爷现下如何,身子可好一些?”
“托惠妃妹妹的福,差不多痊愈了。太医说过上几日,就可照常习武。”说起沈鸢然,沈月然的眸光不自觉地柔和了许多。
“那就好。临淄侯是国之栋梁,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楼惠妃对面坐了王沁,她像嘲讽一般,轻轻哼上一声。也是赵爰清离得近,这才听见了。楼惠妃仍在同皇后叨着,“并非妹妹多事,只是想替姐姐分忧。这大丈夫,建功立业、四方奔走固然重要,但到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临淄侯整日刀光剑影中来去,还是早日成家来得稳妥,一方面后嗣得继,另一方面,有个贴心的人伺候着,也不必事事劳烦姐姐了。这乞巧宴上,有不少京中未嫁的良家姑娘,妹妹特意递了帖子,邀临淄侯来看看,没准能碰上合眼的,也算促成一桩好事。姐姐,您说是吗?”
“是,是啊……。”沈月然说着清淡,没泄出半分情绪。
楼惠妃听了,笑意更深,“说了这会子话,害赵大人干站许久。你快给皇后娘娘尝尝这洛神花酒的滋味。”
“是。”以木端着托盘跟在她身后,赵爰清拿起酒壶,轻轻放在皇后面前。皇后侧首,冲她浅浅一笑,平淡谦和,“多谢大人。”
“替娘娘做事,是微臣应尽之责。实在不敢当一个谢字。”赵爰清深深地看着她,随后起身退下,又给楼惠妃、沁夫人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