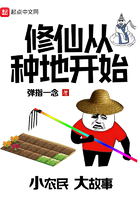按照普遍的说法,崔健出现之前的中国摇滚还是漫漫黑夜。既然是黑夜,那就应该赞美,因为黑夜里埋藏了无限的生机。在70年代末TheBeatles被少数几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摇滚乐还连噪音都不是,但到了1984年的"七合板",刘元就已经写出了《GoAway》这样冲动朴素的作品;1986年马克西姆餐厅为崔健提供了演唱《一无所有》的机会,到了1989年,北京的Party主办者付给乐手的酬劳就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平均每人一两百元,这是不是证明了中国摇滚十年的徒劳啊--但黑夜的美好之处在于纯洁,那些今天被无情挖苦、耻笑的名字,那些因为缺少才华又无法超越名利而堕落的名字,在当年都是理想主义的最完美化身。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梦寻--中国摇滚乐实录》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今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僵死于名誉的巅峰,但如果没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没有第一代摇滚人的饥饿、啜泣、辞职、昏迷、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亲爱的人,这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动力",就像90年代初的动力是颓废、现在的动力是个人创造。将来的动力是娱乐一样,典型的中国特色,带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伴随启蒙主义思潮,跃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峰。
在80年代,摇滚乐还没有基本的商业土壤,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正派、崇高的精神背景,摇滚乐根本就没有力量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那时候,"唐朝"老五背床板的故事、王迪和丁武画风筝的故事,和更多故事一样,不仅传奇得可歌可泣,更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全国摇滚乐手的志向。
1985年,崔健写出了《不是我不明白》(后来作为电影《顽主》的插曲出现,成了第一首触电的摇滚乐作品),有趣的是,这首歌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节奏布鲁斯形式,倒是以Rap的面目出现,像是预示着崔健那一代音乐家后来对黑人音乐和技术的着迷。随之而来的,当然是1986年的《一无所有》,第二届百名歌星大合唱活动让崔健登上主流舞台,当然,这首歌的最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流行歌坛的"西北风"潮流,王迪、孙国庆、井冈山、田震等缺乏创作能力的阳刚形歌手是最大的受益者。《一无所有》当然也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精神的尊严,而不是生理的愉悦或艺术的先锋开创了中国摇滚。接下来,崔健两进北大,1988年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被看作他的、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场正规演出。
早在摇滚被公开之前,1979年成立的"万里马王"(老哥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成立的"大陆"(第一支老外乐队,著名的吉他手艾迪就在其中)、1984年的"不倒翁"和"七合板"、1987年成立的"ADO"已经用翻唱流行、民谣、乡村、软摇滚和老摇滚作品来让北京的耳朵变得西化了。臧天朔、王迪、孙国庆、秦琦、丁武、张永光等人就是那时侯踏上音乐不归路的。一直到1988年"萤火虫"("零点"的前辈、广州"新空气"的同事、伴奏界的名人)的组建,期间"白天使"、"五月天"、"DADADA"等乐队也擦上了摇滚的边,而1987年组建的"黑豹"和"宝贝兄弟"(常宽、陈劲、张卫宁、赵牧羊)则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摇滚乐队。那些最早参与乐队活动的青年,现在统统被当作摇滚前辈,而不只是音乐前辈,这是因为,相对于历史,他们做了叛逆的事;相对于音乐,他们担当了英雄的角色。
当然,在电声的背后,木吉他对这个社会的解放要广泛得多。1972年开始学习吉他的曹平有资格说明这一点。他从广州的业余吉他演奏者,到北京的摇滚战士和后来的传播者,见证了吉他文化为摇滚乐铺开的路基。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吉他热,和大学里的读书热、参政热一起,真正让青年成为青年,他们第一次成为拥有自己的特征的群体,并且开始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民间、青年、群众--中国摇滚只有在这一点上是和欧美国家相似的。如今"超载"又卸载的高旗,就是在1985年参加吉他比赛时认识曹平、曹钧兄弟的。不过,几个乐手的成果,远远比不上吉他对青年--摇滚乐基本受众--的培养更伟大。
受众眼里的早期摇滚,是战士和天使,是殉难记和侠客行,这也是第二代摇滚人喜欢打扮成美国硬摇滚商业明星模样的原因。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幼稚,这没什么。不过,这种神话倾向的另一面却是,摇滚生活的中国特色。广州的摇滚翻唱者们还在歌厅里跑场子的时候,北京的战士们创造了一种绝对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自从1984年国际俱乐部开始为"大陆"乐队举办Party以来,各大宾馆的Party成为了中国摇滚最早的温床,其中尤以马克西姆、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地更为知名。到80年代末期,观众和主办人渐渐以中国人为主时,却又变成了艺术、文化圈里一种最新的时尚,对有的人来说,去看摇滚乐Party和参加贴面舞会是同样刺激的圈中乐事。这种边缘化是非常奇怪的,它没有让摇滚乐真正从社会底层产生对抗,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建立了贵族化的风景。在大众那里,摇滚乐是没有身体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社会应有的基础;在圈子里,摇滚乐是远离主流的另一个中心、边缘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群众娱乐、群众文化的迹象。后来,"呼吸"、"眼镜蛇"这些毫无音乐价值的乐队奇迹般地出现,和他们所依赖的传媒优势、话语强势是分不开的。
中国摇滚的神话效益让它在"石头"上生长到了90年代,其负面效益就是:时至今日,神话、仪式化、文学化、浪漫主义的目光仍然笼罩着它,盲目的热爱让新的孩子失去着独立的思维和感觉。当年的启蒙和解放,今天已经变成了新的枷锁。
1989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无疑是值得一再研究的。摇滚乐从这里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年,并且艰难地摆脱了80年代的贫瘠、理想和幼稚。而青年的性格也好像突然成熟,从单纯的浪漫,进入务实、甚至实用主义的理智之年。
在美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下,我们进入了1989年。这一年是北京摇滚Party最热闹的阶段,李季在这一年由摇滚实践者变成了忙碌的Party主办人,"星光"的Party尤其令人怀念。"面孔"、"TOTO"、"唐朝"、"眼镜蛇"、"呼吸"、与侯牧人合作的"现代人"、"青铜器"、"1989"也都是这一年组建的。西三旗宾馆最初的摇滚群落(一个短暂的乌托邦社群,反映出摇滚的理想本质)、资讯的膨胀、收入的增加、老外的热情,使得摇滚风景成型;借助1988年以来全社会的热情、激进、开放和严肃的面貌,摇滚乐当然也有了蒸蒸日上的样子。除了1988年组建的"清醒"似乎在追求空灵,其他的乐队几乎都走上了高大、膨胀的路线;成功者如"唐朝",在1992年12月发行的专辑《梦回唐朝》中一次性用完了中国摇滚所有的大气和豪情;失败者如"呼吸",1989年录制、1992年发行的专辑《太阳升》已经成为晚会式假、大、空音乐的代名词。
在社会动荡之际,音乐家们的灵魂深处当然也颇有得失,个人生活的变动、演出环境的变动,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他们。众所周知,"唐朝"《太阳》的创作就和丁武的新疆之行有关。有的乐队解散了,有的人却因为对现实失去兴趣而投身于此。集体理想的迅速流失、对社会的热情关注、向自我的迅速撤退,大家都是如此,摇滚乐的位置也就变成了一种逃避之门。当然,首先,它的前景也和其他青年文化在1983、1987年的遭遇一样,变得委屈和黯淡。大家都开始灰头土脸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摇滚乐的众多误会之一:它在中国竟然被看作先锋艺术并冠以前卫、实验的名字,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没有青年的概念和实体,作为非阶层化的青年的产生、成长必然要遭遇社会的考验;在考验中,青年文化的确有广义的"前卫"涵义,但迟早会在商业社会中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要不要改变、做什么、为什么做,是这些没有单位也没有前例可循的浪子要思考的""至于更多,不说也罢。
青年的变化有如电光石火,所有的虚妄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大学生和摇滚乐的感情,也是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3月的"现代艺术大展"把前卫艺术的炸弹掷向了公众,摇滚乐的前卫已经算不上可怕,一种年轻的气质鼓励了摇滚乐和自由主义的联合,"北京大学崔健后援会"甚至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没有基础的浪漫里,人们对摇滚乐的信任盲目增长,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青春岁月。在全国各地,任何人只要使用电声乐器和架子鼓,就会引来不多但绝对热烈的支持,那些在舞厅里伴奏的乐手,很快有了类似地下音乐家的身份。后来,在狂欢的气氛中,大家发现了不插电的、类似集会上的BobDylan的情形,青年和摇滚乐一起体验着集体浪漫的巅峰,大家一样不现实、一样有责任感、一样热情。然后,青年回到现实中去,埋头苦干,抛弃了好奇心、热情和别的;摇滚乐则没有什么务实的去处,孤独地飞了,只好加倍地陷入空虚,要么向后来的颓废滑动,要么向美好的幻境狂奔--众所周知,摇滚乐务实,只能意味着批判或娱乐,这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高潮像回光返照一样,用完了大学生,也是青年对摇滚乐最后的狂热。大起大落的变迁,印证着社会运动--而不是艺术--的规律,迟早要让摇滚乐从精英手中移交到大众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