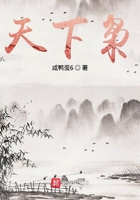吱吱嘎嘎,马车富有节奏的咿呀声划过了清晨的白露,在山间留下一道车辙。
李文此时正坐在一辆马车上,马车里很拥挤,因为马车上不只有李文一人,李大、张初蝶此时此刻都坐在马车上,而在赶着马车的也不是别人,正在前几日一直在城门口说书的张铁嘴。
如果非要问张铁嘴为什么在为李文赶车,那就要从两日之前的一桌酒宴说起。
“你为什么找我?”张铁嘴紧拧着眉毛直视着坐在酒桌对面的李文,似乎要透过李文的黑色瞳孔将他整个人看透,他面前的这个少年似乎笑的太过漂亮了。
没错,就是漂亮,虽然这通常是一个用来形容小姑娘的词汇,但用来形容李文却丝毫不为过,穿着一袭青衫的李文笑的太过干净,同时也太过安静,太过别有意味。
李文怡然自得的用筷子夹起了酒桌上的小菜,浑然不觉的将小菜送入口中,平和一笑,道:“除了你,我实在想不到别人,虽然我之前有一些朋友,但你懂的,都是架鹰走狗的朋友,我不能去找他们。”
张铁嘴没有吃菜,相比酒肆里桌子上的几样小菜,他更喜欢李文点的那壶酒,单单这壶酒就值一百二十文,比桌上的菜还要贵。
张铁嘴像地痞无赖一样将杯子里的酒贪婪一饮而尽,随后回味了片刻,如流氓般明确表示无能为力道:“李公子你不知道,虽然我是张村的人,但我已经出来三年了,这三年我一直都在城里说书,一次也没有回过,况且村里的事都是由村长和粮长说的算,说实话,我帮不上你什么。”
李文淡淡一笑,随后摇了摇头,完全不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道:“我回去只是看看我家里的地,催一催租子,不用你帮我什么,你也看见了,我年纪小,份量还不够,所以你只要陪我去张村就行,催租的事我自己来做。”
李文将右手摸入怀中,从里面拿出一个包裹,平坦放在桌上,将筹码一压而尽,温和一笑道:“陪我去张村,回来后,这些就是你的了。”
张铁嘴皱了皱眉,因为最开始,他以为包裹里的是钱,但随后他就发现,包裹里面的并不是此次的酬金,因为纸钞并不会那么被摆放的方正整齐,于是张铁嘴打开了包裹,包裹里不是别的,是一沓厚厚的书稿,字有些歪歪扭扭,但大体还算整齐。
“什么时候出发?”张铁嘴在一目十行的看了书稿的前十页后才恋恋不舍的放下书稿,像个饿狼径直看着李文向李文问道,仿佛此时真正应该焦急的人是张铁嘴。
“两天后。”李文淡淡回道。
张铁嘴又喝了一杯酒壶里的酒,有些捉摸不透的看着李文,一阵狐疑,脸上好奇的问道:“这些?都是你写的?”
李文点了点头,似是而非的胡诌道:“我小时遇到过一个游方道人,我施舍了一碗粥,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张铁嘴脸上立时一阵恍然而悟,连忙接着问道:“那他说他叫什么了么?”
“他说他叫王重阳。”李文低头吃了一口菜,眼神闪烁一下。
“噢···”张铁嘴慎重的点了点头,用心的翻了翻书稿,似乎要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于是,两天后的一个早上,李文带着李大上了张铁嘴租来了一辆马车,而张初蝶则作为书稿的保管人寸步不离的跟着李文,一有时间就去读那本《济公传》的书稿,生怕书稿在被自己读完之前就移交给了面相有些猥琐的张铁嘴。
“张先生,咱们是么时候才能到张村?”李文坐在马车里,向马车外面驾车的张铁嘴问道。
张铁嘴朗声笑了笑,一个上午过去了,他和李文在已经变得熟络起来,道:“李公子,你就不要叫我张先生了,叫我的本名张新岩就行,张村虽然距县城只有三十里,但却在莽苍山山脚,路不好走,要明晚才能到。”
“原来是这样。”李文在车内点了点头,脸上显得有些慎重,不知在想些什么。
“公子,咱们这回为什么要张村?”李大坐在车内看着李文好奇问道。
因为需要人手的缘故,所以李文这次把李大也呆在了身边,毕竟李文自身也刚刚及冠,有些事情一个人是办不来的。
李文看了一眼坐在车厢内穿着道士服安静看书的张初蝶还有身边的李大,脸上转而笑了笑,道:“老张今年没来咱家送米,所以我要去张村看看他。”
“那少爷你为什么亲自去呀?让福伯去不好么?”李大像个小跟班一样坐在李文身边,想李文好奇的问道,在李大眼里,除了老爷李双之外,李文无疑是李家最富有权威的一个人,像吃米和看望老张这等琐碎事,远远不用李文去担心。毕竟,李大从小就是李家的仆人,从小就是李文的书童。
李文摇了摇头耐心的解释说道:“福伯要照顾祖母,走不开,而且,土地不算小事,汉朝的汉景帝就说过:夫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这里的‘农’说的就是田地,咱们李家要是没有这十亩田,凭着我父亲的那点俸禄,恐怕要吃不饱了。”
李大一听说要吃不饱了,脸上也不禁惶恐了霎那,连忙道:“原来田地竟然这么重要,怪不得城里的那些老爷们都那么有钱了还总是去买田,公子你知道可真多。”
李文再次摇头笑了笑,说道:“话也不可以这么说,土地也仅仅是温饱而已,要想活的舒服一些还是要去经商,别的不说,单单咱们大明最普通的丝绸卖到南洋一匹就可以赚几十两银子,就连咱们庆阳的小麦卖到泉州,价格都可以涨上五六倍,正所谓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无工不活,无才不兴,就是这个道理。”
听完李文说的这些话,李大连连点头。
“哼,商乃贱业,经商有什么好的,弄不好连家谱和祠堂都进不去。李大,不要听他骗你!”
正在这时,只听张初蝶一边看着《济公传》的手稿一边小声嘟囔着说道,明显,刚刚李文的话她已经一句不落的听了过去。
李文转过头看着张初蝶也是一阵无奈,今早是她非要跟过来,现在她竟然还教唆起李大,张初碟对于李文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家伙。
“你凭什么说经商是贱业。”李文看着张初蝶一脸不爽的向她问道,脸上表现得有些阴沉。
“商人为什么不是贱业?”张初蝶撅起小嘴,一脸较真的模样看着李文说道:“士农工商,商居最末,当然是贱业,而且商人不事生产却积贮倍息,坐列贩卖,以有易无,市贱鬻贵,不是贱业是什么?”
“没想到你一个小道士懂得还挺多。”李文不屑一笑,随后说道:“但你也仅仅是看到了表面,还以有易无,说的还像是有几分道理,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商人的话,你现在连这身道袍都穿不上,你的道袍还不是从布商哪里买来的。”
张初蝶听李文这么一说,不由得微愠,两条弯弯的柳叶眉蹙了起来,看着李文据理力争说道:“你这是强词夺理,商人不事生产,与民争利,这是事实!”
“所以说小道童你的修为还太浅。”李文轻哼了一声,玩味一笑,道:“商人买进卖出,看似不事生产,但却是在互通有无,现在假设说咱们三人中我是商人,我有三钱银子,而李大有五钱银子,我将一匹布用三钱银子从你这里买入又用五钱银子卖给李大,那你说咱们三个人一共有几钱银子?”
张初蝶想也不想就马上带着不屑的答道:“自然是还是八钱银子,你有五钱,我有三钱,你这些鬼蜮伎俩是骗不到我的。”
“错!大错特错!”李文摇着头故意说的一字一顿,说道:“是一两三钱。”
“怎么会!”张初蝶马上对李文露出一副怀疑的表情,刻意强调说道:“分明就是五钱银子!”
“是一两三钱。”李文仔细解释道:“那匹布原本值三钱银子,但经过我买入卖出后就值五钱银子,李大的布值五钱银子,我有五钱银子,你有三钱银子,加在一起一共是一两三钱。”
张初蝶的脸上露出了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随后马上就反驳说道:“布怎么能算是银子!”
李文神秘一笑,道:“布当然不能算是银子,但经过我这个商人的买入卖出后自然不一样,那匹布在我过手后就值五钱银子!别忘了,在咱们三个之中只有我是商人,如果我不买你的布,那你的布就一钱银子都不值,只能穿在身上,而在我买入卖出后,布就是银子,银子就是布。”
“你······”张初蝶还想反驳,但一瞬间却不知说什么好,红着脸狡辩说道:“就算你说得对那又怎样。”
李文笑了笑说道:“不能怎样,只不过商人确实增加了社会总财富而已,商人并不是贱业,佛陀不是也曾说过么,众生平等,何必一定要分个高低。”
张初蝶看着身边还懵懵懂的李大,脸上不由一阵羞红,她虽然听不懂李文所说的社会总财富是什么意思,但李文所说的大致道理她却明白了,如果没有商人,布只能穿在身上,有了商人后,布就可以换成银子,银子就是布。虽然她不想承认,但无疑李文所说的没错。
“那为什么士农工商里面商居最末?”张初蝶红着脸颊开口向李文蚊声问道,算是承认了李文。
令李文和张初蝶大吃一惊的是,李文竟然漫不经心的笑着回道:“因为圣贤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孔子不也是遇到过两小儿辩日不能决么?尽信书不如无书,圣贤虽然站在神台上,但终究也是人呀,人谁无过呢?”
马车吱吱嘎嘎的走了整整一天,车厢也跟着摇晃了一整天,在天色渐晚时才到达了一座破庙,张初蝶倒还好些,李文和李大在下了车后就有些吃不消了,感觉整个身子都在晃,李文更是觉得整个身子好像都要散架,比什么长途汽车都让人吃不消。
张村不远,距离庆阳不过三十里,但路却不大好走,十五里的崎岖小路李文一行人走了一整天,据张新岩也就是张铁嘴说,明日的十五里路更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