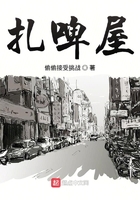下午六点该下班时,贾主席还没想着下班。对于他来说,这种情况,一年有两三次。平时他是个准时下班的人。
戴上那顶洗的发白的有着半圆帽沿的帽子,他急急忙忙往炉前走。他想看看红枫练的怎么样了。他惦记着岳红枫,却不想在上班时间去看红枫练车,生怕被人看见。这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连他自己都觉得太谨慎小气了。他觉得自己有点老了,尽量想的周到些,尽量不得罪人。尤其是,付主任可能到站了,自己跟他搭班子这么多年,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太势利。
贾主席从造型工段的北厂房门进去,经过满地排练整齐的各种沙箱,借着厂房内预留的微弱灯光,自言自语:“这几个摇臂,可是干的好咧。”
“干的好了?那还不是领导们指挥的好。”突然,有人从侧面堆成一人高的沙箱后面闪出来。贾主席吓一跳。
傍晚以后的造型工段,如果没有浇筑的铸件活儿,平时基本上是清净的。空旷的一眼看不清尽头的厂房里,白天热闹嘈杂的翻沙和造型工作场面,只留下一块块或大或小的造型模具。模具上平展展的,像一块块整齐的梯田。这些梯田上冒着袅袅烟雾。几块高高的玻璃窗上,微弱的灰蓝色夜空,显得若有若无,仿佛根本不存在。其实,大工厂的日夜交替,本来就是模糊的。自解放以来,这座号称要建设成煤炭重化工基地的省会城市,在城市的边缘,也就是当时的城乡结合地带,日夜不停地排放着工业浓烟和废气,同时,也不分昼夜地将城市上空渲染成五彩斑斓的美妙图画。像岳红枫的父亲所在的钢厂,大型钢炉出钢时染红半边夜空的壮丽景象,总能激发出人们无限的向往。而它们的魅力,不仅仅是横跨几个街道的,独立成一个大型社会的围墙加大型厂房,加医院中小学的有型地面综合体。同时,动辄上万人的职工队伍,和那些每天从城市的一头,骑着车子奔向另一头大工厂的人们,他们每天对大工厂的憧憬,就像向往一场美妙的春节盛宴一样,每天都充满着信心。
从沙箱一侧出来的是老鬼,贾主席惊讶道:“唉,你怎么在这呢?”
老鬼指一下身后,笑着对贾主席说:“唉,这不是,有一个钢包,白天浇铸完后,因为高车机械故障,不动了,就把钢包扔到这了。我换换砖。”
“我说么,咋跑到造型上了……那该下班了吧?”贾主席想走开,他惦记着炉前的事。老鬼似乎有心事,做出想聊天的样子,把手里砌砖的刀放下,摘下手套,说:“唉,贾主席,你真是个好领导,下班了还不走。”
贾主席客气道:“唉,这不是,马上要技术比武了,事情比较多。你也该回家了吧?”
老鬼却答非所问,问贾主席:“贾主席,你家每天吃啥?”
贾主席一愣,笑笑:“那能吃啥?还不是面,馒头。你不一样?”他心里急,心里嘀咕,老鬼这是咋了?突然问开这了。
老鬼主动说:“我?我在家,每天就是一碗面,一根烟。”
贾主席呵呵笑着,嗓子里嗯嗯,望望四周,高大的灰砖墙上,积满陈旧的灰尘,灰暗连接着一处处污渍和钢水飞溅的凹坑,有点像枪弹留下的痕迹。铸造车间厂房是由解放前旧军阀的军工厂所建,在解放后国营企业职工们的手里,这里被几代人维护使用着,而且越来越有感情了。贾主席想到这里,心里一热,他能猜到老鬼想说啥。老鬼家孩子多,就他一人上班,年年想吃救济。其实,每年救济就四五十块,一年才四五十块,可对于老鬼家来说,可以抵挡一年的困难。老鬼经常不分白班夜班,加班是常事,他如此肯干的内心想法,也许只有贾主席更清楚。老鬼工作积极,对吃救济也格外积极。有人说,老鬼为救济奋斗。动机不纯,所以评不上生产积极分子。可贾主席台了解他了,他不去争取一年一次的救济,他的四五个孩子就要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