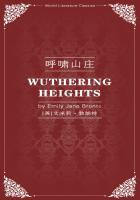是求生的本能救了裴思格,她双手死死抓住坝沿突出的石头,挣扎着并努力昂起头,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惊恐的甄伍。那一秒,甄伍是邪恶的,只要他伸脚猛踩她的双手……或者什么也不用做,她也没有能力自己爬上来……整个坝身足有50米高……但也就在那一秒,他脑袋里浮现了另一幕……
甄伍与美鹃走到一起后,裴思格再也不便踏进甄伍的家,她是个通世故的女人,绝不愿成为别人婚姻里的障碍,因为她原本要的也就不是婚姻。但人非草木,要说她对甄伍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也是冤枉了她,甄伍当时三番五次催促她速来取走自己的物品,可她总是推三阻四,拖泥带水。今天取走一件衣服,明天再带走一瓶洗发水,到最后还是剩下一大堆东西不肯来拿。甄伍是扔又扔不得,留又无处藏,最后索性全部打包塞进了美鹃爬着梯子也难够到的杂物顶橱里,久而久之以为她忘了。
可当甄伍为她买好了那所公寓后,她想起的第一件事却是当初遗落在甄伍家的那些物品,竟能精确地报出那些物品的名称与数量,她差甄伍帮她搬到新公寓里……这事终于让甄伍明白了这女人对自己的用心。她真的是舍不得离开他,即便人已离去,也要留下些东西象征着她的存在……
甄伍犹豫间探身向崖下伸出手……
启亮收到老婆的那条短信后开始坐立不安,近日总有末日来临的预感,他一个电话打到团险2部,请李群过来有事商量。
“你也晓得的,这两天股市在调整,你来看——”启亮打开了行情软件,屏幕上是一只跌得很绿很绿的个股,用启亮一贯的玩笑说法,简直就是“深绿”——他料定无人知晓他股票池里的构成,危言道:“现在抛掉,损失相当大,这个跟你讲实话——”只一闪,启亮便心虚地将K线图迅速切换成技术指标,“看见没?日线KDJ死叉未见底,周线却金叉形成突破,MACD还处于多头行情中,红柱还在,主力进出也还很活跃,这两天的量比和换手率也相当大,之前主力周线拉了旗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回调,只能算是技术性回档,形态上明显属于旗形整理,目前大盘还在大B浪的二浪初,没道理这时候撤出……”启亮竭尽全力向李群描绘着一幅光明前景,可李群显然已经很不耐烦了。
“邵经理,可能是我的话还不够透彻,这钱真的急用,片刻耽搁不得,损失也就顾不得了,回头您卖出之后,直接告诉我金额就OK了。”
“哦?这么急?难道是——帮客户洗钱出了问题?”启亮深谙团险业务的那点猫腻,二季度以来,大约有近半业务可被归入洗钱业务。
何谓“洗钱业务”?通常都是些来路不正的保费,比如各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小金库,有的甚至不惜专门成立空壳公司来洗,个险团做是普通手法,险种也通常选定为储值型、投资分红型,只要本金毫发无损,回报多少通常不被关心。个险做成了团单之后,虽然业务员佣金较之个险少了许多,但“客户利益”被最大限度保护了。到期后,那些团做的个险会以个体为单位返还至银行个人户头,竟还能免税……
这是一条化整为零,从不法来源洗成个人合法收入的完整通路,隐蔽性极好,只要保险公司的保密机制足够配合,资金肯定是安全的,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不同程度地操作着,彼此心照不宣。启亮情急中指望用这个来敲打李群,显然跟老婆下午犯了相同的错误。因为这在部门间也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毕竟那是系统问题。那系统就象是蜂巢,蜂后是利润,工蜂不过在拼命促成其最大化。洗钱?可从来没人会如此煞有介事地给此类“变通业务”上纲上线,保监委不遗余力下了12道金融内控金牌,“自查自纠”也都不知几轮了,可控不控则全然不是“外人”所能决定。
李群一听启亮提这事,顿时有些光火,道:“邵经理这话就有点不上路了,单子能做成,不经你核保这一关,契约部也出不了单啊,能出啥问题?真要出了问题,那就是一条链子全出问题,你邵经理恐怕也难独善其身,况且,这也不是你该关心的吧?!”李群一脸的飞扬跋扈。
业务员其实也就是在保险这种无本万利性质的企业中被奉为神明,如同空手套白狼,正因为“无本”与“空手”,才更显“套白狼”行为的伟大及技巧的高深。“客户是上帝”在他们内部又被分割为两段——客户是外勤的上帝,外勤又是内勤的上帝。外勤是全公司的衣食父母,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与客户签那一纸契约,保费才能源源不断地进帐。也正因签约过程十分艰辛,所以需要不断被激励,而非规范与约束,否则稍脆弱些的外勤会三天两头委屈地哭。仿佛保险公司的文化始终被浸泡在煽情的泪水中。
这种极度扭曲的内部关系,在特定的土壤中反倒成了合情合理,从上到下被高度认同,甚至推崇备至,也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如李群这般骄矜的“宠儿”。启亮平日里其实很看不惯他们团险业务部的人,尤其是这个李群,三天两头带些不三不四的哥们进公司,把个会客室当成吸烟室,弄得乌烟瘴气。但启亮从不敢公然与之为敌,眼下见他翻了矛枪,必须立即安抚。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别往心里去——放心吧,我马上办,下班前你到我这里来领钱。”
启亮预感中的末日终究要降临了……
从蔬果庄园回来的路上,是甄伍在开车,灰头土脸的裴思格坐在后排座上不住地抹泪。
美鹃发来了手机短信,“老公,我成功啦!明日下午到家,等我一起庆祝。”
报喜的短信,启亮的手机上也收到一条,他倒可以暗自庆幸逃过了一劫,可甄伍却不能,只淡然地回了一条,“收到。”
两人趁着夜色再次潜回甄伍家中,裴思格象一头受了惊的小鹿,一声不响,甄伍用冰冷的语气吩咐她去卫生间洗澡,自己却筋疲力尽倒进了沙发。裴思格很听话,去了。
20分钟后,卫生间的门开了。甄伍的家里早已没了裴思格的浴衣,她不敢让他取美鹃的给她穿,因为她明白此刻自己在这个男人眼中什么也不是。于是只裹了一条浴巾,光着脚丫,战战兢兢地从里面出来,洗净的脸上惊魂未定,却依然娇媚横生。甄伍对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真可谓爱恨交织。
晚饭也没吃,澡也没洗,甄伍便不管不顾进了卧室,灯也没开就往床上躺。裴思格在客厅里迟疑了片刻,也蹑手蹑脚跟了进来。甄伍其实很想听她解释,可又怕再听一遍那些可怖的事实,只能背转身去装睡,脑子却在飞快地运转。前晚对赵家父子所动的杀念,此刻再次浮现。屋内一片死寂,甄伍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床稍有晃动,他知道裴思格也上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黑暗中,甄伍感觉被她从身后轻柔地抱住,心稍有回暖,不再那么孤独,可却不想做任何肢体反应。
“阿伍——对不起——”
甄伍仍旧没有回应,心却软了下来。他相信裴思格不是有意要害他,否则不会带他去那种危险的地方,傻傻的以性命相要挟,这会也更没可能跟着自己回到这里,定是被那赵鸣给逼的。
“我晓得你恨死我了,我也恨我自己——可我也同样希望你能得到那笔钱,真的——”耳边还是裴思格柔弱的声音。
甄伍心想,这会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所有证据都在赵鸣手里攥着,那个混蛋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怜他的美鹃,刚看到一线曙光,这么快又要陷入绝望的黑暗中。
甄伍转过身来,右手穿过裴思格的湿发,将她揽入怀中,道:“算了,不讲了。”
说完心中竟泛起了一丝怜惜与负疚,在她的裸肩上轻抚了两下,毕竟下午她已受到了惩罚。其实那个惩罚本也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施加在她的身上,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阿伍,你有梦想么?你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甄伍不清楚她为何要问这个,不假思索道:“曾经有。”他忆起刚与美鹃结婚不久写在自己博客里的一首诗,噫呜道:“妻坐厅堂品佳肴,小儿穿廊戏家猫。恍如一夜白头翁,暑寒春秋不觉老——但现在——一切都破灭了——”
“那既然如此,能告诉我,你为啥最终会选择走这条路么?”
“哪条路?”甄伍这是在明知故问。
“就是诈保——与我有关么?是我给了你压力么?”
裴思格的聪明,就在于既能洞察男人的癖好与盲点,也完全摸得清他们的自尊与脆弱。可这一回,她显然又一次过高估量了自己的价值。
甄伍还是不想告诉她实情,叹息道:“唉——跟你有关怎样?无关又怎样?人生就是一场赌博,能把握的只不过是赌技,我有赌技却没赌运,就成了现在这样。”
“唉——那这回你可输惨了,应当讲,我们都输惨了——”接着是裴思格近乎央求的口吻,“阿伍,听我一句劝,认输吧,我们斗不过,先熬过这一关,我们还有将来。”
“嗯,不过——我有三个条件!”
“你讲讲看。”
“你回头去跟赵鸣讲——第一,只有350万,这350万当中,整头可以全拿走,给我留个零头——50万,假如连这点都不愿给,那就是在逼我走绝路,他们父子的好日子也就算到头了,黄泉路上我也要拉他们作伴——第二,启亮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告诉他,算盘打错了,假如我真有被捉牢的那一天,到死都只有一句供词——我没有同谋!包括你格格,也不是!所有事都是我一人策划和实施的,我要连帮我的人都保不住,那我甄伍也就跟他赵鸣一样猪狗不如了——第三,他必须亲自从我手里把300万现金取走,我不认可银行转帐,更不允许他把你当成运输工具。”
“哦——”裴思格犹豫地应着,似有担忧,大概是吃不准这三项条件赵鸣那头是否愿意接受。
但不管怎样,任务算是完成了一半,而且从这番话中体察到甄伍以往被她忽略的另一面——在她看来男人最可贵的品质——义气。她一直在心里如此评价一个男人:犯错未见得可憎,无论是哪类错,只要敢于承担后果,不推卸责任,那还算是可敬的男人。而那种耍无赖、不守信、懦弱且没有担当的男人才最令她厌恶……
她不由自主地抱紧了甄伍,想用体温去化解他的满腔仇恨。甄伍俯身去吻她,手也向浴巾下摸索进去。裴思格做着软弱无力的抵抗,口中仍喃喃臆语:“老实交代——下午——你是不是想——我死——”
“哪有——我救了你——”
“你就是——想我死——还不承认——”
“要死也是一起死——”
当甄伍撩开浴巾拨腿挺进时,裴思格已呻吟不止,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在床上疯狂地翻滚着……当双双于快乐的海洋中痉挛挣扎时,裴思格用臂死命钳住甄伍的颈,嘤嘤的哭出声来。甄伍清楚,这意味着真实的裴思格又返回了这躯壳,只有这一刻,这个女人才会卸下所有伪装,甘愿做几秒钟爱的奴隶。
裴思格脱下腕表,开灯去了卫生间,甄伍看到那块“真爱密码”此刻就躺在床头柜上,好奇心驱使他再一次去拨弄。上面显示的值高得吓人——9.8。这就对了,甄伍想,这足以证明她没有对自己撒谎……也由此心生一计。为了美鹃,为了自己,为了裴思格,也为了邵启亮,他不能如此束手就范,他要再博最后一次!
等裴思格从卫生间回来时,甄伍又一次拉她入怀,道:“格格,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哪怕是搭上我这条性命。”
裴思格沉浸在片刻的幸福中,“嗯,我相信!”
“我会把你从赵鸣手里解脱出来。”
裴思格一听这话,再度紧张起来,神经过敏般弹坐而起,道:“你又想哪能?你不要再乱来了啊——”
“你在紧张赵鸣么?”
“呸!那个垃圾男人,还不配——不是,我是怕你再为了我去做傻事——能用钱摆平的事,何必要搭上性命呢?破财消灾嘛,对不对?”
甄伍其实很想说,那些钱就已经是我的命了,但脱口时还是修饰了一下,道:“要知道,那些钱也是我用命换来的啊——其实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忍受不了你跟他在一道,受他摆布——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乱来——”
“那——你想做啥?”
“先前讲的那三个条件变一变,你告诉他,做人现实一点,亮亮不欠他什么,没理由,更拿不出150万,从头到尾都是我跟他之间的事,现在我答应把我的350万一分不少全给他,只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带你一道来跟我见面,时间地点我来定——他也不能空手来,带上一打啤酒,见面后我跟他一边喝酒一边数钱,酒喝完,钱数完,我们割袍断义,分道扬镳,从此永不相见。”
“真的假的?你究竟想做啥?你快告诉我啊——”
“你先别问了,我自有妙计,明天美鹃回来,我就不跟你见面了——后天吧,我发短信给你,我再出来一趟,交给你样东西……”
裴思格不再多问,享受着甄伍的怀抱。虽然这男人如今已面目全非,但令她重新审视他的绝不是那张动过刀子的脸,而是这个男人在一无所有、穷途末路时所体现出来的闪亮品质——无疑,他是个值得信赖的男人。裴思格的“爱情指数”在悄然升高,幸福感暗流潜涌。可她全然不知,这些都变成量化了的数值,早已被身边这个男人窥了个通透……
赵鸣一早从裴思格的公寓里出来,也去了一个地方,竟也是地产商马总那儿。马总既是他老爸赵宽佑的朋友,与他本人也已多年老交情了。当初甄伍公司的项目打包出售,就是赵鸣得知后为他们牵的线。
那已是甄伍公司最后一笔业务了,所以当时甄伍的合伙人王大老板不可能放过这最后的机会,事先找到赵鸣跟他商定,将项目价格尽可能压低了出手,堤内损失堤外补,从而确保他个人的资本回收。这实际上就是个跷跷板,王大老板减少损失的代价,就是包括甄伍在内的其他股东都扩大投资亏损。
这事赵鸣是绝对没兴趣跟甄伍合作的,因为他很了解甄伍这个人,视财如命。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无论是谁,一点不损失当然是不现实的,只能尽力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赵鸣想,即便出手帮了甄伍,也很难开口向一个亏损的人讨好处,何况还是多年好友。最终至多得到他一句轻描淡写的感谢,甚至可能连感谢都未必有。因为常挂在甄伍嘴边的一句话是——“帮朋友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用脚趾都能想见事后他会怎么讲——“大恩不言谢,统统给我记在感情帐上……”
当时王大老板深思熟虑后选定了甄伍这个“最佳人选”,全权委托他去参与谈判,事先给他设了个看不懂的底线。裴思格当然也起了些作用,作为总裁秘书,更作为赵鸣的内应,事前向甄伍提供了假行情,而后又在谈判桌上猛敲边鼓,最终促使甄伍这个自认为早已入行的“小朋友”答应了收购条件。当时虽说项目的估价并不透明,但业界略懂行情之人都不可能将价格成交在如此低位,即便那是在人心惶惶的时期。
事后,赵鸣从王大老板的手里得到了80万酬劳。如今,王大老板其实也并未走远,而是作为一个小股东,又整装加入了马总这支大部队……
“老头子还好么?”
“老样子,死性不改,三天两头外面花插插。”
“呵呵呵,你们父子俩还真是一对冤家——对了,你的资金筹得哪能了?我最近头寸是紧得嘞要命了,再拖下去,我看也不指望你了——”
“还差500万,就是这几天的事了,你稍安勿躁——不过股份比例,你再考虑给我往上提一提啊大叔,否则董事局开会我只能蹲在角落里了——”
“这个是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摆在那里的,跟我也商量不通啊。”
“OK!我也不难为你,那你给我安排个好差事吧?”
“浪荡公子哥一个,你能做啥啊?你就安安分分呆在家里等着拿分红吧。”
……
赵鸣在马总的办公室里纠缠了一上午,无果,午饭后在公司四下里转了转,下午才磨磨蹭蹭准备离开。可刚出马总办公室,就在走廊上看见匆匆来退定金的袁静,赶紧扭身远远地逃开。
赵鸣逃得快,可袁静的眼更快,她分明看到了他,心下虽狐疑,却也没工夫理睬。晚上回到家后,袁静跟丈夫唉声叹气地讲述了在马总那碰钉子的事,很想省略见到赵鸣这一细节。因为在她看来,那一刻的赵鸣很没有“腔调”,贼头贼脑象个瘪三,显然与平日里为老公树立的楷模形象相去甚远。但几番犹豫后终还是说了。
启亮心里有了几分敞亮。一是下午美鹃的那条报喜短信令他仿佛看到了新希望,只要甄伍许诺给他的80万到手,眼前的麻烦基本上都能迎刃而解:二是听到老婆的描述,心想,既然赵鸣去过那马总的办公室,那跟马总八成就是熟人,说不准能利用这层关系来退定金。
赵鸣下午又接到他爸赵宽佑的电话,让他晚上回家吃饭,有重要事情跟他说。赵鸣感到有些异样,老妈死了那么多年了,老头子找他说事从不会挑晚上,更不会借着共进晚餐。但老头的命令他又不敢违抗,6点多钟就上了门。
不是郊区的那幢别墅,而是位于黄埔区的一幢公寓。这样好地段的房子,光赵鸣知道的就有5处。他料定老家伙是指望那些房产养老了,否则即便是实在做不动了,也未必能爽快地把厂交出来任他折腾。细细算来,那些房产的总价值远高过了工厂。这种资产转移投资,在上海工商界是很普遍的。做实业的,尤其是私企,拼死拼活赚了点钱,倘若不及时转换为不动产,早晚都会坐吃山空。
“工厂转让的事已经谈好,地、厂房、设备,作价750万,下个月交接,你尽最大努力配合一下。”
“哦,750万——有我份么?没我份你招呼都不用跟我打,时间一到,直接让人把我从厂里扔出来就OK了。”
“小赤佬!走到这一步了还跟我嘴硬?家底都是给你败光的——”老头气得发抖,但毕竟早已过了棍棒式教育阶段,除了破口大骂,拿他也真没辙,“我跟你打过招呼的,从今往后你要自谋生路,这笔钱里,我最多给你50万,你自己好好规划规划吧——”
“呵呵,50万,前辈你好慷慨哟——要不要我三呼万岁,谢主隆恩呢?”
“赤佬!孽障!”
父子俩对峙了一会,开饭了,佣人把菜上齐后退了下去。父子俩就在客厅里用餐。气氛稍稍缓和了下来。
“对方是谁?肯花750万收购的,不是戆徒就是冲头,不是冲头就是洋盘。”
“我托你马叔叔找的,那个人叫王一山,是个浙江商人,也是开加工厂的。”
“啥?”赵鸣惊叫了起来,“就是那个‘王大老板’?啥浙江商人哦,他不做加工已经好多年了啊。”
“你当你老爸戆徒了,我会不晓得么?我还晓得那个老鬼现在就在你马叔叔公司里当小三子,你也不用脑子想一想,你马叔叔也好,他王一山也好,既然有人愿意出高价来收购,不管他绕了几个弯子,只要最后寻到了我这里,我开心还来不及,去点穿这一层做啥?”
“这里面肯定没那么简单啊前辈,你怎么不往深里再想一层呢?王大老板早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产商了,他接手我们的厂有啥用?就算是想推平了要这块地,他们搞住宅开发的要我们的工业用地,也不对路啊。”
“你懂个屁,工业用地变住宅用地当然不容易,但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有那么复杂么?你以为姓马的这个价钱白出的么?还不得你老爸我帮他扫清障碍么?规划局的钱叔叔你是晓得的,小时候抱过你的,不就是撒点米的事情么?人家‘亿科’是看准了将来的地铁站头就在门口,有商业前景才投过来的,你真当他不聆市面了——听王一山话里的意思,好象是打算造酒店式公寓。”
“不是啊——唉——不跟你讲了,生米煮成熟饭的事了——”赵鸣的心思怎可能只在于这一点上呢,他有他的算盘,但眼下显然是落空了。
从赵宽佑的家里出来,赵鸣坐在自己车里,气势汹汹地拨通了王一山的电话。
“王大老板,干得漂亮啊,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收了我的地,你好象早已经忘记了当初我是怎么帮你的了吧?”
“小赵,你这是什么意思嘛?哪来那么大火气?当初你帮我,是因为我需要你帮,事后也没亏待你啊——这趟我是受马总委托,在帮你们家解决困难呀,你怎么反倒冲我发怨气呢?!”
“你少跟我瞎七搭八啥家不家的,你晓得我跟老头子的关系,我的钱全是他的钱,他的钱可没一分是我的,你晓得这趟他从牙缝里挤出多少给我么?50万!触目惊心的50万啊——这么大事,你怎么可以连招呼都不跟我打呢?一定拿了老头子的回扣了吧?要是还象上次我帮你那样来操作,200万是我起码应得的吧?你还跟我装戆?是不是以为阿伍死了你脱离危险了?实话告诉你吧,人家可活得好好的呢!有谁参加过他的追悼会人家都心里有数,你个老滑头以为万事大吉了——报应还在后头呢,你等着看吧。”
电话另一端显然是被唬住了,“小赵啊,这种玩笑可开不得——我出来跟你见一面,有话我们当面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