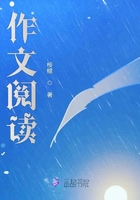“实验做得怎么样了?还在延伸你的流行感吗?”
巴瑞拉长了脸瞪着我。他最痛恨谈论乐团的事。
“是啊。他们真的跟你迷同样的东西吗,巴瑞?”狄克天真无邪地问。
“我们没有迷东西,狄克。我们唱歌。我们的歌。”
“对。”狄克说:“抱歉。”
“噢,少放屁,巴瑞。”我说,“你们的歌听起来像什么?披头士?超脱合唱团?PapaAbrahamandtheSmurfs?”
“我们最大的影响你可能听都没听过。”巴瑞说。
“说来听听。”
“他们大部分是德国团。”
“像什么,‘电厂合唱团’那一类?”
他轻蔑地望着我。“呃,连边儿都没有。”
“那会是谁?”
“你不会听过的,洛,闭上嘴就是了。”
“说一个就好。”
“不。”
“那给我第一个字头。”
“不。”
“你们根本连他妈的八字都没一撇,对吧?”
他生气地大步离开店里。
我知道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是这个答案,而我只能很抱歉这么说,不过如果有哪个小伙子需要打一炮,那就是巴瑞。
她还住在伦敦。我从查号台查到她的电话和地址——她住在兰德布鲁克森林,当然了。我打过去,不过我把话筒拿在离话机一寸远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人接的话我就可以尽快挂掉。有人接起来,我挂断。大约五分钟后,我再试了一次,不过这次我把话筒拿离耳朵近一点,我可以听见是答录机,而非有人接电话。不过,我还是挂断。我还没准备好听她的声音。第三次,我听她的留言;第四次,我自己留一通留言。这真是不可思议,真的,想想过去十年来我早就随时都可以这么做,她已经变得如此重大,大到我觉得她应该住在火星上,因此所有与她沟通的尝试都会花上数百万英镑和好几光年才能联络上她。她是一个外星人、一缕幽魂、一个谜,不是一个有答录机、生锈炒菜锅和“一卡通”的真人。
她听起来老了一点,我猜,而且有点趾高气扬——伦敦已经吸干她布里斯托尔卷舌音的生命——不过很显然是她。她没有说她是不是跟别人住在一起——我自然不是期望一通留言会全盘托出她的爱情现况,但是她没说,你知道,“查理和马可现在都不方便接电话。”或诸如此类的话,只说,“现在没人在家,请在哔声后留话。”我留下我的名字,包括我的姓,还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好久不见等等。
我没有接到她的回电。几天后我又试了一次,而且我说一样的话。还是没有动静。如果你要谈抛弃,现在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在她遗弃了你十年后连你的电话都不回的人。
茉莉走进店里。
“嗨,各位。”
狄克和巴瑞可疑又尴尬地销声匿迹。
“再见,各位。”她在他们消失后说,然后耸耸肩。
她盯着我看。“你在躲我吗,小子?”她假装生气地问。
“我没有。”
她皱着眉把头侧向一边。
“真的。我怎么会?我连你过去几天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你现在觉得不好意思吗?”
“噢,老天,没错。”
她笑了。“没有必要。”
这个,似乎,是你跟美国人上床的后果,这么一些率直的善意。你不会看到一个高尚的英国女人在一夜情后迈步走进来这里。我们了解这些事,大体来说,最好就抛在脑后。但是我推断茉莉想谈这件事,探讨哪里出了问题;她或许要我们去上什么团体咨询课,连同其他许多不慎共度一个周六夜晚的伴侣。我们或许还得脱下衣服重演事情的经过,而我会把毛衣卡在脑袋上。
“我在想你今晚要不要来看丁骨演出。”
我当然不要。我们不能再有任何交谈,你还搞不懂吗,女人?我们上过床,这到此为止。这是本国的法律。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回你来的地方去。
“好啊。太棒了。”
“你知道一个叫斯托克纽因顿的地方吗?他在那里表演。织工酒馆(TheWeaversArms)。”
“我知道。”我想,我大可不出现,但是我知道我会去。
而且我们玩得很开心。她的美国人方式是对的,我们上过床并不代表我们必须讨厌对方。我们享受丁骨的演出,而茉莉,与他一起唱安可曲(当她走上台时,大家看着她原来站的地方,然后他们看着站在她原来站的地方旁边的那个人,而我相当喜欢这样)。然后我们三个人回到她家喝酒,然后我们聊伦敦、奥斯汀和唱片,不过没聊什么有关性的话题或者特定的某一晚,好像那只是某件我们做过的事,例如去咖哩屋一样,不需要检验或说明。然后我回家,茉莉给我甜甜的一吻,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仿佛我有一段感情,只有一段,是真的还不错,是我可以感到自豪的小小平顺点。
到最后,查理打电话来:她对没能早点回电感到抱歉,不过她一直不在,她在美国,去出差。我试着假装好像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知道,当然了——我到过布莱顿出差,到过瑞地奇,甚至到过诺威奇,但是我没有去过美国。
“那么,你好吗?”她问。然后有那么一下子,不过就算只有那么一下子,我想要对她演一段哭调:“不太好,谢谢,查理,不过你别为这操心。你大可飞到美国出差,别管我。”然而,为了我永恒的名声,我克制住自己,然后假装自我们最后一次说话之后,过去十二年来我成功地过着一个运作良好的人类生活。
“还好,谢了。”
“很好,我很高兴你是个好人,你应该过得很好。”
某件事在哪里有不点对劲,不过我无法确切地指出来。
“你好吗?”
“很好。很棒。工作很好,好的朋友,好的公寓,你知道。现在,大学似乎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你记得我们以前常坐在酒吧,想像我们的人生会变成怎样?”
不记得。
“这个嘛……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我很高兴你对你的也很满意。”
我没说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我说我还好,指的是没有感冒、没有最近的交通意外、没有暂缓的刑期,不过算了。
“你有没有,你知道,小孩这一类的,跟其他人一样?”
“没有。如果我要小孩的话我早就有了,当然,不过我不想要小孩。我太年轻了,而他们太……”
“年幼?”
“对,年幼,显然是。”——她笑得很神经质,好像我是个白痴,我也许是,不过不是她想的那样——“不过太——我不知道,太耗时间了,我猜这是我要找的说法。”
我没有捏造这里面任何一句话。这就是她说话的方式,好像整个世界史里头根本没有人谈过这个话题。
“噢,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刚刚拿查理开玩笑。查理!查理·尼科尔森!这太诡异了。大多数的时候,在过去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我一直想到查理,然后把我大多数不称心的事情,归咎于查理,或至少归咎于我们的分手。譬如:我本来不会休学;我本来不会到“唱片与卡带”交换中心工作;我本来不会被这家店套牢;我本来不会有不如人意的私生活。这个女人伤了我的心、毁了我的人生,这个女人必须为我的贫困、乱了方寸与失败独自肩负起所有的责任,这是我足足有五年的时间常常梦见的女人,而我居然取笑她。我不由得赞叹起自己来了,真的。我得脱下自己的帽子,对自己说:“洛,你是个很酷的角色。”
“总之,你来或不来,洛?”
“你说什么?”听见她还是说着只有她能理解的话让人感到欣慰。我从前喜欢她这样,而且感到嫉妒:我从来想不到要说什么听起来奇奇怪怪的话。
“没什么,对不起。只不过……我觉得这种失散多年的男友打来电话让人很气馁。最近他们突然纷纷冒出来。你记得那个我在你之后交往的家伙马可吗?”
“嗯……是,我想记得。”我知道接下来是什么,而且我不敢相信。所有那些痛苦的幻想,婚姻和小孩,许多许多年,而她大概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半年之后就把他给甩了。
“他几个月前打电话来,而我不太确定要跟他说什么。我想他正在经历,你知道,某种‘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的时期,然后他想见我,谈一谈近况如何,而我没什么兴趣。男人全部都会这个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
“那么,只有我挑中的。我不是指……”
“不、不,没关系。看起来一定有点好笑,我没头没脑地打电话来。我只是想,你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看不出她怎么会知道。“不过你来或不来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不知道,我们还是不是朋友?因为如果我们是,没问题,而如果我们不是,我看不出在电话上浪费时间有什么意义。你星期六要不要过来吃晚餐?我有一些朋友要来,而我需要一名备用男伴,你可以当备用吗?”
“我……”有什么意义?“是,目前来说。”
“所以,你来还是不来?”
“我来。”
“很好。我的朋友克拉拉要来,而她没有男伴,而且她正合你的口味。八点左右?”
然后就这样。现在我可以指出哪里不对劲:查理很讨人厌。她以前不会讨人厌,但某件坏事发生在她身上,而且她说一些糟糕又愚蠢的话,而且显然没有什么幽默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会把查理写成什么?
我告诉丽兹伊恩打电话给我,然后她说这太过分了,然后说萝拉会很震惊,这让我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我告诉她有关艾莉森和彭妮和莎拉和杰姬的事,那只愚蠢的小手电筒笔,还有查理和她刚从美国出差回来的事,然后丽兹说她正要去美国出差,然后我戏谑地嘲弄她的花费,不过她没有笑。
“洛,你干嘛讨厌工作比你好的女人?”
她有时候会这样,丽兹。她不错,但是,你知道,她是那种有被迫妄想症的女性主义者,你说的每件事她都会看到鬼。
“你现在又怎么了?”
“你讨厌这个拿着一只小手电筒笔进戏院的女人,假设你想在黑暗中写东西这完全合情合理。然后你讨厌那个……查理?查理到美国去这件事——我是说,也许她不想去美国。我知道我不想。然后你不喜欢萝拉换工作以后,她别无选择一定得穿的衣服;然后我令人不齿,因为我得飞到芝加哥去,跟一群男人在饭店的会议室里开八小时的会再飞回家……”
“嘿,我有性别歧视,对吗?这是正确答案吗?”
你只能以微笑接受这种事,不然你会被搞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