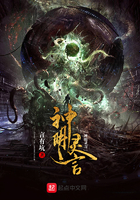【作者的笔记:这部分的讨论主要是根据朗达主教的玛雅语字母表,它是完全不确定的,而且现在被证明是完全不正确的,以玛雅语写就的作品直到最近才被翻译成普通文字。玛雅的象形文字比郎达发明的要少很多,而且完全是表意的,没有特殊的语音密码可言,在这一部分要讨论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旧世界字母表的发展,这与亚特兰蒂斯的问题没有关系】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语音字母表或者代表人类语言声调的符号体系可以说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个发明。假如没有它,可能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文明的存在。
我们还不能就欧洲字母表的源头作出解释: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查找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种形式查找到另一种形式,一直查找到埃及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和库施特人的古体表格,不过除此之外就不知道其他的了。
埃及人并没有把他们的象形文字的书写体系归功于自身的发明,而是把它说成是“神的语言”。毋庸置疑,“神”就是他们高度文明的祖先——亚特兰蒂斯人——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他们成了地中海许多民族的神。
“在腓尼基人看来,透特(Taautus或Taut)是书写艺术的发明者,‘埃及人叫他Thouth’,而且埃及人说它是由Thouth或者Thoth发明的,在其他地方他被称为‘第一个贺密士’,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腓尼基人和埃及人都把发明归于一个比他们自己的独立政治存在更为久远的时期和民族,他们就是从那个时期和民族那里继承这个发明的。”在这里谈及的“第一个贺密士”(后来罗马人称之为莫丘里)是宙斯和玛雅之子,玛雅是亚特拉斯的一个女儿。这个玛雅和法国人阿比·布拉索·德·保尔勃格所确认的中美洲的玛雅是一样的。
威廉·杜蒙德先生在他的《起源》中说:“似乎无法说清楚早期字母在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中是如何被运用的,或者为那些民族所用的一些图表之间为何会存在某些相似之处,除非推测象形文字的书写——如果我可以被允许使用这个术语的话——在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时期就已经被使用了,那时候对行星的崇拜几乎是当时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国家都信仰的宗教。”
亨利·劳林森先生说:“早期书写原则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以致它似乎在迦勒底时期就得以继续了,正如我们实际上能够把它的进步追溯至埃及一样,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最初发明的源头追溯至哈姆族人分散和分裂之前的一段时期。”
很难相信这个令人惊叹的语音符号体系是由一个人或者在一个时期内所发明的。像我们获得的其他东西一样,它绝对经过了长时期的缓慢发展和添加;它肯定是由图像经过像中文那样的中间状态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在这个中间状态,每一个词或事物都是一个单独的符号。像中国人一样古老开明的民族都没有发明语音字母表的能力,这一事实向我们证明了发明它的人们是何等的伟大,以及他们达到这个水平要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
洪保德说:“根据从商博良的伟大发现开始就逐步被适用的有关字母文字发展的早期状况的观点,腓尼基和闪米特的文字都被看做是根据图形文字变化而来的语音字母;这些符号的象形意义已经完全被遗忘了,它们只不过是被当做语音符号而已。”
鲍德温说:“作为海上霸主的民族,与每一个海岸都建立了联系,而且一手操控了已知世界的贸易,在他们逐步到达这个显赫地位的过程中,他们肯定用语音字母代替了象形文字;而孤立的埃及,由于受实际需要和贸易发展趋势的影响较少,所以能使象形文字的体系得以保留,并将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必须谨记这一事实:我们字母表里的一些字母是稍后一些的民族的发明。在历史最为古老的字母表中没有c,c的位置是g。罗马人将g改成了c;后来他们发现有必要增加一个g的符号,于是他们在C的尾部加了一笔,就成了G。希腊人将希腊语的第20个字母加入了古代的字母表中,这个字母的形状和我们的V或者Y很相像,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形状的字母是被混合运用的。他们加上了符号x;他们将腓尼基语中的t改成了th或者theta;z和s成了双辅音的符号;他们还将腓尼基语中的y(yoa)改成了I(iota)。希腊人把一部分是辅音的腓尼基语音表改成了一个完整的语音表——“一个口语表达的完美工具”。w也被加入了腓尼基的字母表中。罗马人加上了y。开始的时候,i和j发同样的音;j这个符号是后来加上的。像欧洲其他语言一样,我们还加上了一个双U,也就是VV,或者W,其发音为W。
那么应当把功劳记在腓尼基人头上的字母是A、B、C、D、E、H、I、K、L、M、N、O、P、Q、R、S、T、Z。如果我们要寻找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字母表的相同之处,那么它肯定与这些符号不无关联。
有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在某些方面与腓尼基字母表类似的字母表,好让我们用以参照呢?它绝不会是中国字母表,其中符号比单词多;它也不可能是亚速尔的楔形文字字母表,其中的700个箭形文字中,没有一个与腓尼基语的字母有哪怕一丁点相似之处。
我们在中美洲发现了一个语音字母表,这件事的确令人感到意外。它是在玛雅人,犹加敦半岛居民的字母表中发现的,他们认为自身的文明是从东方,也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方向通过船只漂洋过海到达这里的。玛雅人是考华斯人的继承者,后者的时代在基督时代的1000年前就已经终结了:玛雅人的字母表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它是通过早期的传教士之一朗达主教流传给我们的,他对外宣称自己把大部分的玛雅语书籍都付之一炬了,因为里面除了恶魔的作品,什么都没有。然而,他给后代留下了玛雅语的字母表,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们把它列在下边。
朗达的字母表:犹加敦的首位主教是迪亚多哥·朗达。他记录下了玛雅人和他们的祖国的历史,他的手稿在马德里皇家历史学会的图书馆中得到了完好保存……在手稿中有对玛雅语字母表所做的描述和解释。人们似乎忘记了被保存在图书馆中的朗达的手稿,因为在法国牧师布拉索·德·保尔勃格发现它之前,谁也没有听说过它,在它的帮助之下,这个法国牧师已经把一些古老的美洲作品翻译成了普通文字。他说:“朗达对那些字母表和符号所做的注释于我而言就像罗塞塔的石头。”如果我们观察到我在这里所给出的不同欧洲国家的字母表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做了多么大的改动的话,两、三世纪以来的玛雅语字母表和古代欧洲的字母表的任何相似之处都会令我们惊讶不已。但是,必须记得玛雅人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人之一。他们的固执令人惊讶,他们还在坚持讲他们在哥伦布登上圣萨尔瓦多岛时讲的语言;而且我们深信那种语言和在他们国家最古老的纪念碑上所刻着的语言是一样的。赛诺·皮门特尔在谈到他们的时候说:“印第安人固执又保守地延续着这种习惯用语,以至他们不愿意讲别的语言;白种人有必要把这些习惯用语放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以方便同他们交流。”因为他们的字母表像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一样没有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所以它在继承考华斯人的原始形态的基础上并没有做出很大的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已经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腓尼基之前的古代字母表的中间状态这一事实,那么发现玛雅语的字母和欧洲字母的形状有些许相似的地方都是让人无比惊讶的,虽然我们承认它们有联系。如果我们发现两或三个字母之间有确定的相似之处,我们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推断对于许多其他在世纪的磨损中消失的字母也一定存在这种相似的巧合。
我们对朗达字母表做出解释的最初根据是这些字母所构成的复杂而华丽的文字。在这里,呈现在我们眼中的是粗糙的物体图,而不是我们用以表示发音的符号的两三画。而且我们发现它们自己经过了一种更为复杂和古老的文字的简单化。例如,字母PP在朗达字母表中的形状是,显而易见,这是一张脸的图像。符号x也是一样,虽然不是特别明显,它的形状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在中美洲纪念碑上刻着的古代象形文字,我们将会在其中的很多文字中都能发现人脸的形状,以下是我们从布兰科的十字架碑上复制而来的。我们从碑铭的左边摘取了这些象形文字。在这里,我们能够发现,在7个象形文字的图形中有6个都包括人脸。而且我们还发现,在那个十字架碑上刻着的108个象形文字中有33个都是部分地由人脸组成的。
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朗达字母表的趋势是逐步的单一化。如果把象形文字的图画——最初的时候它们可能被试图用于制作缓慢而精细的宗教碑铭——放在一个繁忙、活跃的商人手中,例如亚特兰蒂斯人和以后的腓尼基人以及其他时间对其非常有价值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它们就会被简化、压缩;并且如果该图形的原始意思遗失了,他们会很自然地把它忽略掉,比如我们在玛雅语字母表中发现的保留着粗糙模糊的人脸形状线条的字母pp和x。
就像朗达字母表中显示的那样,字母h的两种形状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个趋势,其原先的形状比其变体要更为细致得多。它的最初形状是,变体的形状是。现在我们假设这种简单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个形状的上部和下部均变为一个更小且比原来更为简单的形状,让我们想象他们都是在同一个趋势下被废除的,然后再看玛雅语字母表中的字母h,它是用这个图形表示的:现在来说,因为写一画比写两画更为省时,所以这个图形会适时地变为。现在我们再审视一下古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文字,就会发现字母h是用这个符号表示的,正是从玛雅语的字母h简化而来的。再来看古希伯来人,我们发现了。正如我们所知,腓尼基人书写的时候是从右到左,就像我们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会使我们写出的字向右倾斜一样,腓尼基人的书写方式决定了他们写出的字会向左倾斜。因此玛雅语的符号在古腓尼基语中就变成了这样。我们甚至在一些腓尼基的字母表中发现了和玛雅语中的字母h一样的上下都是由两画组成的字母h。埃及象形文字中h的形状是,而ch是。希腊人又适时地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就像我们已经推测过的亚特兰蒂斯人把双线去掉一线那样,他们删除了上面的横线,于是这个字母就变成了流传至今的这个样子,H。
现在,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说成是偶然的巧合。如果确实是的话,这当然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但是让我们再做下更为深入的观察。
从朗达的字母表的显示中,我们发现字母m有两种形状。第一种形状是;但是朗达说我们也发现m以以下这种方式被字母o,a或e联了起来。M当然是这个联合图形的中间部分。这证明了什么?亚特兰蒂斯人或者玛雅人在试图对他们的字母作出简化并且把它们与其他字母联起来的过程中,从过度装饰的象形文字图案的中间摘取了某个文字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代替整个图案。现在,让我们适用这个规则。
在字母表中我们已经看到,从我们的时代到腓尼基人的时代,在每一种语言中,字母o都是用一个圆圈或者一个圆圈套在另一个圆圈里面来表示的。那么腓尼基人是如何得到它的呢?很明显是从玛雅语中得来的。在玛雅语的字母表中代表字母o的图形有两个:它们是和。现在假如我们将上面适用于玛雅语的字母m的例子中的规则适用于这些图形,那么每一个图形中最为重要的一处就是那个圆圈,在第一个象形文字中是那个下垂的部分;在另一个象形文字中在其下半部分的中间。这个圆圈摘自象形文字,且被单独使用,这与字母m的例子是一样的,后一个例子可以由用于朗达字母表底部的符号得到证明。朗达把它叫做ma、me或者mo;这可能是最后一个,并且其中有在象形文字中分离出来的圆圈。
我们发现标准的玛雅语中的o是两个圆圈里外相套,或者在一个圆圈中点上一个点,这在腓尼基语中得到了再现,因此腓尼基语中o的形状是和;而且字母o在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形状实际上是相同的;希腊语中字母o的点位于圆圈的旁边而不是下边,就像在玛雅语中一样。
难不成这些是另一种巧合?
再以另外一个字母为例。在玛雅语字母表中,字母n是用这个符号表示的,它也许是某一种更加繁琐的形式的简化。它和我们的字母S很相像,而不像我们的字母N。但是如果我们查一下我们的字母N的家谱,就会发现在和埃及语一样有着古老历史并代表着其亚特兰蒂斯祖先的库施特族分支的古代埃塞俄比亚语中,代表字母n(na)的符号是。它的形状在古代腓尼基语中与S更为近似,即,或者是这种形状。只需把这些角弄弯我们就会发现它与玛雅语中的字母n非常相似。在特洛伊发现了这个形状。撒玛利亚人把它转化为这个形状:古希伯来人则把它又转变成这个形状:在默阿布石碑的碑铭上它的形状是这样的:后来的腓尼基人又对这一古代的形状做了更深一步的简化,它简化到,然后到 ;它在古希腊语中的形状是;后来的希腊人又把它演变成,到后来它的形状就演变成了现在的N。所有的这些形状看起来都像是一条蛇:我们希望能在尼罗河的山谷中有所发现,我们发现在埃及语中,N的象形文字就是一条蛇:佩拉斯吉语中的n的形状是;阿卡狄亚语中的n是;伊特鲁里亚语中的n是。
还有什么比在中美洲以及所有这些旧世界的语言中,发现蛇是字母n的标志这一事实更重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