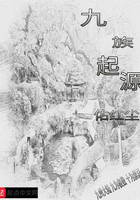人曰:人生是个“怪圈”,而男男女女就是生活在“怪圈”中的求索者。又听人言:婚姻是个“黑洞”,男女一旦结合,就被堕入“黑洞”中,冲撞、磨擦、争斗、撕咬,无休无止,直到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或粉身碎骨,或爬出“黑洞”逃之夭夭。
新婚之夜,文轩与他的爱妻静伦沉浸在千般缱绻、万种蜜意中。爱的浪潮汹涌澎湃,似惊涛拍岸,如大浪淘天。渐渐,风平了,浪静了,收敛性子的浪涛变成一个恬静的少女,轻轻地吻着黄金般的海岸。而此时的文轩和静伦,宛如一叶在浪涛中搏击后的小舟,疲惫而安适地栖息在风平浪静、阳光明媚的港湾。
“伦,累了吧?”文轩目不转睛地盯着娇美的爱妻,发现她的脸颊爬上憔悴的云翳,关切地问,但他的问话是带有广义性的。
静伦心里明白。是呵,这几年她觉得实在太累了。不知是她想检验自身的价值呢,还是真的是一切“向钱(前)看”,她竟辞掉拿起教鞭不足一年的中学教师工作,也毅然告别了与她正处于热恋巅峰的文轩,到深圳成了一个“打工妹”。在特区,老板是上帝,金钱似是俊男靓女,谁都想攀附、想占有,而且无不充斥着血腥般的贪婪。静伦起初在一家中等档次的饭店当女招待,她听说干“桑拿女”赚钱多,就干上了“桑拿女”的活计。几个月后,她听说一家豪华气派的歌舞厅需要一个当班经理,又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试,结果一次性命中,并且将这个歌舞厅经营得十分红火,从而在深圳娱乐圈中一炮打红。她每月的薪水几千元人民币,比国家机关一个司局级干部一年拿的工资还要多。按说应该满足了吧?不。当一个在深圳的外国老板提出愿出比她当歌舞厅经理高出一倍的薪水聘用她当他的贴身秘书时,她又点头作答。较之原本高得惊人的薪水,代替外国老板发号施令的权威,她立刻在这家赫赫有名的外国公司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可是三年后当文轩提出要她辞掉深圳的差事回来与他结婚时,她在爱情与金钱两者间未多加思虑,一周之内便风尘仆仆地投入到文轩的怀抱里。他们的婚事办得相当气派。以静伦给文轩指令性的话讲,即“一切听我的!”从购买这两屋一厅并装修得体的新房到一色的样式别致价格昂贵的家具,从结婚典礼场所的选择到典礼时令人咂舌的排场,都是静伦呕心沥血,匠心独运。文轩呢,倒是落了个清闲自在。
“文轩,这几年叫你等得好苦。对不起。”静伦微启皓齿,甜甜地一笑,颇有几分于心不忍又有几分歉意地说。
文轩轻轻一吻静伦:“爱,就不要说对不起。”说完轻轻吁了一口气,那神情与其说是在宽慰静伦,莫如说是在抚慰自己。
是啊,这三年对干文轩来讲的确不是个滋味儿。从恋爱巅峰跌落而下的落差,使他毫无准备的心灵受到猛烈地一击,那难以承受的折磨实在苦不堪言。他曾喋喋不休地追问静伦为什么放弃人民教师的工作称号而去甘当“打工妹”?静伦的回答是她觉得教师的工作太御用化,而想去按照自己的意愿闯世界。接着他据理驳斥地讲,难道“打工妹”不更工具化?这该怎么解释?静伦却说她还没有跟他结婚即便就是结了婚也不等于卖给他,她有她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最后他摊牌式地讲她如果以此作为跟他结束恋爱的手段就干脆说在明处,静伦说她爱他是海枯石烂不变心,如果他不信她可以对天盟誓,并且讲只要允许她出去三年,三年以后他想什么时候叫她回来她都随时听从调遣,从而使他再也难以挽留她。于是,静伦走了,文轩的心也随着他爱的人走了。诚然三年间不少亲朋好友说静伦一走是肉包子打狗,劝文轩不要犯傻尽快再找一个姑娘,但文轩却总是不吐口,说他在爱情上是忠贞不渝并且自我感觉良好地讲静伦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更有甚者,文轩为了表示对静伦的坚信,居然放弃了两次可以到深圳出差的机会,而这种爱也大有一种雄赳赳奔赴刑场的慷慨。
“伦,恕我直言,我心里一直有个谜。你去深圳才三年,怎么会挣这么多的钱呢?”文轩问得直接,透着坦率。
静伦先是黛眉一挑,接着微蹙眉头,踟蹰片刻,讷讷道:“在外企,只要讨得老板的赏识,他们是会一掷千金的。”
“怎么才算得了讨得外国老板的赏识呢?”文轩的提问越来越具体,无形中透着一股咄咄逼人的味道。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老板面前游刃有余。”静伦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像我这个做秘书的,就更显得重要。”“你是单纯指工作方面,还是包括其它应酬?”
“秘书的工作其实就是应酬,特别是当外国老板的秘书。”
“你的应酬,总不会像时下有人说的包‘全活儿’吧?”文轩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他意识到将面临一种可怕的不幸。
“文轩,我早想告诉你,不要用过去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也不要用过去女人必须恪守贞操的标准衡量我。”静伦说到这里,不知是表示悔恨还是表示哀求,将额头抵在文轩的胸膛上开始我想奋力地改造生活,不久我便觉得这是异想天开,而且明确地感到,什么才叫适者生存。所以,我才被迫无奈地就成了现实生活的俘虏。
“跟谁?”文轩猛地一掀被子,霍地坐了起来,声音如吼。
“跟那个外国老板。”静伦只得坦露真情。
“你、你、你这个臭、臭婊子!”文轩勃然大怒,那散乱的头发抖动着,活像一只狂暴的雄狮。他的手大锤般陡地抡起,在空中停顿片刻,又颓然地垂下来,头一低那沮丧的样子,像只斗了败架的公鸡。
“文轩——你!”静伦被文轩的神态惊呆了。她满以为文轩对她在深圳的所作所为是理解的。大概正是出于理解他才放弃两次去深圳的机会而不干扰她。她觉得,她与外国老板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交易,一种逢场作戏。根据以往她对文轩的了解,觉得文轩性格开朗,胸襟豁达,且修养有素。如实告诉他,才是对爱情的忠诚,也才可能在文轩的理解和爱抚中治愈过去痛苦的创伤。谁知向文轩讲明实情后,他却像遭到致命的一击,从表现看他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难以承受,并难以承认这是事实。尽管静伦泪流满面地向文轩检讨自己一时的迷惘和过错,可文轩抱起被子躺在沙发上不予理睬,一声不吭。
翌日清晨,静伦洗漱完毕,给文轩冲了杯牛奶,煎了两个荷包蛋,夹在法国大磨坊面包里,呼唤蒙头大睡的文轩起来吃给备好的早点。谁知,文轩一掀被子,挺身而起,穿好衣服,冲着静伦给他摆在茶几上的牛奶面包“呸”地啐了一口,厌恶地吼了句:“我不吃,我嫌它脏!”然后悻悻地愤然离去。
呆若木鸡般站着的静伦看着离她而去的文轩,心理痛苦地呼嚎:夫妻之间任何事情都该坦白,那么我将自己的隐私告诉了文轩,他却立刻变得像个暴君,到底是该还是不该呢?难道我错了吗?现实生活就是如此,我又错在哪儿呢?
断想录:静伦的坦诚,使得文轩变得怒不可遏。而文轩的弃静伦愤怒而去,又令静伦陷入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