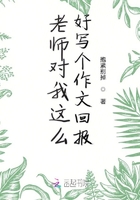父亲是弓,
儿子是箭。
弓为了把箭射得更远,
把背弯了又弯。
——题记
窗外响起了一阵狗吠,门吱呀一声开了,接着,传来一阵干咳。
我揉揉惺忪的睡眼,穿好衣服下了床。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见父亲正佝偻着背为我打点行李。我轻轻地喊了一声“爸”,他没有听见。五十出头的他头发已有些白了,听力也不如从前了。我心里一酸,有种心痛的感觉。
他一转身,看见了我。“起来了,报到时间是8点是不是?”我一惊,昨晚才告诉过他11点到校,他怎么忘得这样快?“11点,不是8点。”我提了提嗓门。“嘿!人老了,这也记不住了。”他嘿嘿地笑道。
行李装好后,他用白开水泡馍简便地打发了早餐后,便和我走出了只有三间破瓦房的家。家门口,母亲久久地站立着,不住地拭着泪。
从家里到县城有20多里路,而只有到30里外的镇上才有车。这意味着,父亲要提着近50斤重的行李走30里地。我坚持着自己拿行李,已16岁的我个头比父亲竟高出一头,但父亲执意不肯。他又讲起了往事:“年轻时,我背着两袋面粉从镇上回到家,走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一直愁苦的脸上浮出了久违不见的笑容。我强忍着泪,不想破坏那笑容。
太阳出来了,日光变得毒辣了。我渐渐地落在了后面。在土路边的水沟里洗了一把脸,我顿觉舒服极了。我赶上他,他的汗珠如雨滴般地下落,头发粘在前额。“到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吃饭不要省,要吃饱;和同学要搞好关系……”他喘着气,说话也不大连贯了。我心疼地拿下包,让他洗洗脸。他迟疑着问了几遍“不会晚吧?”才去了。
到了车站,父亲把包给我,说“进去吧”。又拉着我,“占个靠窗的位置,你晕车。”上了车,我把包放在一个靠窗的地方,买了票。
我看到父亲孤零零地站在太阳下,嘴唇干裂。虽然两边有卖各种饮料的小贩,但我知道他不会买。
我想起他在田地里背麦子上坡的情景,也许他的背就是在那时变弯的吧。
车子启动了,我向他摆手,他在后面着急地说“注意身体,与人和气——”
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怎么也抑制不住,我想起了朱自清的散文《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