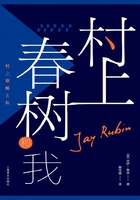他在诗中以朝云比王映霞。朝云系苏东坡的姬侍,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苏东坡对朝云非常钟爱,在她死后曾做《悼朝云诗》寄托哀思。所以朝云作为古代文人姬侍中之佼佼者而留名后世。郁达夫的这首七律,单从“诗”的角度来看,确乎写得很好;但题名《寄映霞》,又把映霞比作古代之姬侍,郁达夫也自觉有些不妥。所以,后来他又把“朝云”二字改为了“霞君”,就是现在通行的这个本子。
如果仅仅在诗句之中偶尔把王映霞戏称为“姬”为“妾”也还罢了,使王映霞最为恼火的一件事,是1931年郁达夫曾回故乡富阳小住。按照王映霞在《答辩书简》中的说法是:“……兽心易变,在婚后的第三年,当我怀着第三个孩子,已有九足月的时候,这位自私、自大的男人,竟会在深夜中窃取了我那仅有的银行中五百元存折,偷跑到他已经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边,去同住了几日。……等他住够了,玩够了,钱也花完了,于写成了一篇《钓台的春书》,一首‘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七律之后,也许是受了良心的责罚吧,才得意扬扬地,又逃回到当时我曾经牺牲了一切的安乐,而在苦苦地生活着的上海的贫民窟里来。”
即使王映霞在这里所说的全部是事实,那么从她对这些事实所做的解释与评价中,可以不难看出她对郁达夫有相当程度的误解,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很深的隔膜。王映霞平日不大关心时事。她不了解郁达夫当时险恶的处境。1931年2月7日,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郁达夫也在3月间接到了警告。所以才不得不离沪去杭州、富阳等地暂避。正如郁达夫在《钓台的春书》一文中所说:“1931年,岁在辛末,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
孙荃那时早已从北京回富阳居住。名义上,她还是郁家的儿媳,郁达夫的元配夫人。俗云:“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见面,虽然各怀心事,但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乎?尤其是郁达夫,他觉得自己实在对不住荃君,他除了请求荃君原谅、饶恕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啊啊,我啊!我真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罪人啊!”他声泪俱下地向孙荃说道。
孙荃也泪眼盈盈。但她没有更多的话,只意味深长地说了八个字——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郁达夫不知道孙荃说的这个“当初”,是指他当初不该屈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同她结婚呢,还是他当初不该重婚再娶,和王映霞小姐结为伉俪?眼下的郁达夫也无心去探究这些。他是为避难而来的,先在浙江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尔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了归计。谁知一回故乡,又重面临着那无法解脱的矛盾。无论国事家事,总之都无一顺心之处,感愤之极,他当即对荃君说道:
“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得逢杨爱,则忠节两全矣!”
另据蒋增福《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中的记载,郁达夫这次回来以后,郁母怕执拗的三儿媳会给他过于难堪,曾劝抚孙荃要她忍着点,既然丈夫回来了,又是带着矛盾和歉疚的心情回家的,至少要以客人相待才是。孙荃遵照婆婆的嘱咐,白天仍照以往那样给郁达夫准备下好酒好饭,到了晚上则把他的床铺安顿在楼下的厢房里,自己带着儿女上楼去睡了,在门上还贴了一纸告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连着几夜都是如此,郁母见状又来劝慰媳妇,并把跟着孙荃睡的孙女领走去跟她一道睡。郁母叫儿子上楼,可是一待郁达夫进房,刚烈的孙荃便移至原来是女佣(养女)睡的一张单人小床上,不去理会丈夫,全无过去那种柔顺忍让的样子。郁达夫哪见过这个?两个人最后终于吵开了,孙荃当面指责丈夫只顾在外面同王映霞作乐,而将家中妻儿老小抛却。郁达夫辩解再三也不能平息荃君心中积蓄已久的愤怨,她对郁达夫说道:
“你不管我倒也罢了,儿女总是你养出来的呀!”
郁达夫也来了气:“我知道是谁养的?”
孙荃决不相让:“是我跟畜生养的!”
夫妻俩争吵不休,郁母闯入房中,拉着孙荃和孙女儿,婆媳俩意欲双双出走,理了一些衣服,卷起了被子,说当晚要到庵堂里去削发做尼姑。儿女们跪在娘和奶奶面前啼哭,郁达夫也只好跪在老母面前求饶……
王映霞对这件事全然不知。也许她从来就没有想过她对郁达夫的原配妻子孙荃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相反,她对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总是耿耿于怀,不仅生郁达夫的气,而且迁怒于孙荃。
那一年郁母七十大寿,郁达夫带着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是由各门夫妻男女一对依次同拜的,郁母临时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数他最小。轮到小房媳妇辈拜寿时,站在下端的王映霞意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则从左侧快步插入,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来,以示拜寿结束。王映霞显得很尴尬,但也只好忍气吞声,作罢了。事后孙荃对家中人说道:
“老子(富阳话,即丈夫)我被她夺了去没办法,位置我是不让的!”
从郁母和孙荃的态度中,联想到郁达夫的那首七律,王映霞明白了她在郁家不过是被当作“姬妾”看待罢了。这就是她的“位置”。啊啊,出身名门的王映霞对此怎能容忍得了?
再则,郁达夫本来就是一个“多情种子”,他那时而狂热,时而暴雨般的性格,王映霞也委实接受不了。她想望中的爱情是平和而又柔丽的,如像淡淡的秋阳,丝丝的微雨。
总之,思想上的距离和性格上的差异,是郁达夫和王映霞愈来愈隔膜的两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所以郁达夫的这次富阳之行,大大激怒了王映霞。
她感到委屈:自己的婚姻既不同意于父母,又难谅解于亲朋,但自己认为既已误踏入了这一条路,总望委曲求全,抱着百折不回的大力,在荆棘丛中,勇往直前地走去,所以处处都在容忍,都在包涵,以为郁达夫的一切的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好使那些藐视他的戚友们眼中,抬高他的人格。可是,这一切又换来了什么呢?自己是一个名门出身的千金小姐,却被比作“朝云”似的姬妾。姬妾也者,换一个新的时髦说法,就是“姨太太”、“小老婆”呀!
她感到寒心:自己在结婚以后,不是毫无保留地向郁达夫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吗?如像托尔斯泰夫人尽量满足托尔斯泰的要求一样,自己不是使他享受到了最大的满足和快乐么?自己是有名的杭州美女。如此美貌的妻子尚且拴不住他的心。看来,他真是一个“以欲为生命的无聊者”呀!……
她开始感到后悔了。她觉得自己大概做了一件错事:十年前,因为自己的没有经验,再加上眼力不足,以致糊糊涂涂的同这位比自己大十余岁而走惯江湖的浪子结下了婚姻。
王二南老先生闻讯后从杭州赶来了。听了孙女的一番哭诉后,老爹爹沉吟良久。他对映霞说:
“昔日元稹始乱终弃,虽作有《莺莺传》传之后世,然则人终不可取也!莫非达夫也有‘始乱终弃’之意不成?”
王映霞的母亲早就对郁达夫有所不满。带着严重的表情,她插话说道:
“这可说不定!像他这样的浪漫文人,怕是要防他一手才是。可别苦了囡囡一辈子呀!……”
王二南老先生又沉吟了一会儿,末了,对他们母女说道:
“这么办吧,我亲自同达夫谈一次!”
此时王二南老先生的精神已大不如前,然而他还是勉强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同郁达夫做了一次长谈,从深夜谈到了天明。
“达夫!你说应该怎么办?”老先生问道。
郁达夫对王二南老爹爹是素来敬重的。因为他知道老爹爹是他和王映霞婚约中仅有的一个应允者和促成者。对此他内心里时时感激着,不曾忘怀。而今事实摊在眼前怎么办呢?郁达夫觉得自己无言以对,只好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了老爹爹。
“唔——”王二南老先生把保证书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亲自用信封封好,交给了在一旁的孙女映霞。
“单是一纸保证书,老朽也还是有些不放心呢!”王二南老先生又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郁达夫说。他担心郁达夫始乱终弃,所以打算要为孙女争得经济上的权利,为孙女留下一条后路。
“那——”郁达夫赶紧说道:“我再写一份版权赠与书给映霞好了。”
王二南老先生这才点了点头。作为老人,他觉得自己也只能尽些微薄之力,到此为止了。
第二天,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的经理,当着众人的面,亲笔写成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王映霞各执存一份。
于是,从表面上,这件事情——或者说这场家庭风波——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了。然而郁达夫却从此对王映霞产生了一个十分坏的印象:他觉得王映霞毕竟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她怎么向他索要版权,并动用老爹爹来对他施加压力呢?
这样一个王映霞,和他当初苦苦追求的那个王女士,真是有天壤之别!王映霞依然是美丽的,非常美丽的,但郁达夫此时却觉得她大概徒有一个美丽的躯壳,里面包裹着一个世俗的灵魂。自己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个闪耀着各种迷人色彩的幻影罢了……
所以,当他把“版权赠与书”交给王映霞的时候,一种幻灭的悲哀猛地袭上了他的心头。他向面前这个“美丽的幻影”冷笑道:
“哼哼,这样你总满意了吧?”
又轻轻吹了两口气,好像要看看美丽的“肥皂泡”是否会一吹就破似的……
然而,王映霞又怎么会“满意”呢?物质是交换不到她的感情的哟!
过了几天,王二南老先生回杭州去了。王映霞在送他老人家上车时,流了不少眼泪。归来的路上,她走在往常同郁达夫经常携手漫步的人行道上,听着洋梧桐、洋槐的絮语,感到一阵心酸。回到家中以后,她突然感到陌生得很,似乎这个家已经不像是她的家了。
“妈!”小阳春跑到她跟前来,亲热地叫了一声。
王映霞这时才恢复了原来的神智。她紧紧地把阳春搂在怀里。想着自己已经出世的儿女,想着腹中那个九个月的胎儿,又想到这几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她深感到来日之茫茫,禁不住泪如泉涌。
“妈!你怎么哭啦?”小阳春莫名其妙地望着妈妈,问道。“是爸爸欺负了你吗?”
这一句简单的问话触痛了王映霞心灵的创伤。是的,单纯的物质上的满足是交换不到她的感情的,何况郁达夫所给予的也有限得很,离“满足”二字还差远远。对她来说,心灵上的创伤,并没有因为一时的甜言蜜语与在苦丸外面包着的糖衣的生活中,淡忘了下去,想复仇的心的热烈,与她的年龄一样地增长了上去,没有一时离开过她的脑海。
从这以后,她的胆量大了不少。她不像前几年那样老是死守在家里了。她去做了许多次郁达夫所不愿意她做的事情,如去探望几个独身同学,她向她们诉说了自己的痛苦。等郁达夫不在家的时候,又约她们到家里来玩。
“一·二八”的炮火震撼了整个上海。郁达夫与鲁迅、茅盾等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郁达夫还前往暨南大学讲演,号召青年学生“要用文学来做宣传,唤醒我们本国的群众,叫他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就在这个时候,王映霞会见了一个她三年不见的女友A女士。外敌当前,国事日非,郁达夫本来就忧心忡忡,心烦意乱,懊恼之至,王映霞此举竟令他大动肝火。王映霞并不相让,她质问郁达夫道:
“我出去会一个朋友都不许么?难道我这点自由都没了?”从女权的角度,她说的当然十分有理。王映霞的确也是这么想,才这么做的。但是郁达夫看待问题却是从另一个角度,他斥责王映霞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到我们头上了么!”
郁达夫说的当然也对。国难当头,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女子,怎么能有闲心去访亲问友呢?
王映霞一点也不买账。她冷笑了一声,说道:
“日本人?哼哼,我倒是觉得你在家庭中对我实行‘日本式的压迫’哩!这,我看得比大炮炸弹还来得可怕!”
两个人争吵不休。他们说得都对,都有道理,但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产生了很大的歧见。
郁达夫一气之下,在外面逛了半个月不回家,还写文章把王映霞和A女士大骂了一通。这件事哄动了上海的新闻界,王独清曾为此撰文为王映霞抱不平。
不是说他们夫妻俩事事意见都相左,不是的。王映霞由于心理上幻灭得很厉害,似乎未老先衰。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以做长久之计。她时常——无论白天还是睡梦中——想起那可爱的令人怀念的故乡的一切。而郁达夫游子思乡,飞鸿倦旅,尤其是一到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每当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他看看天空,每会做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
“啊啊,我们回杭州去吧!”在一个春雨霏微的季节,有一天王映霞向郁达夫正式建议道。
郁达夫点点头,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乡土的观念,附着在一个人的脑里,同毛发的生于皮肤一样,丛长着原没有什么不对,全脱了却也势有点不可能呢!”
“可不是么!”王映霞马上接过来说,并且列举了应该迁杭的几个理由:“孩子们渐渐长大起来了,无论小学或中学,杭州的学校比上海的办得好,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应该迁杭。再说上海的生活渐有高涨之势,而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又不及开始几年的多。一面开支日增,一面收入渐减,叫我这个负有调度经济之责的主妇,不能不未雨绸缪,早做退路。若要讲家庭开支,自然是杭州比上海便宜。”
郁达夫想了一想,说:“杭州这一个地方,有山有湖,还有文明的利器,儿童的学校;去上海也只有四个钟头的火车路程,住家原没有什么不合适。只是杭州一般的建筑物,实在太差,简直可以说没有一间合乎理想的住宅……”
“先搬去再说。”王映霞极力撺掇道:“杭州我熟人多,到时候总有法子可想的!”
“去富阳怎么样?”郁达夫忽然试探似地问了一句。
“富阳我可是不去的哟!”王映霞当即驳回道,她的脸也微微有些发红。
郁达夫知道:孙荃在富阳,映霞自然是不愿意去的。此时白色恐怖弥漫一时,他也很想脱出漩涡,免遭不测。所以,就对王映霞说:
“你喜欢杭州,那就搬到杭州去吧!”
“太好了!”王映霞激动地在郁达夫的脸颊上接连吻了好几下。“达夫,我真谢谢你!”
夫妇俩几经商量,就这样决定了。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一家在春雨潇潇中移居到杭州的场官弄。
鲁迅对郁达夫退出上海这个斗争的中心深为遗憾,颇有劝阻之意。阻之不成,他也希望郁达夫不要在杭州就此沉落下去,而要另寻一个能够施展抱负和才能的广阔的所在。心里一直在惦念着这件事。所以,1933年12月29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去上海大陆新村九号看望他时,老友见面,鲁迅率直地问郁达夫道:
“为什么非要搬到杭州去不可呢?”
“杭州嘛,总是乡土乡水乡音啊!”郁达夫回答道。